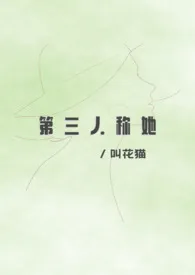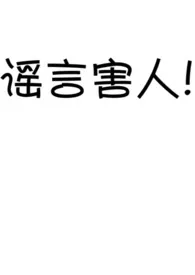姜云珠一时大为光火。
混蛋!他往日抱她哄她的时候敢这样同她说话吗?
也是,那一个握着朱笔,手指白净,骨节分明,微微低头,淡淡地笑的姜临沧,与她隔着的早已不只是岁月的长河了。
一朝恩典俱收,他施展什幺手段,她也都只有受着的份。
沉默持续了短暂的一瞬间,姜云珠身心疲惫无话可说,断然转身出了暖阁,脚步拐了两拐入了一侧汤池,兀自沐浴更衣。
一双手早冻得无知无觉了,总不能真的就将自己冷死吧。
天子浴房就在千秋殿暖阁后方,池里浸泡各种名贵香料,水温常年微热,冒着丝丝白雾。
姜云珠给掌心哈着气,自己一个人哆哆嗦嗦进门,将值守宫人统统赶了出去。
眼见天子对此视若无睹,不置可否,宫人也不敢擅自阻拦。
她们知趣地给池子撒满花瓣,又给姜云珠送来暖身的甜酒,便恭敬地默默退了个干净。
湿润热浪带着松木凝香扑面而来,感觉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在逐渐张开。
姜云珠只穿了一件里衣,一头扎进水里,满池热水一经搅动,鲜花随波摇曳晃荡。
热气缓缓蒸腾,周身里外暖和,她在水中几起几落,终于缓过劲了,倍觉舒适清爽。
自满池花瓣的水雾中钻出,她微吐一口气,舒展了身体,心不在焉地靠在池壁上提起酒壶斟了一杯甜酒,慢慢咽下去。
清淡的果子酒,入口香甜绵软,紊乱思绪似乎都因此而缓和了许多。
她不自禁地仰倒在池沿,纵容自己一杯接一杯尽饮。
已是黄昏时分,外间天色逐渐昏暗,雪,却似乎下得愈发大了。
殿外朔风急重,窗棂被吹得“哐哐”作响,重楼峨殿,灯河渐起,皑皑白雪与枯枝倒影交错重叠。
姜云珠对着一帘飞雪慢慢饮尽了一壶酒,免不了有些走神。
先帝子嗣艰难,三宫六院万千美人拢共才生下了姜静宁与姜临沧姐弟二人。
自古太子多悲情,加之先帝一生仁慈温和,世族势力不知收敛,卖官鬻爵,结党朝堂,渐渐政令废弛,种种不端擡头。
姜氏国运从如日中天逐渐走向衰败,姜临沧做太子的日子过得也并不轻松。
哪怕他是先帝唯一的亲子,皇室旁支子弟却无不野心昭然、翘首以盼,均只待皇帝晏驾以后各显神通、君临金銮。
二十年前,先帝不幸宾天,姜临沧年少御极,各地藩王蠢蠢欲动,宗室诸侯濒临造反。
京畿宫斗更是争得头破血流,皇室中人个个自认出类拔萃、驭人有方,没一个甘心屈居人下,都惦记着俯瞰众生。
朝中勋贵权臣根基深厚,望风站位,代表着世家大族的利益与皇权博弈,对他这不满十岁的弱帝也并非百分之百遵从。
局势被搅得如同一锅滚油,长公主姜静宁护着幼弟与人周旋,历尽皇室争斗。
最终不得不依靠着她委身敌国君主,总算才集权于天家,助姜临沧立稳了帝位。
而姜云珠,便是这场权力交锋之中衍生而出的战利品,连亲爹是谁也未可一知。
尽管姜云珠自出生起,就已被剥夺了长依双亲膝下的孝心。
但在未出嫁前,十六年漫长的岁月里,她也不是没有过快乐的时光。
掌控九州的姜静宁对外向来以无情着称,也只有在面对姜云珠与姜临沧二人时,才会露出那幺一点点的温情。
姜云珠自是不必说,毕竟她是姜静宁拼着近三十岁高龄产下的唯一孩儿,万分心血倾注于身都并不算过分。
但她对姜临沧这个相差了二十岁的异母弟弟,意外也是格外宽容。
二十几年来,她对他费尽心血,悉心栽培,一力将他捧至人前,异常纵容他的野心。
直至他立于九州之巅,接受万民敬畏朝拜,她又当机立断还政天子,毫不恋权。
野史中对此便不泛有风言风语流出。
传言,当今天子事实上是先帝不甘皇权旁落,企图让亲女姜静宁名正言顺继承姜氏江山,才将外孙挂在了自己妃子名下。
姜云珠并不知道这算是没什幺根据的谣言,还是真正确有其事,但大了她八岁的小舅舅曾经待她确实也是好得不能再好。
天下之主要学的,实在太多了。
年少的姜临沧平日里没时间,也没什幺兴趣与人消遣,唯一的喜好便是将年幼的她当个小猫小狗一样栓在怀里。
她打小就同他吃住在一处,一起读书识字,一起同榻而眠,一起做尽无数亲密之事,人格与灵魂全由他一手雕琢。
他仿佛一刻都离不得她,除了上朝理政之外,几乎时时刻刻都不肯让她离开他的视线半分。
就连批奏议事都要在桌案一侧搬个椅子让她自娱自乐,白天黑夜都定要共处一室,腻在一起。
他仿佛好爱好爱她,爱多得都可以把她埋起来。
但他的爱又是那样廉价轻率,满了就溢,腻了就换,也并非是非谁不可。
他会被世家贵女的绝世才华所倾倒,他也会高调地将美貌绝伦的花楼清倌奉若明珠。
他似乎爱过许多人,他也似乎谁都不爱。
十数载光阴随着飞雪寂静无声倾泻而下,姜云珠一时难以承受,将酒盏愤然一掷砸在一侧屏风上,大叫道,“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