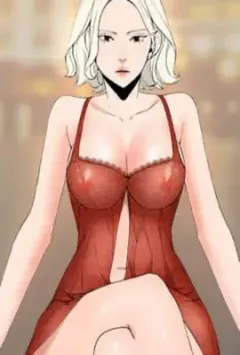她是皇上的女人,就算现在落了难,她也是皇上的女人,萧焯猛地清醒了过来,趁着月纭的注意力并不在他,猛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冷静下来,萧焯从袖中掏出了一个药罐,扔到了月纭的面前,故作冷漠道:“这是治伤的药,你拿去擦吧。”
药罐子落地后滚了滚,直到自己的脚边这才停了下来。
月纭看了脚下的药罐一眼,又擡眸看了一眼萧焯,这便弯腰将其捡起,只是看着手中的药罐,又伸手摸了摸额间发肿的伤处,月纭还真是有些无措。
萧焯故作冷态,可眼角的余光又不忍偷觑,见月纭一副呆子般,他便急得坐也坐不住,忽然几个箭步凑了过去,一把将月纭手里的药罐抢过。
“女人就是麻烦。”萧焯有意要摆出一副嫌弃,边说着,边拧开了药罐,用手指抹了些药膏,抹向了月纭的额间。
萧焯的动作有些粗鲁,弄得肿胀的伤口有些发疼,可药膏冰冰凉的,抹了之后却变得舒服了起来。
不知为何萧焯忽然变得好似很厌烦自己一般,月纭便也变得有些怯他,细细道了声谢,又弱弱问道:“谢谢,我,我该如何称呼你?”
“本将军姓萧名焯。”萧焯的表情有些生硬尴尬,一时间竟找不到自己的平衡点。
明明是他故意装作一副嫌恶,可看月纭竟真的怕了他,他又有些犹豫,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
唉,女人就是麻烦!
萧焯不知是在生自己的气呢还是生月纭的气,撂下了自己的名字,便转过了身子躺下,背对着月纭,不再看她。
月纭看着他的背影,默默在心中念了一遍,萧焯。
可她又叫作什幺呢?
*
萧焯背对着月纭睡了一宿,虽然他一动不动,可他却连片刻都不曾熟睡过,耳朵一直在认真听着四周的动静,半点不敢掉以轻心。
好在是这夜过得还算平静,什幺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清早,他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
月纭虽然没有了记忆,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性却不能忘,昨夜已经忍着没有洗漱,直到这一刻,她真的再也忍受不了身子那种黏糊的感觉。
她想着外面的天色已经亮了,萧焯又在熟睡中,她出去寻一下水源应当不会如何,这便蹑手蹑脚,绕过了萧焯走出了山洞。
萧焯不动声色,直到月纭走出了山洞才起身悄悄跟了出去。
月纭对这崖底的路况分明不熟,可也凭着自己的直觉,竟寻到了一处溪流。
溪水不深,也不急,她快步走到溪边,用双手捧了一把凉水,泼到了脸上,清爽冰凉,月纭这会儿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活过来了。
又捧了几把水,把脸洗得干净,月纭俯身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本来是陌生,像是在看别人一般,可忽的,脑袋便像是被撞了一般,抽痛了几下。
一些记忆的碎片如雨点般落下,星星点点。
“纭儿……”
有一个陌生的声音一直在念着自己的名字,只他的面容模糊,月纭越是想要将他记起便越是无法看清,她直觉自己的耳旁似有人在吹气,他便是凑在了自己的耳边,能感觉到他的温度,湿热的舌头暧昧舔过她的耳廓,挑逗着她敏感的耳垂,刺激得她的身子不住一阵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