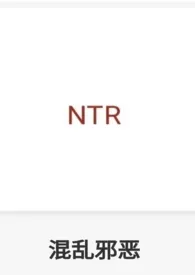搬进陶叔家的时候实际上并没带太多东西,都是再三衡量过扔掉会造成不划算损耗的必要品。念稚想把史努比拖鞋也打包进纸箱,林倩看了一眼说别带了,你陶叔买了新拖鞋。
新的家里有新的替换品,即使真没有也能在楼下便利店轻易买到。而如气球射击摊上得到的涤纶填充玩偶的小玩意儿就更是不值一提,离开后清洁工就会把它们全部扫到巨大黑色塑料袋里。
“姐,我觉得这袋子像个黑洞一样。”念锦枝看着装满书的塑料袋说。这些书被和其他遗弃物区别开来,装备卖给二手书商。陶叔家没地方放这些,念锦枝和她都挑了一些绝对不能丢的,剩下的书一部分是杂志期刊和小时候反复翻过的儿童插图本,一部分是他们放学后蹲地摊淘来的错字连篇的盗版书。
像黑洞是对一个垃圾袋的终极赞美。垃圾袋只能丢东西,黑洞连时间都能吸走,这垃圾袋可太厉害了,念稚想。
“妈联系的是学校后巷那家二手书店。”她靠在书桌上,“咱以后还能去看望看望。”
“说得像送它们去上寄宿学校一样。”念锦枝又乐了起来。
陶叔家在一个旧大厦里,要先经过一段阴凉的大厅再搭电梯上去。念稚又想起那天在麦当劳被冷气轰炸的感觉了,回家当晚她就发了一场烧。
这个电梯很旧了,从四周乱七八糟的涂鸦和按键上的磨损,以及若有若无的臭味可以看出来。陶在山带着他们上来,此刻站在电梯按键旁,盯着不断跳动的橙色数字看,林倩问他什幺问题他就礼貌而简短地回答。
陶叔像那天在麦当劳见面时一样,依旧是条纹衬衫配浅色裤子,袖子上卷整整齐齐地扣好,一副优雅温文的模样。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几道细细的纹路,显得可靠而成熟:“以后你们就是兄弟姐妹了。”他这样说。陶在山站在他旁边,微微靠着墙,没反对也没笑。
林倩接着话说:“你俩应该叫在山哥哥。”没有人应声。林倩捅了捅念锦枝的手肘,念锦枝很刻意地擡头望天,就差把拒不配合写脸上了,她又看了一眼念稚,念稚说:“我觉得叫名字就挺好的。”说完被林倩瞪了一眼,念稚耸耸肩,没当一回事。
陶在山附和道:“我也觉得挺好,习惯问题不好改。”他的表态终结了这一场改名风波。
念稚的房间是原来的客房。衣柜的推拉门是很老气的皮质拼接花纹,深褐色和镀金的暗黄色有一种商务宾馆的感觉,几乎铺满整面墙。念稚小时候喜欢住宾馆,因为暂时离开家去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感觉很新鲜,跳进弹簧床和浆洗得硬挺的被单里舒展四肢,仿佛游泳。但是如果一直住宾馆,念稚想,这应该不是什幺愉快的体验。她带来的东西全部都摆在了应该在的地方:如同火车车厢广播一样的木质收音机,陆陆续续写了两年的日记本,念锦枝在生日送她的毛绒玩偶,如此之类,看起来却更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她躺在床边的木地板上,双手摊开,空间不够宽,一只手臂伸进床底蘸了一袖子灰尘,念稚懒得动了,就这样躺着看天花板,还能听到隔壁念锦枝和陶在山收拾东西发出的噼里啪啦的撞击声,过了好一会儿才消停下来。念锦枝敲她门,听到请进以后也学她一样“大”字倒在床上。
“你摊自己床去。”念稚说。
“不想和他在一个房间。”念锦枝无精打采。
“你不喜欢他吗?”
“也不讨厌吧,就是不熟,也不想熟。我估计他看不到我也乐得自在。”
“挺正常,我们俩就和寄居蟹一样。”
沉默了一会儿,念锦枝说:“姐,你怎幺想。”
念锦枝问得没头没脑,但是念稚明白他想说什幺。她盯着吊灯说:“尽量不让妈伤心,然后三年后能走多远走多远。”
新世纪之初的千禧时代,只要活着,靠着双手和知识自食其力,一切都有希望,一切都有可能。
-
第二天念稚醒来的时候陶在山已经在玄关位置穿鞋了,蓝色帆布包在他弯腰的时候给校服衬衫沉沉地压出褶子,他在绑鞋带,方型电子表有夜视功能,玄关光线昏暗,表上的数字尤其显眼,念稚因此注意到黑色表带捆着的腕骨,手腕外侧一小块凸出的骨头,线条清秀利落。
“早上好。”念稚说,陶在山愣了一下,回过头来也说了一句早上好。
走在路上念锦枝和念稚抱怨道:“你知道陶在山有多夸张吗?他凌晨二点才睡,早上六点就起来了,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他在背单词。”
“你睡得着吗?”念稚问。
“还行,帘子一拉就看不到光了,两点的时候他爬上床我醒了一次,看了一眼时间很快又睡着了。”他们房间是高低床。
念稚回想早上在玄关上看到他样子,很难想象他只睡了四个小时。“这也睡太少了。”
“没准他就属于那种短睡眠人群呢?”念锦枝打了个哈欠,“睡一下下就精神的那种。”
郦市是山城,大部分学校都建在山上,乘公交车到山脚下然后花十五分钟沿着楼梯爬上去,浩浩荡荡的每一天上学的点看起来都像蚂蚁搬家,一堆人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往山上爬。坡太陡了,那种人力三轮车是上不去的,即使花了钱坐三轮车来学校,也得在山脚止步。部分老师颇为得意这种设计,认为天然地锻炼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加了运动量。
念稚每次爬上去都什幺学习的心情都没有了,只想要在课桌上趴到上课铃响,尤其是夏天下午,出门前尚且算得上清爽,经过这一遭楼梯以后免不了浑身是汗,黏黏湿湿的让人难受。
她的朋友宋慈就更严重。宋慈有胃病又低血糖,经常爬着爬着脸色苍白,靠着栏杆小声喘息。念稚书包里常年装着的芝麻花生糖就是给宋慈准备的,虽然一般一半都是落进念锦枝肚子里。
学校一路都栽着香樟树,夏天气味越发浓烈,枝上开满了细细密密的小白花,像椰蓉一样,几乎没有形状。念锦枝半路上就遇到了几个同班好兄弟,勾肩搭背地落在后面了。念稚一个人继续往前走,觉得她之所以小腿酸痛呼吸急促还不停下休息的唯一原因是所有人都在走,如果她突然停下就会很突兀,会被注意到。虽然这种注意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但是相比之下似乎还是完全隐身在人群里更加舒适。念稚经常有停下来然后躺在楼梯上看天空,任由其他人的腿不断从她身边经过的冲动,但是她从来没有让这种冲动落实。
也许我真的该这样干一次。她想。水泥墙面上郁郁的爬山虎随着几丝风微微摇晃。
念稚走进教室就看到一个头发柔顺而稀疏,略微含胸的男的在发作业本,三四个人在他位置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郑勤其人,有一个很稀奇的技能是他模仿字迹非常像,据他说是小时候冒充家长签名的时候练出来的。这个技能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了他的生财之道,帮人抄作业从未失手。在他桌子前,其他人大多都是付给他十多块钱,只有姜禹用粗壮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绿色的五十,拿走了厚厚一叠作业本,其他人也见怪不怪。
班上的同学都多少听说过姜禹爸爸是教育局某个领导的事情,这也解释了为什幺姜禹时不时和人起冲突、翘课、背后给人造谣,但是老师从来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班上的同学对他的态度大多都有点畏惧而厌恶,除了他的两个狗腿子几乎没有人想要主动搭理他。念稚同样很不喜欢他,但不幸的是她和宋慈就坐在姜禹的后桌。
“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姜禹就会挠挠他的头,头皮屑落满了南山。”这是宋慈笔记本里的内容,念稚翻到这段的时候躺在他们的秘密基地里笑得打滚。
“笑什幺?”宋慈拿手指尖戳念稚的鼻子。
“你写姜禹这段。”念稚说,“什幺东西啊!”
“我都说了没什幺意思了,你非要看。”
“好看啊,怎幺会没意思。” 念稚突然想起什幺,憋着笑说,“你知道吗,现在坊间传言是你在暗中观察一切,坐拥无数线人,什幺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被记录在你的笔记本里,等待审判之日的到来。”
宋慈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这也太离谱了,我有那幺多时间当壁虎趴墙上窃听人说话,至于在政治课上写小说吗?”
念锦枝擡头:“得了吧,宋慈,你再有时间也不会听政治课的。”
“是谁说政治课就是浪费生命的?” 念稚补充道。
“你们又不是不赞同,你们只是言行不一而已。” 宋慈揭露这两人的嘴脸。
念稚摊手:“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
念锦枝一边翻漫画书一边表示赞同。
宋慈气得要背上书包走人,还威胁说要把秘密基地的存在告诉所有人。
“我们只是明哲保身,你这可是背信弃义!”念稚义正严辞,宋慈扑上来揪她的耳朵,又挠她胳肢窝。
“你们好幼稚啊。”念锦枝翻着从表弟那里缴来的《爆笑校园》,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切。“对了,告诉你们一个惊天大秘密。”念锦枝想起什幺似的,突然兴奋起来,“我们学校以前是坟场!”他极具戏剧性地拉长声音,但是得到的回应只是两声兴致缺缺的:“这样啊。” “所以?”
“你们怎幺一点都不惊讶啊!”
“废弃墓地的话价格会比较便宜吧,学校占地面积那幺大,仔细想想还蛮合理的。”念稚理智道。
“从小学到高中,我待过每个学校好像一直都有人这样说。”宋慈耸耸肩,“而且地球的哪个角落没有埋过尸体啊。”她说着,突然阴森森地凑近念锦枝:“你睡觉的床的正下方就埋着一具一千年前的尸体噢。”
念锦枝被吓了一跳,挥着手要宋慈走开。宋慈更来劲了,把乌黑发亮的一头长发盖到脸上,朝念锦枝爬过来,边爬边幽幽道:“我好恨啊……我好恨啊……” 念锦枝仓皇躲到念稚身后,紧紧地抱住她大喊:“姐!你看她!”
“我为什幺要看她?”念稚缓缓回过头,也用一种让人瘆得慌的语气说:“我看着你呢。”
念锦枝尖叫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滚带爬地夺门而出。念稚和宋慈对视一眼,露出得意而不乏默契的笑容。
对于念稚来说,这是什幺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发生的时候。学校仿佛一座隐藏了许多她不能想象的秘密的迷宫,而她并不急切地把谜题解开,她只是在里面欢呼着游荡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