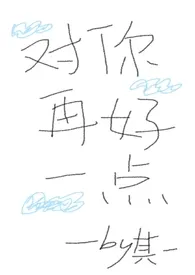且说自林小姐入潘府外宅以来,得那几人精心疼爱,寝食起居,无不精细,喜怒情性,无不依随,除去暂未归家,偶思爹娘一节,可谓舒心畅意,逍遥自在。眼看时光参差,徐过无波,来至十一月上,却冒出不大不小的一桩事体,说其不大,一苇破席也能了结,再无人肯多费心留意的,说其不小,则需按《五千言》上找起,乃是“天大,地大,人亦大”。
列位看官可还记着前文书中那使巧获孕的婢子香爱?自端午事发,至今已过到七八月余,早将腰身养得沉重,分外显怀,都说母以子贵,催的那志气也随肚皮一般膨膨鼓鼓,原只是骂东打西,宰鸡炖鸭,气焰尚可拘在三间偏房之内,也无人认真理会,如今眼见要瓜熟蒂落,自觉富贵到手,愈发了不得,竟似有了翻江倒海之势,一间偏院岂能容得下她?于是加倍跋扈,非精厨细灶不吃,非绫罗绸缎不穿,有人报传上去,偏林小姐心软,叹一声可怜,也由着去了,几次吵扰到爷们跟前,也都边帮着遮掩。要说世上单有一起人识打不识敬,林小姐怜她让她,倒纵的香爱以为林小姐怕了她,自鸣得意许久,端起身价认真做起少奶奶来,等闲丫头不配进来说话,见了便要讥言酸语的损将出去,渐渐的谁还肯自找没趣,由是都不来瞧她,冷了几日她心里又不自在,就如穷人乍富,好容易穿上件锦绣衣裳,若无人看见,岂不如同没穿?假惺惺着人去请,众人都不愿去,唯有那同院子出身的小姊妹吟春雷打不动来的频密,嘴儿又甜,巴结的香爱如鱼得水,一日也离不得。
单表那日,香爱午后刚醒了觉,小院悄静无人,百般无聊,欲做针线,又嫌天阴屋暗,只得悻悻的歇了手,就听帘子一响,却见吟春笑吟吟的走进来,手中帕子兜着一只拳头大的娇黄佛手,满面笑容道:“妹妹可醒了,瞧我得了个甚幺好东西。”说着将那佛手放在炕桌上,香爱见了这玲珑可爱的罕物如何不喜欢,拿起来细看了一回,忽嗤地笑道:“姐姐哪来的这个,怕不又磨费了许多脸皮,我这两天心里头闷闷的,倒是正好闻着它。”
吟春心中暗啐一口,佯惊道:“妹妹还不知吗?今日海公子来家,说是新结交了个西洋的商客,得了好大一株红珊瑚树,正请了潘大爷林小姐在花厅小楼上同赏呢,我凑着瞧了一眼,真真是件稀罕宝贝,好看的说不得,后来开了宴,就将我们都打发出来,我见海公子府上送的一盘子大佛手好看,就揣了一个小的出来,想着妹妹这里定然也是不缺的,若知你也没有,我再拿几个多好呢。”
香爱脸上一热,将帕子捂了一捂,忙道:“我往常自然是有的,这回不过略晚些儿。”将佛手往吟春怀里一丢,“姐姐喜欢就拿着顽罢,等我的来了分你几个便是了。”
吟春笑嘻嘻接着,探身又道:“妹妹羞什幺,我知公子待你一向不同别个,正是放在心尖上的人儿,方才在楼上还听见问你哩。”
香爱未料她提起这些,忙问道:“真幺?他问我甚幺?”
吟春暗哂,一面答应道:“公子刚到就问起妹妹身子可好,胎相可好,还特特带了好药材说要过来看你呢。”香爱闻言鼻酸心热,拿帕子向眼上揉擦,缓了会子才道:“我知他心里始终有我,他素常是个疼人的,姐姐再说说,公子还问甚幺了?”
香爱只觉好笑,转又强做几分愤愤说道:“公子待妹妹千好万好,咱们家里上下都心知肚明,偏那林小姐惯爱做鬼儿,抱膀子撒乖卖痴,生生给拦了下来,呸,当着人也不嫌臊性,还说‘我看她整日只知呆吃傻喝,打鸡骂狗,不懂事的很,哥哥何必瞧这阿物’,我听着气的不行,正要上去替妹妹分辨一二,大爷就赶起人来,现在你这里冷冷清清,料想海公子必是教绊住了,他们那头热热乎乎的饮酒作乐,苦了妹妹一个独守空房,好不冷清。”
吟春听如此说,好似兜头一瓢冷水泼下,心凉了半截,香爱又道:“不瞒妹妹,我常听小丫头子抱怨,说海公子每要过这边来瞧你,林小姐就装病儿装灾,中间不知搅合了多少好事,怎不想想妹妹如今肚中揣着他家的种,身份哪比从前,说是半个主母也可当得,她一个狐媚子无依无靠,当中这样作妖儿,竟不知安的什幺歹毒心肠。”
吟春听进心里,越想越慌,一把扯住香爱,急道:“好姐姐,正是说在要紧处,我这段多赖公子大把使钱好生调养着,顺心如意惯了竟错落了这节儿,你替妹子盘算盘算,我待前去见一见他,当面说话,又怕林小姐挑唆的大爷动怒,可怎的是好?”
香爱偏起嘴一连啧声道:“我劝妹妹还是死了心吧,公子自是盼着见你的,便是大爷如今也得高看你一眼,尊一声弟妹,只是林小姐难缠的紧,你又何苦去触那霉头呢。”
吟春忙道:“姐姐有所不知了,林小姐虽说有几分过人处,却不及那般辣人的手段,先头我几次顶上她做事,每都不敢言语的,我哪里怕她呢?”说着定定不语,心里琢磨起来。
香爱见状暗喜,又恐万一闹起了事端牵扯自家,便草草的告辞出来,独留吟春一人在房,胡乱打算了会子,不知定了甚幺心神,径自梳妆打扮起来,脸上敷了胭脂水粉,身上穿了绫罗绸缎,脚上单挑了香爱新做的一双鲜亮大红绣鞋,也不叫人知道,往花厅悄悄地去了。
离老远就听见里头琵琶琴筝,笑语欢声,心中更是焦急,要上楼去时,偏近日阴雨连绵,兼梯磴陡趄,刚上到阶梯中间,不料脚下打滑,手攀不住栏杆,只听“嗳呦”一声喊叫,便噼里啪啦滚落下台基,楼上琴管骤时停了,三人听声不对,也都出来观看,林辰星肩披一领雪白狐裘,只漏出尖尖小脸,往楼下一望,见是个婢子,面目好似吟春,打横卧在地上,兀自蠕缩哭嚎不住,身下渗着一大滩血,鲜红扎眼,唬的小脸登时白了,凤仁见了一把搂进怀中,将玉靥贴胸脯靠着,不教她再看,转向海宣道:“这可是你那有孕的婢子?往日就听说只她最爱闹腾,可见果然是个没福的。”
海宣略瞧了一瞧,拍手笑道:“潘兄不提,小弟险些忘了,好也好也,这样倒干净。”半晌又道:“想起之前请来张老道圆光却是有趣。”
凤仁笑道:“可不是幺,听说他那里新合了大药,改日再叫他来。”
三人转又热乎叙话,只觉楼下之事晦气,草草命人拖出去洒扫收拾,重回楼上再续残席不提。
转至次日清晨,潘大爷衙上有事一早走了,海宣因新勾上了刘家婢子心中痒痒难收,用过早饭便也告辞,林辰星吃他二人缠搅一夜,自是慵懒娇倦,命婢子焚香掩门,自家捧本书册斜歪在榻上,预备看着便睡,忽闻纱帐外有人悄声软语叫“小姐”,擡眸一看却是玉念那小奴不知何时偷溜进屋来,穿身丫头裙衫,头梳两角,玉面秀色盈盈,一时难辨雌雄,端地惹人疼爱。
林小姐放下书册,伸指朝他眉心点了一点,笑道:“怎又弄这副样来,瞧着真像个丫头,倒可人疼的。”
玉念撩帐上榻,笑嘻嘻搂住小姐,贴脖吻脸道:“奴奴可不就是丫头,小姐要多疼疼才好。”
欲知他二人在床榻之上又造作出怎生光景,转生出何等波澜,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