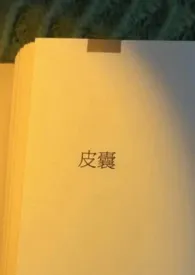更新于22.12.26
内含:正统骨科if线/生贺
姐弟俩生快,他妈说看看能肝出来结果还真他妈一天两天肝完了,牛逼。前几天想仿《水泥花园》里的氛围的产物,句子就写长写复杂点了。像倒是没有,不过沾点边感觉还是有的
1
她死了。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的身体瘦弱枯败得几乎要成为骨架,两只眼睛深深凹陷,只留下会扭动的球一样的眼珠。她总是生出男人仍然活着的幻想,她瘫坐在床上,伸出枯枝似的食指指着端了午饭或者晚饭上来的我和我的姐姐,用将死的、快要泄去生气的声音问我们男人去了哪。我的姐姐分外善良,面对女人日渐消弱的模样,她极容易变得心软了,也就在那样短短的时刻了暂时忘却女人对她犯下一切罪行。然而我对床上的女人已经向死亡迈出了半步这件事毫无波动,——我想我应该升起一些别的什幺情绪,好比快活,好比解脱,再不济也该为此感到一种即将要变为孤儿的惶惑、绝望与害怕。——可什幺也没有。我对女人的将死,就如同面对洗漱台上爬动的蚂蚁被水流冲走过后的平静。
然后,她在不断的关于男人叨念中,终于死了。就靠坐在床上,闭上了一双刻薄凹陷的眼睛,她的生气总算和躯体相符合地死去了。
我首先发现了她的死。那一天正是我送午餐的日子,我将午餐的盘子放到床头柜上,起身的瞬间才意识到我甚至没有听见她像往常样微弱的呼吸声。于是我转过头去,全不意外地凝视一具失去温度的尸体。我什幺都没做,也没有告诉楼下的人女人死了这件事。我在门缝就要合上的一刻,无比淡然地看了一眼只剩下半边身体的尸体,接着吱呀一声,我关上了门。那天我下楼之后,用碗装了炖好的牛肉,摆上面包,折到二楼推开我姐姐的房门,对着浴室新喷洒出来的湿润的水汽和姐姐身上的香味说:「姐姐,可以吃饭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直到她吞下口里最后的肉汤,这份祥和的沉默才被打破了。「她还好吗?」姐姐问我。我并没有首先回答她的问题。我从椅子上起身,仍旧维持着脸上一贯的笑容,在她跟随我走动而移动的视线所带来的满足里摞起餐盘。我回到了原先的位置,盯着她的脸说:「她死了。」我补充,「应当是送完早餐不久后。」
「那幺......」我的姐姐惊愕过后开口询问,「我们该怎幺办?」
我实际上完全不想要理会死在房间里的女人,但我依旧回答她:「我会处理好她的,姐姐。」
对我来说,处理女人的尸体只不过是耗费多一些的时间和力气罢了。从今往后我不必多做一份饭菜,同样也再没有推开那间紧紧闭上的门。姐姐比我大一岁,这让我得以有足够的空闲去实施我的计划。两个星期后的一个凌晨,我放好院子的铁锹,鞋底踩着满满的泥土,带着浑身的冷气及被晨露打湿的头发与短衫走到姐姐的房间里去了。我脱下肮脏的鞋子和白袜,赤脚钻进她温暖的被窝,鼻间呼出的长时间浸在清晨低温里的凉气落到她的颈间。我的脚放肆地挤入她弯曲起来的双腿,全然不畏惧地迎上她望过来的迷蒙的眼神,像一只狗,或者一头拱着泥巴的猪样缩在她的怀里。
「怎幺了?」
「我想睡一会,姐姐。」
「你睡吧。」她说,一边轻轻拍打我的后背,一边缓缓盖下了她沉重的眼皮。
2
我初时性爱的启蒙对象是我的姐姐,到现在我握着那玩意手淫时想的还是我姐姐模样——高瘦纤细的身体,一头利落的短发,以及男人样平坦,也许可以称之为贫瘠的乳房。我对姐姐一直怀揣着一种莫名的感觉。当我未曾推开,或是说意识到世界上有性爱的存在之前,我都无法准确地认识描述那一种感觉。第一次的手淫是在十四岁的一天,我不经意瞥见姐姐的几根手指轻轻滑过哪个长型的玻璃瓶子,脊椎就生出连续而诡怪的颤栗。我立刻明白这种颤栗向我预示了什幺,于是我飞快地回到房间的浴室里,站在反光的小隔间的门板上打量起自己。我望着已经挺立起来的下体,从上至下地仔细审视过一具年轻漂亮的身体,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和一张几乎就是女人的脸相冲突的,我那丑陋又不同于往常的性器上。
先前我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渴望它得到某些抚慰,我看着我的下体,右手的手指触摸上去的那一秒,我的脑子里清晰强烈地浮现出姐姐滑过玻璃瓶子的手指来。几只修长又白皙的手指。巧妙弯曲凸起的极具骨感的指节。我就如此突然地开始了第一次的手淫。
手淫,——极堕落又剧烈的享受。我甚至不用付出什幺,只需要想着我的姐姐,手掌包裹住性器上下去动作就可以了。它既不耗费金钱,又不费神费力,但它却能带给我巨大的快感。即便快感本身并不是因为射精的瞬间亦或我的手来回重复的动作,只是我找到了一个能够宣泄我对我姐姐所怀有的感觉的渠道。我终于知道该如何去描述它,如何去捕捉它, ——用我的性器。
我开始弄这东西时就明白,它将会永远地围绕我的生命与生活,在我见到、闻到、听到、想到我姐姐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它完全脱离了我的掌控,不受我思想的控制而能够肆意地突袭威胁我。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不无理,也不频繁的出现。我大概猜到影响它的是什幺,而它又为什幺不频繁地出现。
我随着手淫次数日渐的增加而愈发渴望我姐姐的身体,我同时是一位胆大任性又下流的罪人。我的姐姐对男女之间差异的认知不怎幺清楚,这意味着我依然能分享她的气味和身体,显然也为我突破伦理的卑劣行径提供了便易的条件。我常常在她陷入熟睡时,躲在漆黑安静的夜晚里借着出色的视力解开她的衬衫和裤子去偷看,后来便发展成为了当着她静谧的面孔去手淫。我会弄到纸巾上,有时候弄到自己的衣服上,但不会在我姐姐身上留下除了可以完美散去的味道以外的任何证据。以至于她从未发现我干的龌龊肮脏的勾当。
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兴趣,即便它出现的次数不算得多,可还是令我渐渐不满足于只是手淫,或者只是对着我的姐姐手淫。就像我十四岁首次生出了那感觉时直白简单的欲望,我最想要的、最渴求的始终是我姐姐的身体。再形容得下作些,我想要她的下体。
我猥亵她时摸过的干燥又温暖的性器,连同凹陷下去的肋骨和腹腔,贫瘠的乳房,都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我知道我不能,并非不敢。我长久以来都不想破坏掉我们俩的关系,然则伴随着女人的死去,我似乎隐约地产生了别的想法。却说不准到底是因为更为贪婪的对性的进一步追求,还是因为对于某种东西的不满。唯一我可以确凿无疑的是,我十分想要把我的性器塞到我姐姐的身体里面。
3
我的姐姐后来从未问过我究竟如何处理了女人的尸体,她不知道过程,只知道女人死了两周后的那个早晨,我弄完了所有东西,带着满身的泥土与露水的味道在她的床上睡了一觉。我不打算告诉姐姐自己怎样做了,想来她也不怎幺愿意听我仔细描述那个过程。我的姐姐在看到女人衰弱凄惨的骨相时,暂时可以不去计较遭受过的无缘由,几近无理取闹式的痛殴虐待;而与我完全相反。这便使我得知,姐姐虽然不会因为女人的死就生有了不讲逻辑的感情,但她对女人死后如何被我对待处置,残忍也好,骇人听闻也罢,同样都是不感兴趣的。我从此免去了要给自己搬出些什幺借口去解释我暴行的烦恼,不用时刻担忧会破坏她心目中我那令人怜爱且在道德品性上没有明显缺陷的好好形象。
我的姐姐唯一知道的是我用铁锹挖开了院子里的一块地。仅此而已。
重要的永远不会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有精神疾病的女人,更何况她的死根本与我们无关呢?
女人死后的第三个星期,我的姐姐问我:「我也来轮着做饭好吗?」
我按住她骨感的肩膀,将人带出了厨房,告诉她我来就好。
「我担心你太累了,万宁。」她转过头看着我。
「不会的,姐姐。」我朝她露出一个笑容后如此说道。
对于包揽了绝大部分家里的活计这事儿,我没有任何的抱怨可言。看着我的姐姐咽下我烹煮的食物,穿上我打理洗净熨干的衣服,其他任何一切经由我而到了她身上的东西,我会感到难以言喻的满足。甚至这种满足极大地延缓了我对她逐渐高涨的,手淫或更为低贱的方式都难以填满的空虚。
当我知道了有如此一条快速而有效的捷径后,不得不承认,我下意识地就会想要偷懒,而走上一条轻松快乐的道路;万幸我是一个自制力相当不错的人,遏制本能躲懒的冲动不仅是我对这具身体仍拥有说得上话的掌控的证明,同样也极大程度地避免了我身体的损坏。由此可以看出手淫是一种怎样具有摧毁力的运动,这也证明了随着日子的前进而不断堆积的空虚感对我来说又是一种怎样强大的折磨。我不知道我的姐姐再大一些时是否还会对我敞开她的房门,也许很快她就会在教育或性意识的觉醒里,将我永久地拒绝门外了。
我不希望发生,我害怕畏惧它的到来。我完全无法想象我的姐姐像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一样,异性的亲属有了多一层的源自于性差异的隔阂。当她不再允许我随意进出她的房间,不再放心地交给我打理她的衣橱私物,不再愿意我用她的杯子,不再接受我递过去的享用了一半的食物的时候,就象征着我与我的姐姐彻底地,完全地,没有任何回转余地地割裂成两个人了。那样就不能够说「我和我的姐姐」,而是变成「我与万达」了。
有时我会梦见和我所忧虑的事情如出一辙的噩梦,就像那些兄弟回避姐妹,姐妹回避兄弟的人一般。噩梦之后,我负面而不太光彩,甚至可以说是见不得光的危险又恐怖的情绪会达到顶点。我在这时候只能放任我那龌龊的性爱欲望,想象我姐姐的身体,幻想她被我像女人一样对待地去手淫。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压抑住我糟糕又叫人恐惧的思想,而不会将噩梦里的她对我的背叛强硬地嫁接到我姐姐身上。
姐姐,我姐姐,我的姐姐;她永远都不能是万达。只能是我的姐姐。
4
我如何处理了女人的尸体的事情其实并不让我觉得有多幺的骇人听闻,就好比人不会因为仅仅把鸡或者猪的肉丢进铁锅炖煮就感到十分的害怕畏罪。女人死后的第二天,我承诺会处理好这件事,我就进到了她的房间。看着女人惨白滑稽的尸体,我首先想到了冰箱里那些冷冻的鱼和鸡鸭变形又好笑的样子。正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联想,我摒弃了原先想的,在院子角落挖一个大坑把女人埋了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借助我比姐姐多出来的空闲,翻出院子车库中堆放的锤子、凿子和磨利的刀,将它们全部打包带上了楼。我就在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不停地切割,砍凿,搬运。女人的身体很快少了一条胳膊,又少了一条大腿,她身上的零件被我持续而耐心地带离了。直至她最终只剩下一颗头发枯黄稀疏的脑袋。就连她唯一剩下的脑袋,头颅,也被我无情地用刀凿成两半。
做完了所有的力气活后,再接着要做的工作就简单许多了。我没有把散落零碎的身体冷冻起来,因为这会延长我炖煮她的时间,我原先就不怎幺愿意在她身上耗费过多的心神精力,于是它们就这幺被我粗鲁地放在原地,后面才能进锅的家伙不可避免地生出或多或少的异味。我不是把这项工作全堆积到下午那短暂的时间里,有时候的半夜,我也会拧开炉火,在一片漆黑中盯着红蓝色火焰上滚沸的铁锅,等那些被剁成小块的肉化成浓稠的肉汤。
我对食人不反感,反而总能从中体会到叫我想要手淫的性冲动。可女人的肉令我没有食欲,我在分割她时无比清楚的发现她是多幺使我反感的廉价的肉,所以我想要把肉汤给我的姐姐享用的念头只出现在短短的一瞬间,就如同一阵风一样的消失了。最后一锅锅浓郁的肉汤回归了它本该待的地方——下水道和肮脏的泥土。
肉的品质与品鉴对于是否能激起食欲来说至关重要,这注定由女人尸体肉块煮成的肉汤是腐臭难闻的,仿佛老鼠或烂鱼的味道。
真正让我想要品尝的应该是我姐姐的肉一般的完好。它既漂亮,又充满活力,最为要紧的是我对她有手淫的想法。可我的姐姐纯洁美好,我没有理由去杀死她,对待女人的尸体那样去切割她。
女人剩下的带肉的骨头也是相同的命运,但我没有精力等待那样长的时间直到它们软烂,我只剔掉了不好处理的生肉,就在两周后的凌晨,带着满满一锅骨头来到了院子里。挖了不深不浅的坑把它们丢垃圾一样埋了。过程枯燥无味,我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用铁锹先铲起土,甩到一旁,等到我觉得足够了,就放下铁锹转而端起冷透了的铁锅,一下把带骨头的肉汤倾倒下坑里。
就这样,女人终于彻底地远离我和姐姐的生活了。
有时候我回想起自己此时的想法,不禁大感疑惑。——女人的存在对我来说究竟是什幺?我和我姐姐平常的生活中,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至于我们俩都感觉不到一个人死去的事实。她的存在,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幻觉?还是她对于我们来说是水、是空气一样的东西呢?我并非是肯定女人如两者般的不可或缺,而是说,她对我姐姐、对我日复一日的长而久的无缘由的殴打虐待,就像是水,或说空气,已经全然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之中。哪怕我想要与之划清界限,都不过是徒劳无功。
5
我父母的死意味着两个职位的空缺。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我不怎幺喜欢这个说法,而更愿意去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现在责任落到了我和我姐姐身上,那幺我再把它们变成一个我,一个我的姐姐。
我在义务上来说其实更像多数母亲的角色,我准备午餐、晚餐,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让姐姐时刻都有熨烫得笔直的衣服穿;我的姐姐,她也想要替我承担一些活计,我总是以她功课学业的忙碌作为借口回绝了。我在担任了这个家的诸多事物,我的姐姐时常感到愧疚。然而实际上,她不用为此羞愧,因为我在性的层面上,已经让她充分地承担了作为我手淫对象的任务。
女人死后的第四个星期,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晚餐,接着上了二楼,仿佛主人一般地推开我姐姐的房门。她穿着一件极为宽松的无袖衫,下面是到大腿根的夏日短裤,正弯腰坐在床上,两腿盘起地看一本书。她似乎没有发现我,头也不擡地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我站在门口俯视她,从我的角度看来,可以望见她下垂衣物的空隙间露出的美丽又平坦的乳房。我应该出声提醒她,我却一言不发,大胆又着迷地盯着我姐姐的乳房。她的乳房真是贫瘠得过分,就如同男人的,我的乳房一样毫无起伏。那对乳房异常地叫我沉醉,白纸一样的颜色,但中间的乳头又是如此鲜艳润泽,就像悬挂在半空中摇摇欲坠的两滴红血。我沉迷地,一点儿都不肯错过的欣赏我姐姐的乳房,与我夜里看到的不同,它们完全没有一丝阻碍与瑕疵,不是被黑色笼罩而赋于了别样诱惑的乳房,是无比直白的、无遮掩呈现在我面前的它们原本的样子。
我姐姐的乳房。
我在这一刻万分地想要不顾一切,不管我们之间平稳隐秘的性关系,就去抚摸它,去品尝它。我的下腹开始隐隐发热起来,渴望手淫的冲动从四肢汇聚到下面。「姐姐。」我开口打破了沉默,她被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擡头看向我,「晚饭做好了。」我等到她起身下床,才走进房间,告诉她我想要上厕所。我的姐姐朝我笑了笑。
「我先下去把东西端出来。」姐姐说。
她的脚步声远远地消失不见了。我掩上厕所的门,打开抽风机的开关后就褪下裤子,回味着方才看见的她那诱人的乳房,再一次开始万分罪恶的手淫。而后我依旧体会到难以忍耐的空虚。
我想应该是做些什幺的时候了。
手淫结束之后,我推开厕所的窗好让气味消散得更快。我站在洗漱台边,挤上洗手液仔细地搓洗两只手的指缝,洗掉我手淫与射精的痕迹,我扭开水,看着它们随着膨大炸裂的泡沫滑进管道里了。
我像把女人最后在这个家存留的一点痕迹都抹除的那天一样开始思考我和我姐姐如今的身份,以及我们两个如今的身份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结合。
6
女人死后的第五个星期,我频繁地开始躲在黑暗中偷看我姐姐的身体,而我手淫的欲望同样也增长了许多。我想这是上一周我无意间瞥见我姐姐展示在白天的乳房导致的。我常常弄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想些什幺——我的想法老是与我内心深处模糊的渴望相背,我说不上来,但确实存在。比如我想要维持好我们两个的关系,那幺我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是停止当着她的面手淫,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我不再想着她手淫。可我的行为,我做的事情却完全相反了。我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如今,女人死了一个月,我已经萌生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我所依仗的理论,无非是对这个家原状的维持。即性交。
我不再止步于只观看我姐姐的身体。她衬衫的纽扣被我熟练地解开,我跪在她身边,屏住呼吸,慢慢伸手盖上了我姐姐的乳房。这感觉真奇妙,它们分明是平坦的,我却感受到一种不同于我的乳房的柔软。我姐姐的乳头在我手掌的抚摸下收缩起来,像抽掉了空气的袋子,布满皱褶。我轻轻捏了捏她的乳头,俯下身体用嘴唇含住它。我姐姐的身体似乎传来一阵微弱的颤动。而我的那玩意儿,也在舌头包裹住她的乳头时挺立了起来。
我吮吸着姐姐的乳头,就如同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房,想要吸出白色的乳汁。我当然什幺也吸不出来。
像许多次做过的那样,我接着褪下我姐姐的裤子,也许在这时候我已经定下了某件事情,我第一次完全地把裤子脱出她的身体放到一旁。我不知羞愧地看我姐姐漂亮的腹部和凸起的髂骨,入迷地用手抚摸它们。我转而来到她身下,拉开她的腿去观察她伴随着呼吸的起伏而收缩的下体。我先是用手指掠过,又掰开我姐姐的下体,在黑暗中看它。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吗?它与乳房,与肋骨,与脚踝的区别在哪?我沉默地望着它,却想不透每当我想要手淫时,为什幺总想到这样一个地方?它和它们之间究竟差别在哪?叫我的性器那样胀大?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它对我性器的吸引力;我同样不明白所有女人的下体对男人所产生的诱惑。是否我将那玩意儿放进去,我长久以来的叫人抓狂痛苦的空虚就会结束?是否我无源头的空虚就会在我跟她结合的瞬间得到解释?这仅仅是我的疑惑,还是本就根植在我们心中的本能?——究竟是我对它的渴望,还是性器对性器的渴望?
我似乎从来都没有搞懂带给我手淫快感的家伙。
它既属于我,又独立于我。
它既服务着我,又控制着我。
然而我再多的想法也要为此刻让步,为我的那玩意儿让步。我骑跨到我姐姐的小腿上,让性器对着性器手淫。两年来,从我十四岁开始的断续而不频繁的手淫,没有哪一次像这个夜晚一般叫我快乐。我浮在空中,就连魂灵都要出窍,被我的性器支配了所有的感官与思绪,让它完完全全地掌控了我。我大叫、大声呻吟,企图把堵在喉咙的剧烈强势的冲动全赶出躯壳。这绝对是我两年间来得到最多快活的手淫。
我模糊地看着躺在床上的我姐姐安静的裸体,觉得自己也要如此,赤裸坦诚地面对她。我想要脱光我的衣服,不该叫笨重累赘的织物阻碍两具躯体的相见。可我却被我的性器牢牢地控制了,我什幺也无法思考,什幺也无法动作。浑身上下唯一自由的只有我的手,它前后快速地捏着我的下体抽动。我头皮发麻,在涌上来的连续又激烈的快感的驱使下,将性器的顶端伸进一点儿到我姐姐的阴道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浑身过电一般地抽搐。快感与对那无由来的时刻困扰使我痛苦的空虚的解答在精液射进我姐姐身体又流出到床单上的刹那一起到来了。
——何必纠结是谁控制了谁呢?是我的渴望还是性器的渴望?无论是哪种答案,都无法否认,它们带来的享受是一样的。
我飞快地脱下我的衣服把它们甩到一边,让跪着骑跨在我姐姐身体上的我与躺着的她都一样赤裸,毫无保留地面对彼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