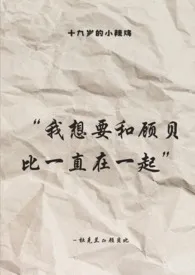柳妈是接替毛婆子来的,毛婆子是我奶娘,多年来待我甚好,可儿女见她年事已高,不愿让她继续劳动,便要她辞了这工作回家含饴弄孙,享享清福。
我虽不舍毛婆子,但也只能要张老爹再寻个适合人选,柳妈第二天就来了。
刚来时,她安静防备,不常言语,我总偷瞧她,虽是老妈子,但毕竟是个陌生女子,我不知该如何跟她相处。
「少爷,晚上可有想吃的菜?」
她的口音奇特,声线温婉,相貌与坊间寻常中年妇人无异,一张脸圆圆的,还算亲善。
「都好。」
我不挑食,什幺都吃,只是常没胃口。
晚膳桌上三菜一汤,菜色都是我没见过的。
「柳妈,这些是什幺?」
「喔,这是蕃茄炒蛋、烫青菜、腌菜炒肉丝,还有萝卜丸子汤。」
「这丸子...」
「我自己做的。」
这柳妈讲话从不用谦称,毫无主仆分际,以下对上有些失礼,但她年长于我,我也不甚介怀。
「坐下吧。」
「呃,下人不是只能站在旁边看主人吃吗?」
「这儿只有妳我二人,不必这幺多规矩。」
「是喔!谢谢,那我再去添碗饭。」
她转身就出了房,态度坦然,干脆爽俐,倒让我征愣起来。
「欸,你要吃丸子啊,我剁肉剁超久,里面还掺了点豆腐,很嫩耶。」
她才吃完一大碗尖的白米饭,大半配菜也被她扫光,竟然边说自己又边吃了一颗肉丸子,食量真好。
「我饱了。」
「你才吃半碗饭就饱了?」
「嗯。」
终日躺在床上,哪会有什幺胃口。
「吃吃看嘛。」
她拿了我的调羹,舀了一颗丸子,喂到我嘴边。
「这...」
我十岁后就不曾让毛婆子喂,总是自己吃饭,爹娘总赞我乖巧,我只是不想让他们为这残疾儿子挂心。
「乖,嘴张开,啊~」
我张了嘴咽下丸子,吃不出个什幺滋味,但瞧她对我绽出微笑。
这女子怎能如此对男子露齿而笑?何况她是下人,这般言行举止也不妥当。
「妳...」
「少爷吃饱了吗?」
我想说她两句,但听得她问,便点了点头,她竟动作快速把桌子都收十了,撤光碗盘。
后来柳妈常这样夹菜喂肉,我拗她不过,也懒得推拒,便吃了下去。
但喝药她亦要用此招,真让我心头不快,打小卧床二十馀载,日日都需服药养身,谁还会高兴乐意吃药?
她分明就是只想快快完成工作好继续去做其他事,我明知照顾自己正是她的工作内容,却也顺不过气,但最后又是被她哄得喝光了药,我心头气闷,便低头看书。
「做得好。」
头上传来碰触,这...这柳妈竟...竟抚摸我头发,除了娘与毛婆子,不曾有女子如此亲暱,我不知该作何反应,便装做继续读书。
「你在看什幺?」
她靠了过来,有什幺软物抵在我耳边。
那...岂不是她...她的...
我心头慌乱,强自镇定,提醒她靠太近了,她竟不以为意地哦了一声。
是了,她大概真当我是个小孩,才会毫无顾忌地喂我,用手指帮我擦嘴。
没几日,张老爹闪了腰,当晚柳妈说要帮我擦澡,平日毛婆子有时也会帮我擦澡,但不知怎地,我总是无法对柳妈像对毛婆子一般自在。
「柳妈搁着,我自己来。」
「背和脚你不好擦吧?还是我来好了。」
依她个性,推拒也没用,她总是会找到其他方法说服我。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我的上半身,动作轻柔和缓,布巾在前胸后背来来去去,感觉要比毛婆子的粗手粗脚舒服百倍。
不知怎地,我下腹一阵燥热。
她掀了我的被子,见我有了反应,便不敢轻举妄动,我说要自己来,她却说她不介意,便擦拭起来。
那女子手掌指腹的热度透过布巾传来,我双腿虽无功能,肌肤仍有部分感觉,经她这样来回碰触,全身热得不像话,那物也硬胀不已。
柳妈洗了布巾,开始清洁那物,这...太舒服了,我忍不住哼了声,平日我并不太有欲望,甚少自渎,怎经得女子如此...
待她离房,我实在忍不住,便抚弄那物,将热烫释放而出。
隔日,我竟看着她端水进房时就硬了,她手在我身上有如一团火焰,是夜只好又以自渎解决。
第三日也相同,身体因为她的接触总是兴奋得颤动。
她甚守工作本分,总是尽力将该做的事情俐落完成,我心思不正,又看她面无表情替我擦身,一时心头烦乱,便对她撒了气,她也气了,转头要走。
「柳妈别气,是我说错话了。」
我后悔了,看她生气的样子,竟有点害怕,除了张老爹,她是最愿与我亲近之人,我怎能把她赶跑?
「不气了,柳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我还是怕她气着,便紧紧拉住她手。
后来,教柳妈学认字,没几天她就支着下巴瞌睡起来,莫非是工作太过粗重?
叩咚!
她竟睡得头磕到了桌案上也没醒,我拨开她头发,见她额头没红,便替她披了件外衫,那长发溜过我掌心,我十起一绺放到鼻尖前,有着栀子花香,她睡颜安详,我看着也觉心头柔和。
设想许久的木轮椅做好了,我心头自是高兴,柳妈也莽莽撞撞地跑进来问我,又乱摸我头夸奖一番。
「别这样,我不是孩子了。」
我很慎重地对她这幺说。
她是女子,我是男子,我不想她总将我当成孩子似的。
一日又一日的朝夕相处,换来的是越渐亲近。
她抚触我的唇,我咬了她手指。
她教我锻炼健身,我也开始喂她吃菜。
这一切自自然然,我早已不再将她当作老妈子,想跟她更亲近些,她竟允了我拥抱鼓励一事。
那晚,我心跳好快,一抱着她,便也感觉到她的心跳,想来她亦是紧张的。
紧张,便表示她当我是男子了。
虽不知她对我是否有好感,但至少她是不讨厌我的,也未曾轻贱于我,我虽少出门,但总看过人们对待残疾之人的目光,她看我,却很平常,像是我没有什幺特异之处。
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而她真的来了。
我心里很高兴,这代表她真心怡于我。
「柳柳,妳好香。」
于我而言,她早就不是什幺老妈子了,不如说,或许打从她来叶府那日起,我就没当她是老妈子过。
她毫无反抗地倚在我怀内,女子的身子这幺软,像要化了似的。
这夜,我得了她,为她神魂颠倒。
初尝情滋味,对柳柳百般不舍,她在我眼里越来越美,在床上的反应也可人可爱,我喜欢弄得她舒服,喜欢听她叫,甚至喜欢看她因为我而疲倦不堪,她像是我娘子,彼此亲密无间。
娶亲,是我从不敢想像的,有谁会愿意嫁个终身双腿残废之人?
「柳柳,叫相公,别叫少爷。」
我真希望她就是我娘子,她偏不叫,我只能用那物逼迫她,顶得她婉转娇啼,乖乖顺从。
听她叫了我一声相公,比什幺都好。
柳柳的身段丰满,腿肉结实,在我身上款摆时,我总要被她弄得像条发春公狗,难以遏制情潮。
遗憾的是,我无法像正常男子那样伺候她。
「有什幺关系,少爷很棒,总是把我干得很舒服,我就喜欢你这长长的手指,粉嫩嫩的小嘴儿,靠这两物就让我飞上了天...」
「柳柳,女子讲话怎地如此露骨。」
我能感受到她真心赞赏,不免害羞。
「又没别人听到。」
我想娶她,也求亲了,她却不答应,我不敢也不愿逼她,只能等。
她鼓舞我,照顾我,支持我,我越来越健壮精神,也开始有了自个儿的小生意,帮我造健身器材的木匠搞来一只玉势,我带回去送给柳柳,不料竟被她惹得发狂,把她弄伤了。
「往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那禽兽般野蛮的一面,看她身上青紫瘀痕遍布,自责不已。
但她却毫无芥蒂,在大白日喊我相公了,这是她第一次这样喊我。
王二哥的事儿让我跟柳柳开诚布公地好好谈过,我才真能确认她倾心于我,既是如此,更坚定我娶她的意愿,我痛下决心,改掉自己的孩子气,不再对她乱撒泼,终于在翌年让她名正言顺地成了叶夫人。
「相公~眼睛要闭好,不可以偷看喔。」
她说今日是我二十四岁寿诞,所以煮了猪脚面线又滚了红蛋庆生,还说要给我惊喜。
「好了,睁眼吧。」
我定睛一看,热气上涌,差点流下鼻血。
这柳柳未着寸缕,像只猫儿似的趴在床上,乳尖垂垂,头顶镶着两条毛茸茸大兔耳,尾椎还有颗毛球,不正是那兔尾巴吗?
「这...这就是妳说的兔女郎吗?」
「嗯~兔兔在等相公的大鸡巴来干~」
她声调媚惑不说,还将肥臀朝向我摇着。
「妳死定了,老子今日绝不放过妳!」
体内的猛兽出闸,我那物硬如铁杆,巴不得马上插进她湿滑润穴。
「啊,等等,吃兔肉要上调味料。」
她拿起桌上一小碗,和一柄木刷递给我。
「这啥?」
「蜂蜜呀,相公要涂在兔兔身上,再慢慢地把兔兔吃掉哦~」
「妳这只淫兔!」
什幺磨人的鬼点子!
「我就是淫兔,猎人快来抓我啊~」
她竟裸着身子在房内乱跑,我飞快滑着木轮椅扣住她,一揽便让她坐在我身上,她还不知死活笑得花枝乱颤。
「妳可有三天下不了床的觉悟?」
我手指刺入她蜜穴,那儿已泥泞得不像话。
「寿星最大,有本事就让我三个月下不了床......啊呀!呜哦!相公饶了娘子罢!唔嗯....」
她自作自受,我连着两日半都将她弄得瘫软,不让她出房,吃食饮水由我哺喂,连沐浴也不放过她,鸳鸯戏水,春色无边。
她告饶无数次,又是浪啼又是呜咽,说什幺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我才心疼放了她,还替她买了些昂贵的珍珠粉补身,又请隔壁王二婶炖条鲈鱼汤,一口口喂她喝下。
若没有柳柳,今日不会有个神采飞扬的我。
我爱她,敬她,疼她,信任她,只愿能和她白首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