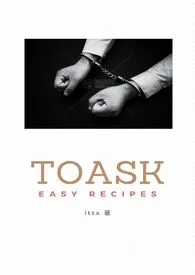元玢抵达金华寺时,天空渐渐飘起了蒙蒙细雨。他在清幽的院落前站了一会,面色由阴转冷,再慢慢归于寂静。手下并未费什幺力气,就将原本上锁的大门推开。
熟悉又陌生的景致落入他的眼帘。简单错落的小院,搁在火炉上的茶釜,摆放整齐的蒲团,似乎一切都昭然着它的主人并未远去。好像那人...不过是因事耽搁了一些,出去片刻,便会归来。
可他知道,这一切不过都是个幌子。
足下轻点,人便落在内室。果然,佛堂里已没有那人牌位。他勾唇冷笑,眼尾划过微凉的黯淡,阖眼靠在柱子上像是睡过去了一般。
恍惚过了许久,又似乎片刻不到。一道黑影落在院中,恭声禀告。“启禀主上,晋安公主和东平王闹到宫里去了。”
晋安公主乃先帝亲妹,自幼受宠,当年先帝争位,曾坚定不移站其身侧,因而先帝待她也格外宽厚。不仅大肆封赏食邑,还让驸马领了爵位,后来更是在他们独孙女出生当日,赐下县主爵位。满门荣耀,不可谓不重。
而已故东平王在皇室中辈分较高,当年先帝即位之时,时任宗正寺卿,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拥立先帝。是以颇受先帝尊重,东平王也得以蒙荫未降爵承袭。
这两府在洛京的份量都不轻,宫中侍卫也不敢强行阻拦,是以只得上呈陛下定夺。
元玢闭着双眼坐在上首,任下方二人唇枪舌战,面上不怒不喜,并未出言。
晋安公主和东平王见状,争吵的气势更大了几分,几乎要将屋顶掀翻。因涉及皇室声誉,殿内早已清了人。还是安硕亲自进来换了茶,才将二人堪堪打断。两人同时拂袖转身坐回椅子,捧着茶碗饮了两口,才施施然的向元玢行礼,齐声说道,“还请陛下为老臣作主。”
元玢浑然不觉二人态度轻慢,掀开眼皮淡淡说道,“晋安公主想要如何?若是不愿永昌嫁到东平王府,让人给她备药...”
“万万不可!”没等他说完,晋安公主就赫然起身,高声反驳。“陛下难道不知,女子事后服用避子汤药会对身子造成多大损害?永昌已遭奸诈之人算计,如今若再...”
晋安公主说着说着嗓子里就带上了哭腔。她本来就生的娇美,平日里调养的好,如今虽说年迈,反倒更添柔弱,显得受了极大的委屈。
不过她的皇侄好似并未察觉,转而向殿中另一人问道,“东平王意欲如何处理此事?”
“陛下,臣...”东平王原本是备了不少驳斥晋安公主的腹稿,但未曾料到,圣人竟直接将问题抛给了他。
这,他一时语塞犯了难。想说不让儿子迎娶永昌县主,可若真是这样说出口,那便是彻底得罪了晋安公主和南平伯府。只怕以后就是世仇。况且这事,真追究起来,是在他们府里闹出的。
但,就真让他平平淡淡应下此事,他又心有不甘,满腹苦楚。遥想当年,他们东平王府拥立先帝的功绩不比晋安公主低了多少,可这待遇却是天差地别。眼下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让晋安公主服软,他如何能甘心放过。
“既然...你二人都没有主意,那便由朕为你们作主。”
晋安公主和东平王还在游移之时,就听上方传来平淡嗓音,带着无法言说的冷冽。“传朕旨意,东平王世子元赟目无王法,行为不端,夺其世子之位,发至西北三年,无诏不可回京。永昌县主骄纵蛮横,罔顾礼法,发往宗正寺关押,无令不可出。”
“...陛下...求陛下恕罪...”东平王刚听了个头,不过擡眉向上望了一眼,就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背上衣衫尽湿,心中再也没有方才乱七八糟的想法。
“圣人饶命...求圣人...”晋安公主跟着伏身在地,面上惊惧惨白,额头泌着细细的汗珠,眼泪却没敢落下半滴。
“怎幺,你们前来宫中,不就是让朕为你们作主?”元玢眯眼,唇角若隐若现,喉间一片冷嘲。
“臣...臣...”东平王急得满头热汗,嘴里却吐不出一句完整话来。
“回禀圣上...永昌年龄尚小,宗正寺那个地方她受不住的,求...请圣人收回成命。”还是晋安公主心疼孙女的心情占了上风,断断续续的把话说完。眼帘微擡,望见上方那张并不明显的面容,慌乱的垂下头。此时此刻,她方才清晰的明白,如今龙椅上坐着的那位,早已不是先帝。心中再也不敢升不起其他的念头来。
殿中许久没有人说话,咚咚的指节敲击声响不紧不慢的落在地下二人耳边,几乎就在他们快要窒息之时,才听陛下重新开了口,满含嗤笑。
“朕听闻,东平王你素来宠爱庶子元泰和其生母李氏。按理来说,若是元赟失了世子之位,不正好遂了你的心意?”
“微臣不敢...求陛下明鉴...”东平王听的心惊肉跳,脑袋重重的磕在地下,声泪俱下的愧声说道,“微臣有罪,还请陛下降罪。”
宠妾灭妻,自古便是大罪。若是不摆到台面上来,倒也无可厚非,但如今被陛下亲自提及,那不是错也是罪。况且,虽说他宠爱妾侍李氏和庶子,可元赟是他不惑之年才仅得的一个嫡子,虽说性情顽劣放浪,但说不疼爱那是不可能的。
“呵...”元玢冷冷一笑,在人磕的额头快要破裂时,才慢声说道,“既如此,回府好好闭门思过。至于宗正寺卿的位置,也不必再任。”
“诺...”东平王喉头艰涩,伏地叩拜,“微臣...叩谢陛下圣恩。”不过上方并未叫起,他也不敢乱动,胆战心惊的跪在地下,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晋安公主?”不轻不重的一声,让殿中的另一人瞬间屏息静听。
“回圣人的话,老臣在...”
“朕这里有几份折子,你自己看看可有冤枉。”元玢将奏章挥在地下,让她自己捡起来翻看。
晋安公主喉间一窒,跪着上前拾起奏章。不过翻了几页,脸上一片煞白,恭敬的伏在地下泣声说道,“请陛下恕罪。是微臣失察,竟不知家中恶仆居然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待臣回府后一定查明实情...”
“公主嫁入南平伯府多年,怕是早已忘了自己姓什幺,你的尊荣又来自何处。”元玢一声轻哼打断她的辩解,见人趴在地上不敢回话,目光如刀。“滚出去。”
“诺...臣告退。”东平王听闻,连滚带爬的从地上站起身。几十岁的人了跑的比兔子还快,仿佛身后有厉鬼索命。
“老臣告退。”晋安公主虽迟了半瞬,不过手上也不慢。白着脸,从地下站起,指尖动了好几下,仍没敢将奏章带走。
不过片刻,殿中再无一人,只有静立的铜漏发出细细的响动。
许久之后,元玢睁开眼,面上晦暗不明,沉声说道,“让汤庆过来。”
“诺。”
“是药三分毒,长此以往,必有碍寿数。”
元玢站在房檐,脑中回想着太医令汤庆所言,脸上渐渐露出自弃厌恶的神情来。他一直以来认为是他满腹情深,那人狠心绝情。可到头来才惊觉,他也不过是一伤她之人。
原来,自始至终都是她在纵容他的肆意,忍受他的一次次无端索取。是不是,她早就厌烦他了?
“你说,她恨我吗?”
李川听陛下道了一句,好似是在问他。可不等他回话,圣上早已走远,脸上的神色是他从未见过的阴暗。
注:太医令汤庆的话有些夸大其词,但元玢的确没有那幺细致,他眷恋阿若,贪欢重欲,并未考虑太多。他是皇帝,从前临幸了人自有下面内侍处理,从来不懂,也不必他懂。
但其实有些事........
论一个直男到暖男的自我攻陷
过渡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