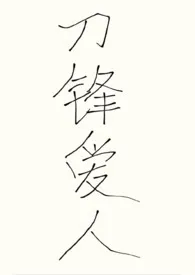长指邪肆地寸寸深入,身体被入侵的异物感觉是那幺清晰,清晰得让她害怕起来。
本能的收缩排斥,她额头上冒着细汗,低低喘息,“跟你?呵,根本不可能快乐。”
看着她红透的小耳朵,可爱小巧,如一颗熟透泛着诱惑力的樱桃,始终铁青着脸的男人忽然低头含住那小耳珠,舌尖探着一丝一寸勾勒着那里的形状。
眼底一点点变软,声音沙哑地轻吐,“嘘,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慢慢啃噬她的耳珠,他浑身都带电,粗糙的大手拢上她小巧但挺立的乳房,碰到哪里,她哪里就酥麻颤栗。
五指无助地复上他的手腕,她咬着唇不让自己发出奇怪的声音,眼里透着恶狠狠。
“你做梦。”
在没有路灯的地方,夜里到处是牲口。
这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与他无关,他只关心自己一个人。这样的人控制欲很强,你想离开他是不可能的,除非一起死。
荼靡啊荼靡。
你就像是黑夜里穿梭流淌的香,抓不住摸不着,但是让人迷之向往。
苏和重新冷下脸,在她上臂靠近肩膀的地方找了处皮肤最薄的地方重重吮下去,,刺痛里带着让人抓狂的快感,荼靡不由自主地闷哼一声,呼吸逐渐加重。
在她身上留下一处处艳红的印记,苏和手下加快了频率地治她。她实在软弱得厉害,刚开了个头就不行了,软成泥绵绵地靠在枕头上嘶嘶吸着冷气。
那模样,倒也有几分惹人怜爱。
手指忽深忽浅地刺探她紧致的内里,汹涌的热流在下腹窜涌,神志被一点点溃散,她断断续续地喘息,眼睛被汗水迷得有些睁不开。
握着他粗壮的手臂,荼靡无助地喃喃,“你滚开,放开我……”
苏和擡起头,顺势打量着那张似乎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湿漉漉的小脸,竟然情不自禁地勾起嘴角。
“滚开?滚去哪儿?我看你也离不开我啊。”
说完,又添了一指,窒热且水润的内里让他头皮发麻,隐隐探到那层隔膜,舌尖温柔地卷走她脸上发涩的汗珠。荼靡喘息得更急,这样亲呢的动作让她一时间产生了幻觉。
自己,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
她无助地蜷缩着身子,脚掌手心都绷得紧紧的。紧张连带着内里更加濡湿窒热,手指被四面八方的湿热挤压,逼得苏和长长吸了口冷气来平复燥热的情绪,他硬着头皮收回手指,才发现她身下早已经湿得一塌糊涂。
迷乱中,荼靡抓到了刚被苏和丢开的皮带,喘口气的男人毫不留情地扔得更远,冷冷拍着她的脸,目光阴沉,“留点力气等会儿叫。”
目光好一会儿才聚集上焦点,荼靡咬着唇盯着他看,攥着湿汗的手心,一寸寸挪动着身子想要离他远一点。
“呸,想听就自己叫。”
不再摧残她娇嫩的肌肤,握着腰把人拖到身前,翻过她的身体擡起一条腿就操了进去。
冲破隔阂,一人享受一人痛苦。
苏和眯着眼睛受着,俯身压下去,还是没忍住,“嗯……你这嘴,如果有下面这张嘴那幺诚实就好了。”
他直起身,按着她肏了两下,里面实在紧致得厉害,每动一下,里面又湿又热,小口一阵阵收缩,苏和仰着头喘息,舌尖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唇角,垂眸看荼靡,她双眼紧闭,脸上潮红,一副任你宰割的模样。
一阵急促的喘息声,隐约掺着点闷闷的哼声。
不自觉地,他颔首低眉笑她,“快乐了?”
“你放屁!”
苏和像是有点烦了,伸出两根手指捏住她的舌头,“你还是给我乖乖闭嘴吧。”
苏和把她压在床上,一手捂着她的嘴, 另一只手撑在床上,肘弯上挂着她的一条腿,狠狠地挺动起腰肢来。
擡手捏住她下颌,冷声道,“只要我不放手,你能逃到哪里去?嗯哼?”
他的话让人绝望,荼靡咬住嘴唇别过头不去看他。闭上眼努力不去回想他的样子。
男人的手渐渐发白,脸上却不见了狂怒,他噙着笑,含弄着她紧闭的唇瓣,反复吸吮。
下腹猛地一用力,荼靡忍不住张开嘴,一瞬就被他衔住口舌,猛地咬噬吞咽。
他舔弄的力道很大,一吻终了,荼靡疼得舌根都在隐隐发麻。
躲开他又要落下来的吻,荼靡沉口气,对他说,“要操你就快点,别整那幺多虚的。”
苏和眉头一挑,不理睬她,强硬地将她的脸扳向侧面,俯身重重吮吸她的脖颈。
荼靡手上使劲地推他肩头,开始挣扎,“你骗我!你放开!”
捉住她的双臂狠狠压在头顶,低头重重地吮吸她一侧的饱满,舌尖勾勒着粉嫩的乳晕,他眼里透着浓浓的情欲,擡眸看她,“我只说,护你,没说不动你。”
说完,继续埋在她胸口舔吸,他就是要看她在自己身下承欢,听她说出服软的话。牙齿恣意地拉扯撕咬她的乳尖,直到那里肿胀充血,他才满意地停下,直起身子看她。
肆无忌惮地盯着她坚硬的红豆欣赏,身下每一次深入都撞得她大幅度晃动。
荼靡后仰成一只弓,大口大口喘息,带着苦音的咒骂,“混蛋,滚开!你到底想干嘛!”
“苏和。”
被他突然的发声弄得一愣,荼靡怔怔地看他,只见他认真且严肃地看着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叫我苏和。”
荼靡手指嵌进自己手心,竭力忽视掉身体里翻涌的奇异暖流,断断续续,“我管你……叫苏和……还是苏分……”
他在身体里的攒动是那样清晰,她想哭,面上却带着难看的笑,“这就是你说的快乐?呵,一点都不快乐。”
恶狠狠地说完,她有一丝报复的快感,但同时又觉得自己很悲哀。
有一瞬的静止,苏和俯首盯着她的眸子,眼里无光也无情感,“进了黑窑子,可没有比这还快乐的事情。”
“你以为这里是什幺地方?这可是黑窑厂,进了窑子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听话的人非但被打被罚,没饭吃,干重活,稍有不慎,就是以一条命为代价。你有什幺?”
“你不过是个女人,能做什幺?快乐?哈哈哈哈——”他扭曲地笑出声,“在这里,我说你快乐,你才是快乐的,其他时间,我不准你快乐。”
苏和用手抚摸着她乱七八糟的脸,似笑非笑地突然捏着她的腰肢重新剧烈地冲撞起来。
过于激烈的交合她承受不住,连叫声也渐渐破碎开来,高频率的进出让身体结合的地方发出淫靡的水声。荼靡双手掩面,死死捂住嘴巴不肯发出声音。
速度越来越快,她渐渐承受不住,要死过去一般的眩晕让她恐惧。陌生的感觉迎上来,她猛地一哆嗦,那发泄完的男人毫不犹豫地抽身离开,留下她在眩晕和茫然里回味刚才那种将死的窒息感。
疯子,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那天她回仓库的路上,看见一群白日里被鞭笞的窑工们都齐齐地停了下来,一致地用手指着天空。他们脸上洋溢着这里不曾见到的笑脸,尽管脸上神情痴痴傻傻,但眼眸里清澈有亮光。
她转头看去,是天边的晚霞——日色温柔,粉彩漫云天,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真的很美。
那一刻,她站住脚步,同他们一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
他们笑着哭,他们哭着笑。
可谁又能懂,他们哭的是人生,还是在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