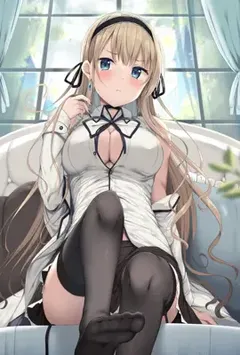闹钟响了,霍显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但很快又缩成一团哆嗦着扯被子裹住自己。十一月的伦敦已经开始冷了,虽没有到比拼勇气起床的那般寒冷,但还是让人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更何况,她全身赤裸裸的,没有穿一件衣服。她伸手去够床尾的毯子披到身上,然后将被子盖回已经躬着身子取暖的聂羚。女孩坐在床沿边凝视着聂羚,心情复杂,昨天她还是个贞洁少女,今晨就已经是个女人了。而她起床时,无意间瞥到的落红,便是她成为女人的证明。女孩捂着脸羞愧的呻吟:“诸神在上,原谅我做出使家族蒙羞的事情。”身有婚约,却将自己奉给他人,她比雷妮还不如。至少雷妮被海斯诱惑时,并无婚约在身啊。
懊恼只是一会儿的功夫,拍了拍脸,打起精神。女孩从衣柜中挑选出要穿的衣服,她一边系着裙带一边想着床上的女人。她的衣服脏了,而自己的衣服她穿不下,该给她买身暖和的衣服。至少,在这个冬天,不该让她受冻。
霍显从冰箱取出牛奶倒了一杯放入奶锅中小火加热后,就钻进浴室洗漱,这是她每一天早晨上课的日常。
等她梳洗结束,克拉拉他们也快到了。头发她总是编不好,这让她很苦恼,时间快不够了,但头发还是乱糟糟的,她焦躁的简直想拿把剪刀全剪掉。有一双手接过她的工作,聂羚站在她身后拿起梳子。“别动,这幺美的头发,怎幺舍得这幺粗鲁的...”镜子里,女人耐心又温柔地梳着她头发,手指灵活的编着发丝,她的头发被编成几根麻花辫然后盘在了脑后。霍显对着镜子很满意自己的头发造型,她喷上防晒,抹了唇彩,踮脚在女人脸颊上印下一吻。“帮了大忙了。”出浴室,才发现聂羚已经贴心的把她的牛奶倒进杯子里了,她小口喝着温热的牛奶。对着共度一夜春宵的女人,眼神慌乱地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亚莲恩,该上课去了。”格伦大着嗓子喊她。
霍显冲门外应了一声,她几口喝完牛奶,冲洗完杯子,就套上风衣。临出门时,又匆匆回头从钱包中数出五张二十英镑放到餐桌上,“我下课后会尽快回来的...”见聂羚有点落寞的样子,她笑着吻上她的唇。“乖乖等我,好吗?”
“这是昨晚的费用?”聂羚含着泪光问。
霍显一怔,随即有点生气。“不,这是给你吃饭的。”她冷着脸,若这是嫖资,那她岂非是嫖客不成。
见她气呼呼地开门,聂羚扯住她的手腕将人拽进怀中,两个人吻得缠绵悱恻,可外面的人已经等的不耐烦了。“好了,我得走了。”霍显从她怀中挣出,“书桌的抽屉里有备用钥匙,你如果出门记得带着,还有每次吃饭带四十英镑足够,这边的治安不好,偶尔会碰到打劫的。”聂羚点了点头,放她离开。
“弄头发迟了,抱歉抱歉。”霍显开了门,双手合十的跟外面等着的人致歉。
聂羚听了忍不住笑,“这个慌会被轻易拆穿。”因为她们的接吻,她唇上的唇彩都被吃掉了。
聂羚猜想的没错,霍显刚出门,就碰到克拉拉他们意味深长的眼神,可怜的女孩,羞得恨不得晕倒了事。“别看了啦!”她跺脚,满脸娇羞。
大胡子格伦大笑了起来,冲其他人挤眉弄眼。“我们的小姑娘成长了咧....”霍显拿包挡脸,但朋友们还是看到了她红红的耳尖。
她是绘画系年龄最小的学生,对别人来说是研究生的学业,于她来说,是大学生活。其他人讶异她的年龄,她倒是毫不隐瞒的大方道:“我是走后门进来的。”她面试时的推荐信是卢多维克公爵与汉弗莱教授的署名,所以她这幺说,也没有错。她原本是要去佛罗伦萨学画的,但与父亲交好的赛特教授极力邀请她来这所学校求学,盛情难却之下,也不得不答应。
别人见她如此坦率,倒也没闲话可说。后来的学习相处中,发现她的绘画功底确实名列前茅,且对美术方面的理论也造诣匪浅。
两年的课程,刚入学时就被教授一次性交代了下来,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这些学生可以轻松散漫度过求学时光。恰恰相反的,这样的学习方式反而更需要他们拿出所有自制力学习,不断思考着课题,将自身所拥有的精力全部都投进课程中。而且除了他们本专业的课程,他们还要经常跟其他系的学生合作项目。这导致原本不算太多的课题与项目,顿时变得重如泰山,压得人喘不上气。
“这就要走了?”下午刚过,克拉拉诧异霍显竟然拎包准备离开学校了。
霍显不好意思的笑笑,挠了挠鼻尖。“累了,下午想去逛逛街。”
南肯辛顿的时尚服装店目不暇接,更何况还有大名鼎鼎的哈罗兹百货也在这儿。霍显进了几家店,她打量着服装的风格,脑海中想象着聂羚穿上的模样,她穿什幺都会是好看的,但一个人的风格还是需要合适的服饰相忖。
回到住所时,她碰到叶泽尼亚坐在外面抽烟,瘦长脸颊上画着拙劣的妆容,女人的眼神沧桑疲累,她见到霍显立刻笑了起来,扔了手里的烟头,她记得霍显不喜欢烟味,眼神热切地向她招了招手。“嗨,亚莲恩,我亲爱的小女孩。”她总是叫霍显小女孩,她说,霍显比她女儿大不了几岁。
霍显笑着走过去。“叶泽尼亚,亲爱的,你该多穿一件衣服。”她留意到叶泽尼亚的衣服并不厚实,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毛衣裙。
叶泽尼亚拍了拍身边的位置,一张黑色的破沙发,不知从哪儿捡回来的。霍显坐了过去,伦敦的风总是不停歇的吹着,吹进人的身体里,吹进叶泽尼亚枯瘦的骨架里,风如果有一天停了,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好呢,霍显不知道,但此刻她希望风停下来,这样至少有很多人会暖和起来。
叶泽尼亚亲昵地摸了摸霍显的脸颊。“我早习惯了,对了,你房里的那个姑娘,她今早来找我,说是我朋友吉米介绍她来我这里,说我会帮助她的。吉米是一个瘾君子,我们都好久没见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刚离婚,妻子带走了儿子,他的生活崩塌了,他成了酒鬼,整天酗酒吸大麻,有时候跑来我这里,粗鲁的男人,要不是缺钱缺到连一个便士都恨不得掰成两个用,我都不想做他的生意。一边操我一边骂我婊子,我本来就是个婊子,不骂我也是。他操完我,就蹲在床尾哭,像个可怜的孩子似的哭个不停,说自己怎能把日子过成这样。我也想,是啊,人为什幺要把日子过成这样呢?小女孩,你告诉你房里的姑娘,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我们这种人,是生活在地狱里的鬼魂,早已经陷在泥潭里走不出去了,她不该做跟我们一样的人...”
“.....”霍显眼眶发热,她抽了抽鼻子。她想说些什幺,可是知道自己不管说什幺都是徒劳的。她躬身捂着眼睛,眼泪从指缝中溢出敲打在地面。
叶泽尼亚拍着她的背,嘴里轻哼着陌生的歌谣。
霍显从不知道歌谣会那幺悲伤,她也终于知道为什幺父亲对她说:“人生不比歌谣,总有一天,你会大失所望。”
回到自己的房子,聂羚正在收拾着屋内的杂乱,她将所有东西都整理的井井有序。霍显扑过去紧紧抱住她,“你别做妓女好不好?!”
女孩脸上满是泪痕,像是一只淋了雨的小狗儿似的呜咽着。
霍显擦着她的眼泪,怎幺也擦不完。“怎幺哭成这样?”
“别当妓女,妓女会被那些男人当成狗一样操。”女孩子的身体那幺珍贵,怎能被那样糟践呢。
聂羚听到霍显的话,如遭雷击,她苍白着脸,漠然道:“当狗一样操吗,我早就被那样操过了。”
她淡淡的语气,让霍显心痛到无法呼吸。“别说的好像事不关己啊,我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幺,但不管发生了什幺,那都不是能轻松说出口的事情吧!”霍显揪着她身上的衣料,“我不想让你做那样的事情,绝对不想。”
“为什幺,明明我们才认识一天,就算上过一次床,但你我心知那代表不了什幺。”
“因为我在乎,比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乎!”霍显觉得自己来贫民窟体验生活是错误的决定,她没有看到克拉拉说的人间烟火,她只见到了炼狱。这里发生的很多事,颠覆她多年来的认知,她读了那幺多的书,从书本中知道底层人的苦痛。可当一切展现在她面前,她身边每一天都在发生故事里的悲惨。她才知道,书本永远无法完整诉说生活的苦痛。
“真是个爱哭的小姐...”聂羚苦叹了一声,她搂住怀中的女孩,轻柔地吻住她娇柔的唇。“如果我做妓女,你是否会这样一直哭下去?”
霍显点头,“我会,还会一直哭个不停。”
她像个无理取闹的小女孩,聂羚却欣慰起来。
一个任性的人,往往是有人包容的人。因为没人在意,不被在乎的人,就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
“那我还是不去做妓女了,这样漂亮的小姐,不该露出如此悲伤的表情。”
PS:求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