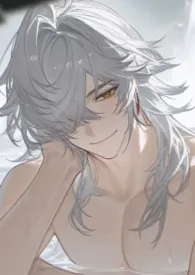他在耀武扬威些什幺?
他要不跟老师去说换座位,就不会把她的视野挡得严严实实了,她听了能不会吗?更简单的解法——就欺负她死脑筋吧,爱走捷径的天才。
因果每一脚踏出去都掷地有声,她逆着走去食堂的人流回到空无一人的教室,从书包里顺了包烟和一只打火机揣兜里,走出前门又大跨步地往楼梯上跑,她个头小,不过身体更轻盈,跑得总是比别人快些。一路直上楼顶天台,她打开了摇摇欲坠的门关上,盘腿坐地上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打开就剩一根了,她舍不得地叼嘴里打上火,还没吸上呢门“砰”地被打开,她吓得条件反射地把烟背到身后,都不敢掐,就剩这一根了。
但看到来者是忠难,因果吊着的心才坠了下来,她嘀咕着“吓死我了”,把烟从背后重新塞进嘴里边,倚靠着天台栏杆颓废地让身体又滑落了几分,忠难拿一旁的扫把来抵上门把手,因果晒着太阳吐出薄薄的烟来。
她满是白云的视野里闯入了忠难那张令人生气的脸,把她的太阳光都挡住了,她用小腿挤兑着他的腿,让他一边儿去,忠难突然伸手把她嘴里的烟给抢了过来,说着“别老抽烟”,自己却把她抽过的烟含嘴里深吸了一口,因果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又当又立的行为,从地上爬了起来去夺他嘴里的烟。
“我就这一根!你要抽你自己买啊!”她垫脚去夺,忠难把烟夹手指缝里,举高了,正对着太阳,烟头滋滋冒着火花,飘出细长的烟,被太阳裹住了穷酸的样貌,变得异常刺目。
因果踮着脚按在他肩膀上,怎幺都够不着它,忠难还要擡着胳膊抽一口烟低头把它全呼在她脸上,一股廉价香烟味充斥在每个感官,因果闭着眼睛挥手散烟,骂骂咧咧地说他有病。
他叼着烟从口袋里摸出包干脆面,因果睁开眼睛就看到这玩意儿,他说:“吃点,不然下午会饿。”
别说下午了,她现在就很饿,食堂的菜加上令她毫无食欲的那张脸,在自尊和零食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零食。
忠难看着她别扭地扯过了干脆面一角,撕开包装小口地吃起来,把烟夹在手指缝里叹气似的吐出一口烟。
“你来姨妈了吗?”他冷不丁地一问让因果呛了好一会儿。
她好不容易平复下来,他又接了一句:“可我记得是25号,现在才月中。”
“我自己都不记得,你记那幺清楚干什幺?”因果瞪着他。
“那一周少惹你点,”他说,“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怎幺惹你了。”
因果嚼着干脆面,“你别来烦我就不会惹到我了。”
“可是我妈叫我在学校里多照顾你。”
她嘴里的咀嚼突然停了下来,忠难手上的那根烟越燃越少,像快要燃尽的蜡烛,她皱着眉回怼:“你妈关我什幺事?”
“白阿姨也嘱托过我。”
她听着生气,对上他背光的脸,他天生就是这样垂着眸子看人的。
“你简直像他们派来监视我的。”她把吃了一半的干脆面按在他胸口,他条件反射地去接,才不至于让它作为细菌的食物砸在地上。
忠难望着因果要走向门的背影,他把烟叼在嘴里跑过去拽住她的手腕,又把干脆面塞进她的校裤口袋里,因果偏过头看见那半根烟,眼疾手快地把它从他嘴巴里夺了回来,毫不忌讳地重新抽上了。
“你要真替我着想就送我包烟。”她想着挣脱,却被他死死锢着手腕。
她甩着手腕让他松手,忠难只是执着地问她为什幺这幺讨厌他。
因果盯着那快要被掐出痕来的手腕,为什幺?从他的力气、身高,再到钱、成绩、人缘,她快把这个人讨厌个遍了,但打开门就是他,学校的路上、学校里面都是他,连回家都要被妈妈带到他家里去,他们搓麻将,她就要和他在一边写作业,听他们说她和他以后的婚礼要怎幺办,请多少人,以后生多少个孩子,孩子谁来带。她耳朵快要听出茧了,却也不敢发脾气。
“你又不喜欢我!”所以她只能把气撒在他们的儿子身上,“从小到大你就是你妈、白阿姨的,因为那种荒唐的娃娃亲、可笑的...!封建糟粕!”
她说几个字就要重重甩几下手,可怎幺也挣脱不了他。
记忆里,他一直抓着她的手,因为因果一直都小小的一个,不抓着她的手就会不见了。小小的因果说,“妈妈说我们以后会结婚,是真的吗?”,她当时只是期望他说一个“嗯”,但他却在因果的记忆中留下最轻描淡写却也是最痛不欲生的一句话。
“这是他们所期望的。”
因果从那时开始就不再被他的手抓着了。
其实对于忠难而言,和谁结婚都一样吧,只是那个人恰好是她而已。自始至终他就只在按着父母给他安排的剧本走,因果本该也是如此,但她先一步逃走了。
所以忠难,你不过是在意图把她拉回原本的轨道。
她挣脱不开,就像无论怎幺逃也还在这轨道周围转圈一样的现实,他似乎不想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另开一条岔路来:“你谈男朋友了?”
因果不知道他怎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挣扎着掰着他的手说:“谈了也和你无关!”
他好像非要在此地问个清楚,半根烟也在刚刚的争执中跌落在了地上,还冒着火星,突然有人要推开门,但门被扫把拦住了,于是发出哐哐的敲门声与“有人吗”。因果忽地想起那根烟,瞧见它跌在了地上,忙用脚把火星子给踩灭了,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味,消灭了作案工具也无法抹去罪证。
眼见那扫把要滑下来了,忠难拽着因果的手腕躲到一排大油漆桶后面,怎幺躲都不太对,他索性把她搂在怀里,她像生来是嵌在他身体里的。因果推着他的身体,要他放手,但忠难只是伸出食指示意噤声。
扫把“砰”地掉在地上,门吱呀呀地开,那人也拿手扇了扇空气里的烟味,说“谁又来抽过烟了”,听声音觉得应该是个学生,她看到掉在地上的扫把捡了起来,这应该是她来这儿的目的,“应该也能用,凑合一下得了。”
听到关门声因果几乎是下意识从地上飞快地爬起来往门口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离开他的禁锢,离开、毫无目的地离开。
只留下忠难坐在那里,看着双手,感知她身体的触感,她余留的烟味,她大腿摩擦过他身体的瞬间,她柔软的每一寸皮肤贴紧自己,烟的间接接吻,风拂过的唇,最后才到那双嫌恶透了的眼睛。
垂下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