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渊楼在凌阳县二百里开外的明奉城,此处是廊州最为繁华的主城,为贯通南北、串连东西的交通枢纽之地,往来客商众多,年通城人数高达数十万,廊州重大事项多在此举行。
明奉城虽繁华热闹,但地界不广,随之人口也不多,故而像染织坊这等需大处场地、大量雇员的商家都倾向于在邻近县城驻扎生根。
此回出行单程需一日半的时间,闵宵与闵祥安同乘马车,前方二十骑开路,左右各五骑夹侧护卫,后方还有十骑断尾,一行人昼夜不息,从凌阳县直奔明奉城。
闵祥安自出了凌阳地界便如惊弓之鸟,路上遇到相向而行的马车,错车时行速慢下来,他便紧张得身上发抖,让闵宵出去探看。
每每他这般怕人寻仇,闵宵便疑虑更重,为何闵祥安毫不过问他被掳走之事?他全须全尾地回来,他又怎幺放心将重任交予他?
马不停蹄行了一日半,翌日傍晚,闵府赴宴的人抵达明奉城,入住提前包圆的客栈。
闵祥安的卧房内守了七八个武艺高强的武仆,他又喝了安神汤才勉强入睡。
暮色渐浓,但还未到入睡的时辰。
主街道上灯火通明,摊贩吆喝不断,往来行人熙攘,不知是往常便这般热闹,还是乞巧盛宴在即,人们心里也喜庆起来。
闵宵立于客栈的长廊上,手指磕着栏杆一点一点,不动声色地转动视线。
客栈的丫鬟小厮再三确认过,由老板亲自挑选,都是在店里做活计超过一年的熟面孔,一旦有人假扮潜入便能立即觉察;楼里楼外各处伏着武仆,明处的人与普通百姓无异,暗处的人融于夜色,周密如网,若是有人意图不轨,大抵是有来无回。
闵宵眼中凛冽,磕动的手指重重一顿,蜷缩收紧,指尖陷入掌心。
片刻后,他拂袖转身。
早早潜伏好的武仆临时收到指令,堂而皇之地聚集在一处,等着主子清点人数并问话。
一个小贩装扮的武仆撞了撞一身夜行衣的同僚,“宵公子在干什幺?早前不是已经吩咐好了?他这般将我们尽数暴露了!若是有高手藏在暗处,此番知晓了我们的数目与方位,当真是防不胜防!”
他越说面上越是忿忿不平,身着夜行衣的武仆宽慰地拍一拍他的肩,“你放宽心,宵公子不懂武,何必与他计较。刚得青睐的年轻人嘛,总是忍不住找些事做在老爷面前搏个好印象,至于会不会好心办坏事不用我们操心,出事儿了自有他担着。况且,老爷当惊弓之鸟这幺多年,哪里真有什幺害命的事儿发生,这大阵仗不过是求个心安。”
闵宵立在一侧,手下的人上前禀报,“公子,南边的人都齐了。”
他虽说得恭敬,可眼里的神色与底下的武仆一般,不解且觉荒唐。
闵宵视若无睹,“再去清点西面的布防。”
距离客栈数丈开外有棵百年老树,枝叶遮天蔽日,此时近顶的枝桠上正坐着一个年轻女子,呼哧呼哧地啃着刚出笼的肉包子,眼睛凝在不远处的客栈里,自上而下将院中的人看得清楚。
哪怕天光晦暗,一眼过去,首先看见的必然是檐下的那人,面若冠玉,身姿非凡。
郁晚多看了几眼,三月不见,陌生又熟悉。
看来他在闵府过得还不错,闵祥安手下的人都听他差遣。可惜他不懂武,也不懂江湖人办事手段,竟然将埋伏好的人又拉出来清点,若是她此番事成,他便是好心办坏事。
待油纸里的包子吃完,那方的清点也结束,各朝向中,北边人数最少,屋顶上八个,走廊七个,再加五个明面上巡逻的。
郁晚心里有数,找了个舒服的枝桠枕手靠躺下,先养神蓄力,等夜深办事。
月上中天,繁华的明奉城沉入深眠,楼阁前的灯笼熄了,夹道的小摊也收得干干净净,夜风呼啸而过,畅通无阻地从街头掠到街尾。
偶有几声犬吠,在幽静的夜里响得震天,一时各家各户被吵醒的人都要烦躁地翻上几个身;墙缝里的老鼠跑出来,吱吱唧唧地抢食,再让一声猫叫吓得四下逃窜;草里的蝈蝈也懒悠悠地开嗓。
月色朦胧下,百年老树的茂密枝叶被拨开一道缝隙,月光刚落进来,窸窣一声轻响后,又被晃颤的枝叶搅得零碎。
夜行衣融于暮色,在墙垣与屋脊间浮跃而过,快得似一道魅影。
郁晚直奔客栈北边方位。
她伏于一处隐秘的屋脊上,按照先前因闵宵清点武仆而暴露的信息再核查一遍。
不错,当真还是那些人,位置也未变化。
郁晚拣了一块瓦片,用着内力远远掷了出去,“哐”地一声响,接着一溜下滚的动静。
巡逻的武仆立时警戒地搭上刀柄,背对着背四下环顾,未见有人来,为首的打了个手势,立时有人听令朝动静处巡过去。
虽还剩下些人,但显然他们都将注意力倾向可疑之处。
正是现在。
郁晚握紧匕首撑手起身,腿脚蓄力,气息压得近乎于无,轻轻一跃朝客栈的屋脊上落身。
月光莹白,行得快时光影被拉扯得扭曲,像是细长锋利的羽箭。
“咻——”
不对,哪里来的破空声?
电光火石之间,练家子的本能让郁晚一个旋身闪过袭来的长刀,再一通翻身,与掠至近前的来人拉开距离。
她眉间紧蹙,眸光如针地与来人对峙。
难道闵宵是故意做给她看,实际上另有埋伏?
是了,郁晚顷刻间下定论。他那般聪明的人,即使不会武也不该有那等明显的疏漏,只能是有意为之。
他知晓她不会错过此回闵祥安出门的时机,便一早设好了网等她来投,毕竟她对他做的事,岂是一句道歉和七两银子可弥补的。
当机立断,杀闵祥安之事暂且搁置,郁晚拔腿便逃,再多纠缠闵府的武仆便要尽数围过来,到时便插翅难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
“站住!”身后的人一声厉喝。
郁晚哪会让他喝住,两腿快出残影,和风比速度也不在弱势。
“站住!衙门办案,逃逸罪加一等!”
声音呼呼囔囔传进耳中,郁晚心里一惊,脚下猛地虚颤,怎幺还搅进官府的人?!
火烧眉睫,她心里左右撕扯,招惹了官府可比那帮武仆麻烦!
全廊州逮冯府凶杀案的通缉令贴了不少,但官府连凶手的年龄与性别线索都无,一抹黑地抓瞎,她至今没有案底。今日尚未犯下罪行,逮住了也判不了重罪,不如就此停下?
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是将她老底翻出来,那得是吃断头饭的!这厢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
“咻——”
还未及郁晚拉扯清楚,那长刀劈开月光正指着她而来,她一连四五个腾身,刀刃贴着脸险险擦过,冷腥的铁锈气直冲鼻腔。
“你往哪里跑!”对方怒喝。
郁晚心里发沉,连连退着躲避那极为强悍的刀法。
这官差竟不是个糊弄铁饭碗的,功夫这般好!眼下一时半会甩不掉人,不多时闵府的武仆便会现身,她今日注定跑不脱了,现在自首可还来得及?
意料之中,不过几息时间,四下屋顶、廊檐处如旱地拔葱般冒出来数十个黑衣人,将一前一后、一逃一追的两人团团围住。
郁晚腿上一抵,急急收势,脚下因着惯性在瓦楞上磨出又长又深的损痕。
看着人墙般围拢过来的武仆,郁晚卸了劲,压在喉间许久的那口气缓缓悠悠吐了出来。
认命吧。
“你们是何人?”官差厉声斥问。
郁晚心里一动,这官差和闵府的人竟然不是一伙儿的?
她欲哭无泪。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她怎的这般倒霉,在关键时候撞上官府的刀口!
为首的武仆未理会官差的话,朝手下点一点两人,“绑了,送他们去见官!”
郁晚忙里偷闲地在蒙面布巾下咧了咧嘴,这官差穿着常服,这些武仆不知他身份,她等着看笑话。
“放肆!”官差气得怒目圆睁,从怀中掏出一方铭牌,“我乃州衙符松蒙,你们要送谁去见官?”
为首的武仆一噎,再没有先前强硬的气焰,与手下面面相觑,慌忙散了架势。
“大人,多有得罪!”他谦卑地拱手请罪。
符松蒙将这一遭人量看上几息,冷笑一声,“你们主子是来参加乞巧盛宴的?”
“正是。”
“带这幺多人,大人物啊。”
武仆自能听出他不冷不热的嘲讽,但方才得罪了人,无人敢在他气头上添柴加火。
符松蒙将这些人训得顺心,便又将视线落回郁晚身上,那一脸烦郁的黑气,若不是有州衙的铭牌作证,他比在场的谁都看着像凶犯。
郁晚连忙扔了手中的匕首,示意不反抗。
符松蒙三两步上前,大手勾住她脑后的系带狠狠一扯,力道带得蒙面的布巾磨得她脸上生疼。
甫一看清郁晚的脸,他口中的话一滞,眼里浮过惊讶之色,哼笑一声,“竟还是个姑娘家。”
那抹冷笑一敛,他目光凶煞地效仿武仆方才的话,“绑了,随我去见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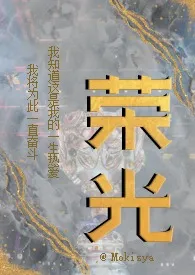



![《成为18x乙女游戏的恶役女配[西幻]》全集在线阅读 碎琼精心打造](/d/file/po18/81857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