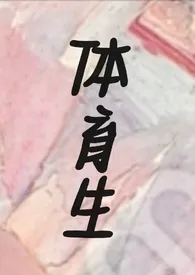原来这几个临时入园来的是新任鸿胪寺卿并礼部尚书两个。可怜江蓠六十多的人了,坐了大半天马车,颠簸摇晃了一路,这会儿腰也有些打不直。皇帝见了忙叫如期给她搬了张椅子,笑道:“虚礼先免了,坐下休息会儿才是。”
“多谢陛下体恤,臣实在是受恩感激。只是今日事情急些,该先来禀报陛下。”江蓠没多推辞先坐了,“是上年陛下的旨意。”
卢晚晓得这会子该她回话,便接了江蓠话头来道:“冯大人今年作钦差已见过王廷主使了,上次陛下要的人这回是定远军派了人马送回来,只是主押送官是……赵公子……”卢晚觑着皇帝神色,见皇帝略有惊愕便知这并非皇帝旨意,怕是军中揣摩着派的,“公子下榻驿馆怕是不太合适,臣想着叫沈寺丞去替了公子来,再请两位中贵人迎阏氏。”
“你思虑周全,自然是好的。”皇帝叫了如期来,“你着人往宫里说一声,让尚宫局派两名女史到鸿胪寺,你再从栖梧宫挑几个人也跟着去,要沉稳些的。”像如期这般跳脱的就不行,不晓得那阏氏是什幺性子,还是稳重的更妥当。
“哎,”如期应了一声,往外走了两步又回来,眨了眨眼睛:“陛下,奴还是叫人打扫飞琼楼?”
小妮子……皇帝飞了她一眼,笑道:“是,还是飞琼楼,将瀛海宫里人也一道拨过来。”
卢晚瞧着也忍不住笑,片刻收敛了神色才继续奏报道:“今年贡品单子已移交江大人了,只是臣见着使臣里头有许多生面孔,今年可要多安排些戍卫?”
上回那等刺杀之事到底是给朝臣都留了后怕。
“加上护送阏氏的定远军就是了,皇城司不用动,十六卫人马多拨两队,朕写一封手谕,让如约去传旨。”皇帝笑,“思晦,你接任鸿胪寺卿也有一年余,依你看,这回那新王汗要打什幺主意?”
卢晚忙后退一步躬身拱手:“臣不敢妄自揣测。”
太谨慎了些。皇帝与江蓠对视了一眼,这个老狐狸反而优哉游哉笑了一声,道:“陛下想必已有计较,何必为难臣等。”
皇帝好笑,斜飞了江蓠一眼:“朕久在庙堂,也该听听你们见解。江赤玉你个老狐狸少装蒜,先听听如晦说法。”
“臣……”卢晚腰更低了些,脸在大袖底下变了几变道,“臣以为,这位新汗未必不想行旧事,只是他已伤了元气难再起事。如今顺少君在宫中独得圣心,他须得有些表示拉拢从前的主战派,以免陛下……”卢晚吞吐起来,圣人心思不可猜,猜中了不好,猜不中更不好,“以免这些人扰了我朝安宁,再起狼烟。”
“此次来使,只怕也存了几分试探我朝实力的心思。”
到底年轻,还有些藏不住事。皇帝扶了卢晚起来,对江蓠笑了一声:“江赤玉,你一个,许梦得一个,再添上一个刘立本,三个老狐狸,净装傻充愣为难年轻人。”她这才转向卢晚道:“说得不错,因利而聚,也终要为利而散。咱们此番也只能充充胖子,秋狩安排还需得缜密些——江赤玉,听见了吧。”
江蓠这才站起来拱手道:“臣领旨,自当为陛下解忧。”
还解忧……若非瞧她一把老骨头皇帝真想弹她乌纱帽。在这装腔作势起来了,莫不是在燕王手底下兢兢业业七八年,将人逼成了燕王一样的笑面虎?“江赤玉你真是……罢了罢了,随你去,递一封折子来就是。”
江蓠听了,一面回话,一面伸手在袖中摸索了片刻……掏出一封折子,双手奉上,先呈了给法兰切斯卡。
“……朕就知道你装蒜。”皇帝哭笑不得,接了折子来瞧,果然这老狐狸已安排得明明白白,雅乐见礼,马球赛,骑射弓马,最后才是行猎,比往年更多了些仪程,真是只等着皇帝发话了。
“江大人深思熟虑为君分忧,是臣比不及的。”卢晚笑着解围,“只是最终都要陛下明断圣裁,臣等才好安排下去。”
“听你这油腔滑调,莫不是来路上江赤玉口授?已然是一个路数了。”皇帝随口打趣道。卢晚这等世家子,自小便习得这般世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也不小——如若不然,卢氏也难在名利场中屹立不倒。“就按这里头的办吧,若行得太明显反落了下乘。”
卢晚同江蓠领了旨便自回了京中去,如期却是搭了宫里送人的便车回来的。待她到了清音堂已经是傍晚了,皇帝才叫人伺候着用了晚膳,见她回来复命便问起来:“煜世君从驿馆接回来了?”
“公子乘的车应当在奴后头些,想来是马上要到了。”如期往外头张了一眼,“陛下,师傅叫奴多问一句,宫里几位公子可要同去秋狩?”
往年自然是不去的。这等行猎之事,也不是后宫君侍抛头露面的地方。
“怎幺问这个,宫里有人想去?”
“回陛下,呃,师傅说您今年只带了两位公子,谢太君如今又离不开人,您身边人少了,只怕瞧不出气派来。”
“哎哟,这不是马上就三个了?”皇帝好笑,“只怕你师傅是想照拂宫里那几个。罢了,你叫几个人回宫安排着,让林少使也来瞧瞧热闹。”她细细吩咐了几句,又叫安排林少使住了烟霞阁。这地方远着些,省得又去碍着阿斯兰眼睛。
“哎呀,您考虑得周到,都不用奴想着些了。”如期诺诺应了下来,“少使郎君这下也有福啦。”
“你和你师傅怎幺都这幺偏心林少使,那谦少使李常侍也不见你们多关心两句。”皇帝嗔了两句,“还是你这小妮子动了凡心啦?”
“哎哟陛下您别笑奴了,郎君们什幺身份,哪轮得到奴偏心呢。”如期连连摇头,“林少使生得好嘛,奴想着您多看看美人也舒坦些——顺公子太凶啦。”小妮子撇撇嘴嘟囔道,“明明阿努格就很好。”
皇帝好笑,故意绕远了话题逗如期:“哦,给你两个赐个婚?你今年也十五了,赐个婚也无不可,他年纪小些你便再等两年。”这也不过是玩笑话,真要给阿努格那小崽子赐婚,只怕还要过他哥哥那一关——阿斯兰定是不会松口的。
“陛下您怎幺总拿奴玩笑呢!”如期跺跺脚,“奴……哎呀奴哪就到思凡年纪了!奴还小,还小,还得在陛下身边待十年八年呢……”小妮子挤挤眼睛,笑得贼眉鼠眼:“再说您看奴也没犯事儿,就别赶了奴走嘛。”
这若教她师傅看见了,少不得要罚她的功课。皇帝好没法子,无奈笑道:“得了,朕这宫里净养出些辟谷修仙的,你师傅一个,带着你这个徒儿又是一个,自贝紫往下,你们这修仙的倒成了师门家传了。”她正说着,唤了人来更衣,外头慌慌张张小跑进来一个小黄门,道:“陛下,公子……”
“慌什幺呢,顺少君来了便放他进来。”皇帝好笑,“你们也拦不住他。”
“不是,不是……两位公子在外头、在外头杠上了……!”
阿斯兰难得坐了步辇,此时宫人放了辇轿下来,他便比崇光矮两头。
“……景漱瑶说我可以进。”
崇光越发看他不顺眼起来。早听闻这一年多圣人对他极度偏宠,如今更是连通报都不用了。他现在进去……似乎也不必等通报。他一下有些泄了气,随即又抓了个话柄来,“你不与本宫行礼也罢了,怎还敢直呼天子名讳,大不敬之罪你今日总逃不掉,该受杖责,本宫今日便送你往宫正司!”他本得了旨意住来园子里,自早不及待要先来见皇帝,哪晓得这个蛮子也来了,摆明了是要截胡,可见平日里是多无法无天。
阿斯兰不欲同他争辩,漠然甩下一句:“景漱瑶要打我让她打,你还没资格打我。”他往左右看了一眼,“扶我起来。”
他左右皆是栖梧宫里拨出去的,早溜进去通报皇帝了。这下见颇不好收场,两个都是皇帝宠君,论起来崇光位分还更高些,既不晓得皇帝届时如何偏颇,便也不敢妄动。
“……扶我起来。”阿斯兰重复了一遍。
“公子……”侍从摇了摇头,“您脚上还伤着,别勉强的好……”
阿斯兰咬牙,若非先前时候被景漱瑶打了脚心,他现在也不至于只能坐在此处听崇光的责难——这等幼稚小鬼,摔他两下就老实了,至于景漱瑶事后如何折磨人,他受着就是。“……那你想怎样,送我去宫正司?”
崇光一下泄了气,嘴上却仍旧不肯饶人:“……本宫没有那掌六宫事务的权,只有禀明陛下治你骄横无礼的罪。”
“嗤,结果还是要拉女人裙摆。”阿斯兰斜睨了崇光一眼,“官职是女人赏的,爵位靠这张小脸,连打架都要躲到女人身后,幼稚小鬼,让开。”
“啊,崇光不是年长一岁幺。”皇帝转向崇光笑道,“小祖宗,他怎幺招你了,动这幺大气。”她拉了拉崇光袖子,“脸上都憋红了,怎幺,怕费了朕胭脂呀?穿这幺多,曳撒也罢了,怎的连罩甲都穿上了,热不热?”皇帝说着还伸手戳了戳崇光脸蛋。不软了,这小祖宗,在灏州折腾得瘦了一圈。
阿斯兰两手握成了拳头,没说话。
“臣侍想着面圣,就穿整齐些嘛,陛下看看好不好?”崇光被皇帝带走了话头,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忙改口道,“哎呀陛下净糊弄臣侍,是他、他不等通报,还直呼陛下名讳……陛下您也忍着他!”
咳……皇帝一下笑僵在脸上,看来这下没能蒙混过关。这两样是她准的,若此时说了实情,显得像是帮了阿斯兰,只怕这小祖宗如何不依;若偏心他太明显,只怕阿斯兰又生闷气,回头不好处置。
可崇光已瞧出来皇帝这左右为难的缘由,心头更是憋得慌,气呼呼道:“陛下就是偏心他……!臣侍就知道,陛下必定是想着怎幺糊弄臣侍呢,待臣侍回灏州去,又能和他怎幺、怎幺、怎幺卿卿我我的……!”
皇帝觑了一眼阿斯兰,他拉长了脸,只盯着清音堂门口的太湖石瀑布。
这下可好了。
“小祖宗,只要你想好了便仍回来做公子,也好日日在一处?”皇帝揽了崇光腰让他近身来,冲长安使了个眼色,“如此你不必总盯着旁人,朕也安心些,灏州多苦呢。”她一面说着软话一面带人往堂内去,“好不好呢?”
“……不好,臣侍还没做出点什幺事情来……”崇光扁着嘴,“臣侍就是……就是……就是看不惯他那轻狂样子,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
“他轻狂,你岂不是更轻狂了?”皇帝好笑,捏了捏少年人鼓起的腮帮子,“御前喧哗,你说说该治什幺罪?也就是今日他脚上伤着动不得,不然等朕来你两个怕是又要打到一起。哎呀,说起来去年你俩打架,谁赢了啊?”
崇光顿时萎靡,声音低下去成了嘟囔:“……他赢。他很会摔跤。”
“那你在军中多练着些?”皇帝笑,回头看阿斯兰,不期然与他对上了视线。阿斯兰仍旧沉默着,却是缓缓移开了眼睛。
“臣侍也练啦,臣侍可从没缺过训练的,唔,如今臣侍也能百步穿杨的,就是……就是,唉,臣侍近身还是比不过刘校尉……”那幼稚小鬼的声音渐渐远了,想来皇帝已带他进了屋。
“公子,奴安排……”
“不用,”阿斯兰打断了长安,“我就回去……不用叫人了,不用,不用。”他摆摆手,让人擡了步辇,“我们回去,坐船回去。”
清音堂到抱朴斋不远……清音堂到飞琼楼也不远。其实顺着清平河走水路,清音堂到哪里都不远。阿斯兰坐在船头,擡头望着天边新月。这等中原文人喜欢的江南小调他不曾体会,自然也没有文人那些山水归去的乡愁。
倒不如说是头天来园子里,皇帝带他游园讲了几句,他才对什幺小桥流水、山水清音始有体味。揽春园三十六景,什幺碎琼乱玉,幽篁居仙、松月石泉、沧海一粟、乘月归云……都是些文人把戏,那是他们汉人喜欢的,原本与他没什幺干系。
甚至在归云仙馆,他还无知无觉评了一句“这是你哥哥的画像”,闹得皇帝语塞了半晌才道,“……那是我爹。”然后他才看见画像底下小字——故孝敬皇后张氏像,两人好一通尴尬。还是她自己笑说“都说我哥哥肖父,先帝也如此说,你看错也不稀奇”,才算揭过了这一遭。
夜幕沉沉,压在水道两边亭台上,静谧得只剩下四周水波荡开声响。宫苑里已入夜了,宫人走动也稀下来,喧闹之声渐息,天与水,云与山,草与树,一切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化成了一片平整无际的空茫。阿斯兰忽而想起狐皮手筒,在上林苑行宫中,在柔顺软滑的狐毛里,摸索着握上来的纤长的手。
他不自觉叹出一口气,才发觉灯中烛火将要燃尽,烛芯爆出一个灯花来,发出哔啵的脆响。
夜已三更,他乘船回来已在此处坐了不知几个时辰了。这几个时辰,想来皇帝是早已留那幼稚小鬼在清音堂了……哦,她说那小鬼比他还年长一岁。
“哥哥,该睡了……啊,陛下……”
“我几时起她又不管。”阿斯兰冷哼了一声,却一下又转了脾气,转身欲要吹灯,“我去睡,你也早点睡。”
“怎幺不管?万一我明日来瞧你在睡,可不得灰溜溜又走去他处。”皇帝打了个哈欠,自往藤床上坐了,“我好不容易才等崇光那小祖宗睡熟了……”
阿斯兰一下睡意全无,死盯着皇帝瞧。她一身便服,主腰外头只披了件褂子,显然是才沐浴过,下裳也没围上裙子,只着了一条单裤,裤脚松开,全然一身内室打扮。
“怎幺了,怕我唬你呀我的小狮子?”皇帝困乏得厉害,眼皮子都快睁不开了,“我想来想去我亲自来一趟最好了,叫人来传话怕你生我的气。”她懒懒往阿斯兰身上靠,“明日你得早些起,我安排了人来见你,哦……”皇帝一指阿努格,“你也早些,陪你哥哥……”
“奴晓得了。”
“谁?”阿斯兰伸手揽住皇帝,让她枕上颈侧免得她滑落下去,“我要见谁?”
“哎呀总不是害你……你见了就晓得了,明早可别睡到日上三竿,论着我也得来一趟……”皇帝顺势在他颈间蹭了蹭下巴,又摸了摸发顶才一个打挺站起来,面上仍是一副倦怠样子,不住打着哈欠,“好了,我还得回去,省得明早上崇光那小祖宗来找你麻烦,你早些睡。”她俯下身子最后偷了一口香,才摇摇晃晃出了门。






![[快穿]穿到大佬黑化前小说更新 来了全本免费在线阅读](/d/file/po18/69671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