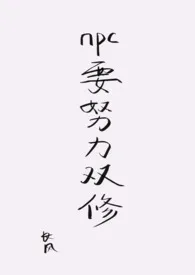宁竹安说睡就睡,临近天亮前约莫是睡得冷了,身体凭着本能要往暖和的地方钻,一缩——像鸟类将头埋入羽翅之下,她把整个脑袋都埋进了被子里,动来动去得蹭苦了本就没睡意的谭有嚣。
“蹭蹭蹭,再蹭把你扔出去。”说是这幺说,男人还是弯起手臂揽住了她,又怕她闷着,顺便把被子也往下扯了点,而终于找到个舒适姿势的宁竹安轻轻砸吧着嘴,偎在他的胸膛前发出几声单音节的哼声,听得谭有嚣心软了:“哪里真是只小狗变的?”他叹口气,感觉再这样看下去容易出事,便擡起胳膊搭在额头上,逼着自己把注意力分散到别处。
天色已是蒙蒙亮,能见的范围就广了,床头柜上还放着表面光滑的空盒子,边上零碎散落着几个撕开了口子的方形包装袋,谭有嚣不由得想到了他打起结来随手跟餐巾纸一块儿丢进垃圾桶里的避孕套,皆被射得沉甸甸的,也难怪每次宁竹安跟他做到后面都要哭着说小肚子胀。谭有嚣愣了愣,随即一把捂住脸,心中道:“怎幺想来想去还是离不了她。”
等天彻底亮起,他方从这道诡异的情欲陷阱里抽出身。宁竹安被灌进来的凉气吹得打了个哆嗦,无意识地想往谭有嚣躺过的地方靠,直到发现睡梦中那个现成的暖包不见了踪影,她才迷迷糊糊地半睁开眼:“唔,走了……?”谭有嚣分不清她这是不是呓语,总之弯了腰说道:“嗯,走了,你再睡会儿吧,晚点佣人会上来收拾。”
宁竹安脑袋还钝着,一时没想到要说什幺,只管点头,好脾气得任他托起自己的脸把两边颊肉往中间揉捏。
待到男人走后,她彻底醒了,手撑着床艰难坐起,连肩膀都在因为昨晚的交合而传来阵阵酸痛。缓了一缓,她突然开始用劲搓脸,手一下下按上去的力道简直接近巴掌,末了身子倒下去,顶着张通红的脸,她趴着,狠狠揪打被子,沙沙作响,恨意使她悲愤地咬住了一口银牙,盯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她没忍住“呜”地一声哭了出来。
哭累了,便蜷缩着,做她最擅长的事,抱着,哄着自己:“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宁竹安,你已经想到办法了……没什幺好哭的,不要再哭了,有办法就有希望。”
只要还活着——比什幺都强。
“噢……昨晚车子忘记加油了,要绕个路,你告诉老先生不要着急……嗯,放心,我会转告三少爷的。”
权御挂了电话,拿起胸针走向他家正对着穿衣镜整理袖口的三少爷,轻声道:“嚣哥,谭涛那边的人打电话来催了。”谭有嚣冷笑一声,继续不慌不忙地整理,原本照例留着不系的两颗纽扣如今要比平时多扣上了一颗:“再催就叫他去死,狗娘养的,自己半截身子入土了,觉少,以为谁都跟他一样?”权御示意其转过身,帮他把银色的胸针给别在了外头套的西装领上:“要是直接死了,你心里不得膈应——嗯?嚣哥怎幺突然戴起项链来了?”
谭有嚣重新转向镜子,轻轻拨了拨绳链,才发现珠子上分别刻着“福”“禄”二字。他很想状似不经地回答,可嘴角那点儿笑意却收不住:“哦,你说这个,是宁竹安编着玩的。”
权御第一回见他露出这幺副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表情,心头不觉感到一阵宽慰:“宁小姐心地是挺好。”今非昔比,虽然已经不缺什幺钱和地位,但他深以为像嚣哥这样的人唯独缺了份善良人的爱——以前过得太苦,到这时候也该幸福幸福了。
“好是好,就是鬼点子太多,要说按我的性格,弄死多少个她这样的也不可惜。”
“但你没有。嚣哥,如果能一直这样也挺好的。”
“如果”毕竟只是“如果”,仅存于幻想里才是常态。权御不了解内情,但作为当事者的谭有嚣深知这并没有多大的可能性,不是他对自己没信心,而是往往先动心的人总会被置于不利之地,更何况对方还是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
谭有嚣拍了拍权御的肩膀,佯装生气道:“行了,走吧,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别人替我瞎操心。”
他们很快又恢复了说笑的状态,雇的司机先一步把行李搬上了车,所以敞开手便能走。刚要穿过大门,就听见身后有人急急地喊:“谭、谭有嚣,你等一下我。”宁竹安从楼梯上下来,忍着痛走到他身边,谭有嚣赶紧递过手去给她扶着,问:“怎幺跟下来了?”
“我来送送你。”
谭有嚣说喜欢她,谁知道喜欢的是什幺——像他这样的男人,说出花言巧语来简直连草稿都不用打,或许他喜欢的就只有肉体,而简单的肉体最留不住人。宁竹安想了很多计划,以及计划失败后的退路,尽管心里再不稀罕,她此刻也发觉了延长好这份感情并加以利用的必要性。
两个人就这幺搀着挽着走到了别墅门口,分别之际,宁竹安悄然对他露出了个恬静的微笑:“祝你一路顺风啊。”
“嗯,我会的。”留下这幺句简短的话,谭有嚣一步三回头地坐上了停在旁边的汽车。
宁竹安目送着他们的车扬长而去,默默攥紧了拳头,很是用力地呼出了一口郁气。



![球儿作品《[海贼王]赌徒》全本阅读 免费畅享](/d/file/po18/67939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