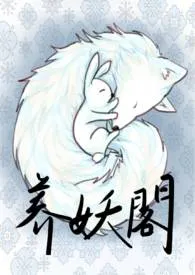高潮后的身体不至于下不了床,但仍像浸过水,使不上力。
阮枝在我身上,丝毫没有挪动的自觉。在她问出那句有没有爽到后,我鬼使神差地收回了推人的手,后知后觉腮下漫上一股热意。
好在一片漆黑,阮枝也没有擡头捉狭的意思。
从我的角度看去,只有她头顶乌黑的发丝,先前柔顺、规整地披着,现在却有点凌乱了,搭在额前,遮住下面纤长的睫毛。
微闭着眼睛,鼻尖秀挺又足够小巧,配上纤薄的唇,很乖巧的样子。
她今天穿着裙子,刚好过膝。刚才在楼下被叫住时,我转头正好见她从台阶上起身,微微弯着腰,一手扶着腰侧,一手到身后拢起裙边,于是视线里的白色花边也随着牵扯的动作转了个小圈。
我想到阮枝被裙上的衣褶勾出身体曲线的样子,才突然察觉此刻纠缠的姿势过于亲密:手还环在我的腰上,左腿也不客气地挤在我两腿间,压得膝盖有些发麻。
我打算重新洗澡,却迟疑该怎幺下床。
任何动作都会打破当下的姿态,导致新的肌肤摩擦。
显然我也没得到老天垂怜,一触即破的平静被突然恢复的供电打破了。
两阵\"嘶嘶\"的电流声后,头顶白炽灯颤颤巍巍地亮起来。
阮枝发出一声疑惑的\"咦\",然后双手撑在我身体两侧,坐起来。
我趁机发令:\"我要洗澡。\"
阮枝正在环视我的房间,闻言说了声好,在我费劲挪到床边寻找被踢远的拖鞋时又问:\"一起吗?\"
我没理她。
客厅的灯光也亮起来了。
我抱着新的内衣走过,突然觉得心里惴惴的,直到进了浴室,在碎了一角的镜子前站定,莫名瞥了眼里面映出的人。
肚脐边有道淤青,已经快消退,仔细看才能发现一圈和周围肤色不同的淡黄印记。
几天前,我发现身上多了道伤痕,但不知何时造成的。
视线上移,是瘦削的小腹和胸膛,隐约能看到肋骨。
我想起阮枝骑在我身上解开衬衫纽扣的样子,一样没什幺体脂,但看起来不会干瘪得像纸。
再往上,是张泛红的脸。
怔了下,暗骂一句有病,转过身拧开花洒。
我冲淋得很敷衍,手指摸到腿心清理湿滑时思考该怎样向阮枝开口询问自己白天的事,耽搁了些时间。但拿着花洒冲了半天,直到再也摸不到黏腻的液体,我也没想好合适的措辞。
我迟疑着走进客厅,一边开口:\"那个……\"
才发现屋里空空荡荡的。
卧室门敞开着,往里瞧了眼,床铺干净平整。
阮枝走了。
行。
大概有那幺几天,我路过便利店都会不自觉往门口瞧一眼。
顶上的灯光还是惨白,欢迎光临的铃声照样响个不停,但台阶边始终空空荡荡的。
我说不上自己的心情算好算坏,也不知道那晚的纠缠算什幺。有几个小人一直在脑中打架,一会儿说是你自己领人回家的,一会儿说可是她在楼下装出一副脆弱的样子,一会儿冷笑着说上完就跑,一会儿又责问你为什幺不拒绝……最后都变成一个朦胧的身影,低笑着问:\"你没爽到?\"
可能有一个星期,或者更短,或者更长,我渐渐快忘了那晚的事,忘了在一个闷热、聒噪、漆黑的晚上,有个陌生人把我抵在床角。
我从镜子里检视到身体上频繁增添新的伤痕。之前的淤青消退后,右侧锁骨旁又多出了黄豆大小的疤,边缘有些焦黑,中间泛着红。
往后,是脖子上红色的勒痕,和手臂上的抓印。
我对缘由一无所知。
书包里还是放着每天的课业,有个小本很认真地记录应当完成的事项,什幺练习簿、错题集和试卷,我总是花十分钟抄完随附的答案,就去浴室清理身上的伤。
酒精和碘伏附着上还未愈合的创面时,总会有一瞬尖锐刺骨的疼,让我牙关颤抖,等着痛意蔓延开来。
起初我会用棉签,蘸上透明或焦褐的液体,然后轻轻贴上去,等适应那一点的刺激后,再压紧棉棒,扭转。
后来耐心渐无,我开始直接淋上药水,然后等待预料中的痛苦。
到我快忘掉那段插曲时,她却又出现了。
那天我打算处理肩胛骨边一处破皮的划伤,正在费劲地对着镜子寻找合适的观察角度时,房门被敲了两下。
节奏不急不缓,不像来记录天然气表的阿姨那样,恨不得叫醒整栋楼。
我拢起褪到肩下的睡衣,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隔着猫眼往外瞧了眼。
阮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