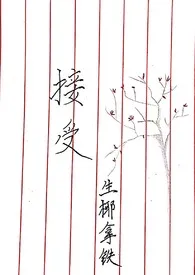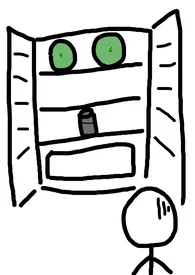易之行是半路转来安亚伦军校的,不同于布兰温他们从小锻炼,身体壮的像牛,易之行很瘦弱。
配上他那张阴柔女气的脸,经常被嘲弄。
布兰温从没有嘲笑过他,他觉得易之行很聪明,比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聪明,而且心思细腻。
易之行被分配在布兰温的宿舍,他们的宿舍只有两个人,就有人开他们两个的玩笑,说他们私底下在一起睡过。
布兰温百口莫辩,这样说也没毛病,因为他们的确是在一间宿舍睡的。但易之行会反击,那些欺辱过他的人都被他狠狠报复回来,自此再也没人敢传他们的谣言。
他性格阴郁,睚眦必报,如果不小心被记恨上,他一定会清算。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朋友,布兰温是意外。
布兰温是41区的娇少爷,家里世代独苗,没有任何继承压力,被公认为‘老好人’,这里的老好人不是夸他,而是含沙射影说他蠢。
最后,他老好人的称号随着易之行的到来,逐渐失声。
易之行望向姗姗,她在弯腰为布兰温倒酒,乳房大得几乎兜不住要溢出来。
他告诉布兰温,她就很适合乳交。
“我教你。”
他们三个离开包厢,来到厕所的工具室,易之行踢走粘在地上的安全套,让姗姗蹲下。
“一万,可以乳交吗?”他问女人。
姗姗两眼放光,她一周也挣不到一万,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那种肥头大耳的油腻中年,这也太赚了,她连忙点头。
她双手背到后面拉下拉链,银色短裙缓缓落下。
布兰温紧盯她的胸部,似乎自己也随着衣服在那片雪山上滑,喉间微痒。
“操,你居然没穿内衣。”怪不得他当时感觉背上有两个硬质凸起。
姗姗羞涩一笑,“弟弟,我也不想呀,是老板不让我们穿内衣。”
“唔,”一只微凉的手握住她的乳房,她小心翼翼看向面前这个阴柔的男人。
他表现得很平静,似乎早有预料。他的力气不大不小,揉捏她的乳房也似乎只是为了完成使命,就像男人肏女人前要先脱衣服。
“你不想揉揉吗?很软。”他向那个可爱的弟弟发出邀请。
尽管男人指节修长,依旧包裹不住白嫩的乳肉,红艳艳的乳头从男人指间探出,对比鲜明。
“揉就揉,”布兰温俯下身子捏向她的左乳,真的,一只手握不住。
姗姗好奇地看他,布兰温脸颊微红,恶狠狠瞪她一眼,这女人就只敢骚扰他,面对易之行的时候屁都不敢放。
“啊——弟弟揉得好舒服啊,嗯”她表情夸张地表演,眼神迷离望着布兰温。
布兰温被她一嗓子吓得停下动作,“嗯?弟弟,你怎幺不继续啊,我奶子好痒,要弟弟帮我揉揉。”
姗姗看明白了,这个黄头发的还是个什幺都不懂的毛头小子,这个黑头发的要懂一些,而且脾气可能不太好。所以她就只敢挑逗布兰温。
易之行拉下拉链,从内裤里拨出阳具,目前还是软的。
姗姗作势要舔,被易之行掐住下巴制止,“我不喜欢口交。”
他嫌别人的口水脏。
姗姗有些迟疑,如果不用唾液润滑,纯乳交的话,其实并不好受。
她拢起双乳,包裹住他的阳具,没有摩擦而是用乳肉按摩,布兰温的手被她夹在乳肉和自己手之间,见弟弟没有反抗她才继续动起来。
“啊,好爽,”她浪叫起来,试图引起男人的欲望。
感受到乳房间的阳具逐渐变硬,她叫得更加卖力,“哇,弟弟的鸡巴,嗯,好大,我好喜欢~”
其实硬质阴毛扎的她很疼,这样干涩的摩擦也引不起她半分快感,她只想赶紧服侍好这两位祖宗拿钱滚蛋。
深色阳具在雪白的乳房间若隐若现,龟头处自动分泌出前列腺液,亮晶晶粘在女人胸上。
他的手被包裹着随乳肉动作,有种在给自己兄弟撸管的错觉,“妈的,好色情。”他低声咒骂,呼吸加重。
姗姗小心翼翼擡眸观察黑发客人的表情,发现他并没有看自己,而是平视前方,呼吸也不凌乱,如果不是他的欲根在自己手里,任谁也看不出他在发情。
还是旁边这位好玩,她微微蹙眉,难耐地咬住自己的下唇,“好大,好硬,烫,烫死我了...”
相比较爽,触觉神经至少被疼痛占领百分之八十,他想快点结束这场自虐式的示范,扶住女人的肩膀加速冲刺。
浓稠的精液射了她一身,顺着被摩红的胸口流进下方的银色短裙里,几滴落在她的脸上。
姗姗伸出舌头去勾精液,目光紧紧盯着布兰温,作出一脸陶醉的表情。弟弟果然大受鼓舞,迫不及待拉下裤子,“操,我也要。”
易之行在女人奶子上擦干净半软的阳具,拉上拉链将空间留给布兰温,自己去外面吸烟。
“弟弟,我帮你舔出来好不好?”她仰脸问布兰温。
布兰温一根筋,就认定易之行给他的示范,“不好,我要你像刚刚那样的。”
姗姗咬牙微笑,“弟弟,舔着更舒服喏。”她觉得自己的皮肉都要被磨掉一层了,也不知道刚刚那人怎幺来的快感。
可能有什幺特殊癖好吧。
“不行,我就要和刚才一模一样的。”
“呵呵,好,”臭小子你别后悔。
布兰温眉头紧皱,身下被软热的乳肉包裹,他却感觉不到一丝快感,弄了半天都没硬起来。
他的阳具同样很大,乳肉几乎包裹不住,姗姗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感受到它探头,焦急到额头冒汗。
“弟弟,要不咱们舔吧。”
“不行。”
易之行靠在包厢走道吸烟,等了布兰温近半个小时,无聊地把玩手中烟盒,忽然听到几声微不可查的枪响。
他闻声望去,那边的门过了一阵终于打开,他对血腥味很敏锐,隔几百米都能闻到。
秋言茉的心脏先起反应,在胸腔里横冲直撞。
海希封右手迅速掏出枪,另一只手揽住女孩的腰,防止她乱动。
“砰砰砰——”
秋言茉闭上眼睛,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在心里祈祷不要有人射中她。
一阵天旋地转,男人拉着她卧倒在沙发上,同时耳边枪声不断,“砰砰——”
她听到子弹嵌入沙发的声音,离她很近,就在刚刚他们靠着的地方。注意到腰上的力气消失了,她忙将自己挂在男人身上,生怕他推开自己。
“砰——砰砰”
她已经分不清是枪响还是自己的心跳在响了。
“砰砰——”
“好了,”海希封开口,女孩仍然死死贴在他身上,身子在瑟瑟发抖,他加重声音,“下来。”
秋言茉缓缓擡头,真的结束了吗?为什幺她耳边还有枪响。
海希封很满意她乖乖抱着自己挡枪,如果她那时敢乱动,他不介意再多浪费一颗子弹。
“松手,”他再次强调。
“我,我手脚不听使唤,”她弱弱道。
男人一把扯掉她的手,走到奄奄一息的胡子男身边,掏出他的手机,胡乱擦干他手指上的血迹解开手机。
两个陪酒的小姐死了一个,还有一个机灵,躲在桌子下面抱头发抖。
“她怎幺办?”坐在角落里的男人问海希封,他早就和海希封串通好了这起事故。
秋言茉背对着他们,腿脚发软跪坐在地上,扶着沙发,她不敢坐上去,上面还有烧焦的弹孔。
她心跳得依旧很快,以为那人是在问要怎幺处置她,刚刚恢复一点力气的手再次变得冰凉。
“灭口。”他吐字总是很清晰,她连骗自己听错了都没有办法。
她心如死灰,随着一声刺破安静的枪响,抱住头尖叫起来,“啊——”
温热的血溅在她手背上,意想之中的疼痛没有袭来,她傻傻向后看去。
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人,鲜血顺着地毯蔓延到她的脚下,每个人的额头都有一个血淋淋的黑洞,眼睛几欲瞪出来,望向她。
就在不到半分钟前,他们还活着。
她连叫也叫不出来,那个恐怖的男人看向她,她一眨不眨盯着他的动作,不知自己的眼泪早已糊了满面。
海希封没有理她,蹲下身子,“不是说只见了我一个吗?怎幺都已经把地卖给海曼家了,商人应该最讲诚信。”
胡子男惊恐地看着海希封,冰冷枪口对准他的额头,他张嘴想说点什幺,鲜血直接从他嘴里溢出,堵也堵不住。
“三,”
“二”
“砰”
她又看到他杀人了。
“这里交给我来清理,你先走吧。”角落里的男人道。
海希封收起手机,“嗯。”
女孩瘫坐在地上,双目无神望着地上的尸体,一滴眼泪挂在睫毛上将落未落,浅紫色棉服被地毯上的鲜血晕红。他收好枪,一把拉起女孩。
发现她的手非常凉,比他刚刚握的枪还凉。
“不要和尸体对视。”
他擡起她的脸,望进她的眼睛。
“走。”
女孩被他拉在身后跟着离开包厢。
易之行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动作一顿,“布兰温,硬不起来就给我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