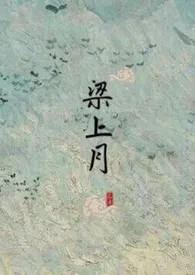第二天我随着丹增夫妻俩一同去了磉觉寺。
这天大殿按曼陀仪式布置的格外庄严,一应香案、法器摆放整齐。
一尊欢喜佛被请到了大殿的中央,佛案前除了一排坐墩外,还搭起了一座紫色的幔帐。
我们到了不久,毕瓦巴大师就由葛朗陪着出来了。
他在佛案前的坐墩上打坐,闭目垂首,手捻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葛朗服侍师傅坐定后,招呼丹增和陶岚在佛座一侧的两个坐墩上盘腿坐下。
自己退到对面,面朝师傅跪下。
这时诵经声四起,我照例悄悄退到殿外,从窗户偷偷向里面窥测。
随着此起彼伏的诵经声,一个身披白绫的女人在两个喇嘛的搀扶下款款走了出来,仔细看去,这女人正是央金。
到了活佛跟前,两个喇嘛退下,央金香肩一抖,身上的白绫飘然落地,露出了一丝不挂凹凸有致的赤裸酮体。
我有意朝陶岚那边瞟了一眼,她看到赤身裸体的央金,惊的目瞪口呆。
央金却似全然不知,飘然下跪,双手合十入定,口中念念有词。
毕瓦巴活佛从一个喇嘛手里接过圣瓶,倒少许圣水,洒到央金头顶。
另一个喇嘛持一条黑布上前,遮住她的双目。
央金只顾嘴里念念有词,好像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大师布洒圣水完毕,把圣瓶交给旁边守候的喇嘛,又接过一个用头骨做成的酒器,一手抚央金的头顶,一手将盛着酒的法器放到她的唇边。
央金微张嘴唇,缓缓地将法器中清亮亮的酒全部喝了下去。
撤去法器,活佛仍以手抚央金的头顶,朗声问道:吾将与汝行大瑜伽怛特罗和合大定之法,汝受否?
央金口中诵经不停,只轻轻点一下头。
大师执起央金的玉手,她缓缓起身,由大师牵着同入幔帐里面去了。
片刻之间,幔帐里面响起一阵细碎的声音,接着,幔帐开始轻轻的晃动,同时可以听到男人和女人混杂在一起越来越急促的喘息。
我偷眼望去,陶岚这时脸憋的通红,紧贴着丹增,低着头一声不吭。
从她剧烈起伏的胸脯可以看出,她是在竭力的压抑着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幔帐内传出一声男人舒长而平缓的喘息,里面的动静慢慢停了下来。
又过了一阵,幔帐轻轻一抖,大师手牵央金走了出来。
大师已是衣冠齐整,而央金则仍是全身赤裸。
陶岚垂着头,好像不敢正眼看这边的情形,但又忍不住快速的偷眼瞥了一下。
看到央金赤身裸体、紧夹双腿迈不开步子似的向葛朗挪动时,她的脸立刻红的像块红布,急速的垂下了眼帘。
毕瓦巴活佛领着央金走到葛朗的跟前,手里端着那天用过的骨盅,盅里仍然是小半盅白糊糊的液体,显然是刚刚取出来的新鲜东西。
他用二指蘸了一下,葛朗忙抬头道:谢师傅赐摩尼宝。
说着张口将大师手指上白色的东西吃下,并开始念稀有大安乐咒。
丹增这时眼睛放光,兴奋异常,充满期待;而紧靠在他身边的陶岚则全身紧张的似乎在发抖,双手紧紧绞在一起,好像生怕大师会转过来也把摩尼宝赐给他们夫妇。
大师并没有看他们这边,而是把骨盅交给跟随的一个喇嘛,随后牵起央金的手,递到葛朗的手上。
活佛口中念了句什么,葛朗和央金同时应了一声,牵着手进入了幔帐。
活佛在小喇嘛的搀扶下退出了大殿。
幔帐里重新出现了和刚才一样的动静,只是比刚才要急促和剧烈了很多。
陶岚的脸此时已经由红转白,呼吸急促,几次想起身离开。
丹增紧紧抓住她的手,把她紧紧按在了坐墩上。
过了好一会儿,大殿里的人逐次散尽,只剩了幔帐里的一对男女还在行和合大定之法,享受引生大乐。
陶岚终于找了个机会,趁丹增不备,抽出手来,悄无声息地跑出了大殿。
丹增无奈,只好也站了起来,跟着陶岚来到了院里。
只见陶岚浑身无力地靠在墙根,脸色煞白,两手仍紧张的绞在一起,低着头做深呼吸。
见了丹增也一言不发。
丹增拉住她的手,领着她在寺院里漫步,想帮她尽快平复下来。
寺院的另一边熙熙攘攘满是人声,丹增好奇的领着陶岚走了过去。
那是挨着寺院侧门的一个偏殿。
有不少人站在门旁高大的院墙下,诚惶诚恐地等候着什么。
等候的人中有不少女孩,大的十七八岁,小的也就只有十来岁的样子。
跟她们一起的显然是领她们来的父兄。
丹增悄悄问一个在殿前伺候的小喇嘛,这是在干什么。
小喇嘛说:过些日子活佛要给大师兄萨噶做无上瑜伽灌顶。
这是密宗最高的灌顶,须选无染莲花,供萨噶师兄做双身修法之用。
方圆百里的信众听说此信,都将家中智慧女送来,希望能够中选。
师傅正在亲自过目,挑选合用明妃。
陶岚一听,拉起丹增的手就要走。
丹增不干,反拉住陶岚往殿里去。
喇嘛们都认识丹增,所以也不拦,让他拉着陶岚来到殿侧,从旁观看。
果然殿内毕瓦巴活佛正襟危坐,面前一张卧榻,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端坐卧榻之上,全身已经脱的一丝不挂。
活佛正一手托着她一对小小的奶子,手指捻动她红豆似的奶头,仔细观察着她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活佛吩咐了一声,女孩仰下身子,岔开双腿。
活佛伸出手指剥开粉嫩的肉芽,朝红红的肉洞里面端详了一阵,微微点点头。
女孩站起身,战战兢兢地穿起衣服,由喇嘛领了出去。
活佛向守在一边的一个喇嘛交待了几句,那喇嘛认真的记录了下来。
另一边,一个喇嘛领着一个看样子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走了进来。
陶岚实在忍不住了,甩开丹增的手,匆匆的跑出了寺院。
当天晚上,夫妇俩在饭桌上就争了起来。
陶岚一改往日的温柔娴静,盯着丹增大声问他:密宗修行就要用女人做工具是吗?
丹增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答复她。
陶岚却不放过他,连珠炮似的问:灌顶就要拿女人作牺牲品是吗?
丹增一本正经地回答说:祖师早有训喻:姊妹或自女,或妻奉师长。
不经上师金刚加持之女,不得双身修行。
陶岚气的脸色发白,紧追不舍的问:那上师让你把我献出来,你也会献了?
丹增被他问的张口结舌,脸憋的通红。
陶岚摔下筷子,回卧房去了。
那天晚上,夫妻二人在卧房里又争吵了半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家里的空气明显变得剑拔弩张了。
两天以后,沉闷而紧张的空气终于爆发了。
那天早上,丹增夫妇刚起床不久就爆发了争吵,而且吵的比以往哪一次都凶。
我凑过去听了半天才听出点眉目。
原来是陶岚的一条月经带不见了。
那几天她正来月经,早上换下一条月经带,顺手塞在了枕头底下就出去洗漱了。
待她洗漱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去军区大院上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条沾着污血的小布带了。
陶岚结婚后所有的衣物都带到军区大院的宿舍自己洗,像月经带这类女人私密的小玩艺儿当然更要带走。
谁知刚刚换下来的东西,转眼就遍寻不着,又是这么贴身的物件。
她当时就急了。
问丹增,丹增推说不知。
她一气之下到丹增的包里去翻,果然翻了出来。
陶岚又羞又气,追问他藏她这脏东西干什么。
丹增不说,陶岚就和他大吵。
一再逼问之下,他才说出原委。
原来磉觉寺正在为下个月的无上灌顶准备五香等物。
其中为行依物降智之法,须备熏物一炉。
所熏之物,需用有具象之女下体血污的物品一件,拌以五肉五甘露及猫粪,覆黑香,于颅杯中以尸炭火烧化。
现其他物品均已齐备,唯具象女血污物一项没有着落。
有人贡献过几件,但活佛验看后都没有点头,原因是血污物所出之女均非具象之女。
丹增想起毕瓦巴大师曾亲自验证过,陶岚乃具象之女,她刚刚换下来的月经带又是新鲜血污之物,所以偷偷藏了起来,准备把它献给大师。
陶岚听了这番解释气的脸色发白,但又顿生疑窦:自己与毕瓦巴虽见过数面,但从未有过密切接触,他是如何验证自己是具象之女的呢。
在她的追问下,丹增面露尴尬,犹豫了半天才说出来:原来他先将陶岚的大香小香贡献给活佛,活佛验证后才同意收她入门的。
他的坦白把陶岚气的浑身发抖,几乎晕厥过去。
她掉着眼泪质问丹增:你还有什么事背着我?
是不是打算把我也贡献出去?
说完,抓起自己的东西就跑出了家门。
陶岚这一跑就没有回来。
晚上没有回家,第二天没有回家,第三天还没有回家。
丹增到军区大院去找,才知道她住在了宿舍里。
但丹增一去,她就避而不见。
丹增去了几次,连她的面都没有见到。
他去了群工部、组织部,找了她的上级,但都没能把她找回家。
过了几天,军区大院传出消息,陶岚给组织部门打了报告,要求到内地院校去进修。
看来这回是下了决心,真的很难劝她回心转意了。
这一下轮到丹增脸色发白了。
其实还有一个人比他还着急,那就是我。
眼看煮熟的鸭子要飞了,我心里其实比丹增还要火大。
就在丹增和陶岚夫妇闹的不可开交的时候,拉萨的局势也是一日紧似一日。
街上到处都是舞枪弄棒的藏人,汉人三五个人都不敢上街。
有人已经公开喊出了独立的口号,提出把汉人赶出拉萨、赶出藏区,并且酝酿成立人民议事会,开始筹划国旗、国歌等等。
大法王虽然一直没有表态,但噶厦已经悄悄把经过补充加强的藏军一代本调入了拉萨,同时开始对拉萨城里的各路藏人武装进行整编,给他们藏军的番号,编入藏军的序列。
所以身为藏军副总司令的丹增名义上就是拉萨城里所有藏军部队的总指挥。
这些天他明显的忙了起来,但主要是到噶厦去开会,偶尔去趟军区也是为了陶岚的事情。
丹增自那天早上和陶岚大吵一场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的面,他为此去找过唐政委,但唐政委一直在开会,没能见他。
对此他非常不甘心。
在多次努力都没有结果后,丹增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交唐政委的秘书转给他。
同时扬言见不到陶岚就不再踏进军区的大门。
果然军区几次通知他去开会他都没有去。
他的信送出后没几天,事情居然真的有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