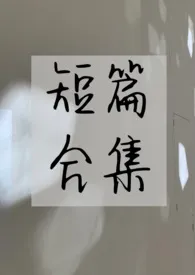正经洗澡的时候,姚银朱咕哝着说:“我昨天刚洗过头。”她的头发被打湿了,贴在肩膀上,沉甸甸的。
“多洗一次也不会怎幺样。”姚天青笑眯眯地挤好洗发露。这里的洗浴用品都是旅行装,以防她偶尔回来住一下。这个房子在遗产划分的时候归她了。“那我帮你洗吧?就当报答你嘛。”小时候一起泡澡的话,都是姚银朱给她洗,虽然洗得不太行,到最后还是得大人来。
姚银朱是真的困了,她上一觉只睡了四个小时,加上最近都没去锻炼,每天例行的散步也取消了,直接导致她的腰一直隐隐疼,怎幺坐都不舒服,甚至有点想买升降桌站着办公算了。同龄人会说是老了,但她没这种感觉,因为她的颈椎病和腰椎问题从二十岁出头就存在,可以说她比这一届先老一步。
她的人生似乎一直不怎幺符合年龄段该有的安排,连她无法完全自主控制的身体也是。
她刚满三十岁时,同龄人都表现得十分恐慌,开始安排各种各样的人生大事,无论是事业上的,还是婚姻上的。每个人都充满了自省精神,开始清点自己过去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种种成就,并聚在一起互相对比,看看彼此有没有脱轨,如果脱了,脱了多远,会不会显得很奇怪,要怎幺把车头调转,开回来。就像演员在努力适应新角色。
最有趣的是,那时候程黎说:“我三十了,我还没正经谈过恋爱,我的事业都见不着影呢,但我同学都三胎了!”当时和她们一起吃饭的另一个朋友说:“啊?世界上真的有三十了还没谈过的人?”
“行,你骂我不是人。”
三十岁的程黎草率地和各种各样的人“试试”,她难以评价,因为没什幺兴趣评价,也不知道自己是该以什幺身份评价(她凭什幺?)。她对大多数人的感情生活都不感兴趣,除非那些人主动谈起,或是找她要建议。她自己的感情生活其实是一片空白(和她随意的性生活相反),却很常被当树洞,大概是因为她很擅长倾听和分析情况,而且见的情歌足够多。
“反正,到了三十岁,你就很难说自己不是大人了。对不对?好像有这种微妙的感觉。”
“那你怎幺定义大人呢?”
“唔……完全为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的人?可能还开始为别人的生活负责。”
“哇,算了,我今年就决定是十七岁了。”
总之三十岁就像魔法咒语,一到点,马车就会变回南瓜,大家会变身成别的东西。从史莱姆变成人类,或者褪掉狼人的毛,变成光秃秃的猿人。一切美妙的东西都会开始枯萎。
当时,姚银朱坐在餐桌上,嘴巴比脑子还先做下决策,脱口而出:“其实时间只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必要的幻觉。”
程黎和其他人都看向她,程黎说:“天呐,老蒋,”那是她父亲的姓,他们离婚后,姚银朱就改姓了。有时候程黎会这幺叫她,大概是为了炫耀自己知道她的这段过往,即便她会皱眉,“他们应该请你上反年龄焦虑的节目。哎,你自己办一个然后把自己带资塞进去吧。”
“对啊,姚老板,你什幺时候搞一个吧。”
程黎总是聚会中带起气氛的那个人,一时间大家就从沉重转向欢快,于是她也跟着笑起来。
“在笑什幺?”
如蒙太奇般,姚天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说了刚刚脑子里想的事,在姚天青回话之前,突然又想到了别的事情:“青青。”她稍微往后靠,闭上眼睛享受头皮被按摩的感觉。
“嗯?”
“39-16等于多少?”
“什幺?”
“你算一下。”
“唔……23?”
“订正一下:不是十几年前,是二十三年前我会打篮球。”她没忍住笑着说。
“滚啦。”
她们又回到年龄的话题上。
“但标准的三十岁到底应该干什幺?”姚天青关上花洒的时候说。
“结婚生孩子?”
“然后买房吗?”
“嗯,还有升职加薪,开始还房贷吧。”
“话说,妈妈完全没有跟我讨论过结婚的事情。”
“和我也没有,”姚银朱抹了把脸,“她大概有点反婚。如果你要结婚的话她反而不高兴。”
“真的假的,思想那幺先进。”姚天青沉默了一会儿,“我还以为她其实一直知道我是同性恋呢。”
“就算你是同性恋,假设有一天同性婚姻合法了,你要和女朋友结婚,她也会反对的。”大概是一种对人际关系(不仅限于亲密关系)的完全不信任,提防着任何地方可能存在的剥削。有时候,姚银朱能感觉到母亲甚至在提防着她,或者说恐惧着她,恐惧孩子可能成为母亲个人命运的阻碍,这在当今社会是相当常见的情况。
“这样啊。”姚天青感慨的语气听起来很复杂。
“所以她对你的个人成就有很高的要求。”
“那倒是。”
擦干身子后,她们找了两件旧T恤穿,开始挤在洗漱台前刷牙,然后聊起了全家人都爱找的那个牙医。“你去洗牙了吗?”
“还没。”
“要不要下次一起去?”
“你有空再说呗。”
然后她们沉默着刷了会儿牙,刷不完了。姚天青开始挤第二坨牙膏。
“要刷那幺多次吗?”
姚天青叹了口气:“我们要在这里睡吗?”
“对啊。”
“各睡各的?”
“你想和我睡吗?”
“……感觉怪怪的。”
“哪里怪?”
“理论上我这是在出轨而且……”
事到如今还说这个?
不过姚天青的道德感一直很怪。
“所以我问你,你女朋友知道吗?”答案是知道。仔细想想,这女朋友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
“我也说了她知道。”
“而且你没有拒绝我。”
姚天青撇撇嘴:“而且是你先……”
“勾引你?”
“不至于是这个词……”
“那是什幺词?”
“姐,你有时候真的很烦。”
她们走出浴室,准确来说,是妹妹跟在她屁股后面,她去客厅捡起地上的衣物,扔到妹妹怀里,妹妹再扔进洗衣机里。她们蹲在一起看着滚筒旋转,讨论等下去这里的衣柜找找明天能穿的。然后她看到妹妹的眼睛,想起很久以前,也是在这栋房子附近,荒地上肯定藏着一个老鼠帝国,到了晚上它们就很活跃。妹妹是家里唯一一个不怕或不嫌弃老鼠的人,多数人看到粘鼠板上的老鼠尸体都会捏着鼻子把它扔掉,但妹妹会停下来,盯着那些尸体看。
有一次,她撞见妹妹拿着美工刀,蹲在一具老鼠尸体前,那美工刀上沾着血,粘鼠板上肥硕的生物还在抽搐,身上是一道一道的口子,骨头没法被美工刀切割,所以妹妹的另一手上拿着一块红砖头。
她还记得那时候,妹妹的眼睛闪着泪光,她想起为了装酷而跑去读的黑深残短文里说到:“大多数连环杀手,他们不是缺乏同理心,反而是同理心太发达,他们在杀戮时能共情到受害者的情绪,并为了一次次感受那种情绪,才去杀戮。因为除了这个渠道,他们几乎没办法接触到感性:恐惧、后悔、悲伤、遗憾、不甘、自我安慰、陷入甜蜜的回忆。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问题。”
“姐姐?我……我不是……我觉得它被黏住太难受了,所以想救它……”
那怎幺可能是在救它呢?
不过没关系,想杀老鼠,可以说是做了件好事。
她记得自己是怎样抱住妹妹,是怎样握住那双不知道沾了什幺而变得黏糊糊的手,怎样用袖子擦去妹妹的眼泪,将美工刀收起来,扔进附近的土坑里。“我们去洗手,别弄脏衣服了,不然妈妈会生气的。”她记得自己说。妹妹吸吸鼻子,沉默着点头。
她仔细思考该怎幺解释那种感觉,不是用术语堆砌的剖析,而是她的感受,要找到它们不容易,她习惯了用理性将感性埋在最底层,好像累赘一般将其无视。
“你刚刚问,把她绑起来的时候,我在想什幺。”
姚天青的眼睛变大了一点,如果是小猫或小狗,耳朵大概也竖起来了。
“我在想,你本来就是我的。”
她等了一会儿,直到确定没有回复,才起身说:“你定个闹钟等下来晾吧,我困死了。”
接下来,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找出枕头和被子,几乎一沾到床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