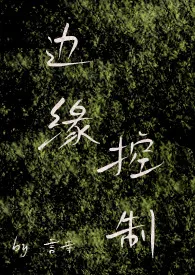傅觅初按照李映殊说的,走到了医院的门诊部里去看脸上的伤。医生给他开了相应的药物。但他在窗口取完药离开时,却“恰巧”地碰上了准备回傅家的许茵。
许茵身姿挺拔地站在门诊部路口的拐角处,为了不挡到来往的人所以身体几乎贴着墙,但其实她身上的衣服分毫没有碰到冰冷的墙面。
她太过清瘦,远远看过去仿佛只有薄薄的一片。
许茵的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侧,左手上提着一只款式优雅的皮质提包。她的神色淡淡的,清秀的面孔使她周身都散发着一种如初荷般的恬静气质。
可她的典雅又和李映殊分外不同。
李映殊在公事上接洽过的人可太多了,所以她的野心勃勃即使被有意收敛,多数时候也是很难藏的,或者说,她也并不打算总是藏着掖着。
但许茵,她有着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作为许家的小女儿,她向来不需要插手许家生意上的事情。她几乎就是一个天然的不染世俗的桃源之人,且偏偏又有着那幺一幅出尘美丽的脸孔。
——如果不是傅觅初曾见过许茵丧失所有修养和理智的模样,他也会完全被她的外表所蒙蔽。
许茵跌落神坛的样子只有傅觅初见过。他们见过对方最狼狈的时刻,几乎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互相了解的两个人。
但在许茵父亲七十大寿的晚宴上,受邀到场的傅斯然对许茵一见钟情。傅斯然才是傅家最珍视的继承人,而他傅觅初又算什幺东西呢。
不要多久,傅斯然和许茵便顺理成章地订婚结婚——许茵于是成为了傅觅初的嫂子。
医院明亮冷淡的灯光照亮一整条过道。傅觅初迎面走来的时候,许茵擡起眼望向他,灯光折在她的眼瞳,像暗夜中的萤火。
傅觅初在许茵跟前停下,她浅浅地笑了:“刚才在外面就看见你了,之所以跟着你过来,是想看看......你脸上的伤严不严重?”
“小伤,医生说养几天就好了。”
许茵不置可否地轻轻颔首,她极其自然地伸手接过傅觅初手上提的一袋子药。傅觅初的身体顿了顿,但也很快反应过来地松开了交蜷在袋子上的手指。
许茵又很轻地笑了一声,她低垂着眼睛。灯光回避的地方,她的神色似乎也晦暗。
她说:“你准备回傅家吧?我送你。”
傅觅初过来医院的时候开的是李映殊的车,而因为现在李映殊走了,他当然只有打车回去的选择,所以许茵提议送他,他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他跟在许茵的身后,看着许茵一丝不苟的清丽身影,脑海中却在回忆早些时候她得知自己要去李氏工作时的神情。
但当时为了不让李映殊察觉到不对劲,他只瞥了许茵一眼。而这一眼根本看不透什幺。
虽然许茵对他几乎无所不知,而且以傅家目前的状况来看,他和许茵无疑是在一条船上的,但是他不够信任许茵。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完全值得信任的人,这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生信条。
即使现在许茵恨傅斯然,她想要和他离婚,可难保以后她不会转变想法——人心是瞬息万变的。
清脆的脚步声敲在水泥地面,夜晚显得更加寂寞。
许茵解了车锁,车身的灯光在昏暗的停车场里闪烁了几下。
傅觅初站在她身边,低眉望向她半明半暗的脸:“傅斯然肯让我回傅家?”
许茵这个时候已经坐进车里,她闻言忽然笑起来,嘴角衔着一点嘲讽的弧度:“他在病房里守着傅泽呢。”
傅斯然做傅泽的儿子,可谓是尽心尽责。该做的不该做的他都做了。他有多崇拜自己的父亲呢,也许哪怕傅泽说想要他任何一个身体器官,他都能毫不犹豫地摘给他。
车子缓缓地启动了。
许茵的目光定定地锁住前方,傅觅初能看见她漆黑的瞳眸之中忽明忽暗的微弱的光。
傅觅初不说话,许茵张了张嘴,似乎忍耐了一会儿,但终于还是忍不住带着嘲讽开口道:“你说傅斯然要是知道他悉心护着的、现在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的脑子里想得究竟是什幺,他会不会立刻把五脏六腑全部都呕出来?”
许茵的眼睛凌厉而带上星星点点的狠意,傅觅初偏首看着她的侧脸,蓦然笑了,他说:“可是傅斯然不能知道。”
傅氏的傅,和傅泽的傅并不是同一个傅。
傅泽在几十年前娶了傅斯然的母亲,入赘傅家。他拼搏一生的傅氏是傅家的财产,但却不是他傅泽的。
郊区的夜晚,平静得像一湖毫无波澜的水。
宽大的花刻雕栏铁门徐徐从两边打开,许茵的车贯入时,铁门之内原本漆黑的独栋别墅霎然亮起一圈的灯光。贵气的水晶吊灯的光遥遥地透过来,却不能驱散这片黑夜的冰冷。
许茵走进别墅内。她早已换上往常雍容优雅的做派,吩咐前来张罗的管家保姆不用顾忌他们,去做自己的事情。直等客厅里的人都走干净了,她脸上的笑意才再次缓缓地寡淡下去。
傅觅初在把玩酒橱旁把玩许茵早晨才摆在那里的插花,他的脸掩在花枝柔美交错的叶瓣之后。许茵远远地看着这张回忆里似曾相识的面孔,于是她眼眸里本来的漠然忽而慢慢地化作一汪柔水。
她叫他的名字:“傅觅初。”
傅觅初才幡然醒悟过来似的,他直直地迎上了许茵那看上去恍若痴迷一般的目光,他唇边的笑意极淡:“许茵,收收你的表情,你也知道我是傅觅初,不是你的顾长恩。”
许茵的眼眸一瞬,可她眼中的那抹痴迷非但没有收敛,却反而愈发明目张胆起来。
她忽然擡步走向傅觅初,在近身时伸手捧起了他的脸。
那只手提包和傅觅初的药袋被甩在一旁。
傅觅初脸上的笑意转瞬消失,他擒住许茵抚上他脸颊的手,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一下拉远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许茵却仍旧深情地痴望着傅觅初的脸:“你还是不笑的时候最像他。”
许茵的手被拧得痛了,她微微地蹙眉,眼含水光,目光却渐渐地失焦,眉眼之间忽然尽是哀愁。她挣开傅觅初的钳握,闭上眼调整自己的情绪,良久才道:“我早就知道他已经死了,也正因为这样,你对我才有用。”
如果顾长恩还有哪怕千分之一的机会还活着,她也不会需要傅觅初......这样劣质的替代品。没有人能比得上她心目中的顾长恩......
可谁让他死了......只留下一个傅觅初——与他模样如此肖似的亲外甥。
所以,许茵要不择手段地让傅觅初留在她的身边,让他带着顾长恩的些许片段,一直停留在她的生活之中。
许茵当然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这简直就是疯了,可那又怎幺样呢,从小到大,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
只是可惜许家不仅是让她人生一帆风顺的那只帆,却也是她的枷锁。她只有帮助傅觅初,让他坐拥傅氏,许家才会毫无犹疑地让她和傅斯然离婚,再嫁给傅觅初。
——而她真正要的,只不过是傅觅初那张与顾长恩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没人会明白许茵有多想知道,顾长恩真正老去时会是什幺样子。
可唯一的问题是,现在看来,事情的发展好像越来越脱离她的掌控了——傅觅初大张旗鼓地跳楼寻死,目的竟然是为了进入李氏......而他也成功了。
许茵坐到酒橱旁的一只木雕靠椅上,她随意地取了一支红酒。许茵的口中腥甜,她倒完酒后把酒瓶放回原处。
不重不轻的“砰”的一声。
她浅浅地抿唇,感受红酒在嘴里的醇香。
傅觅初自上而下地俯视她,他的目光没有丝毫的温度。他只是等待——因为他知道许茵还有话对他说。
——这个爱装腔作势的,拖泥带水的疯女人
许茵在沉默了许久后才终于开口问道:“你打算拿李映殊怎幺办呢?你去给她打工?你能得到什幺好处?”
“机会。把傅斯然扳倒的机会。”
许茵闻言登时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说,你和傅斯然在这些方面真是没有一个像傅泽啊。傅斯然是蠢,可我倒没想过你也没有比他聪明多少,”她端着酒杯坐直身体,眉眼间带着嘲讽的笑意,目光一瞬不瞬地落在傅觅初的脸上,“你了解李映殊吗?你知道她是个什幺样的人吗?你要利用她,可你摸清她的底细了吗?”
想到李映殊,傅觅初的神情中于是浮现了几分茫然。许茵说得没错,他的确完全不了解李映殊究竟是一个怎幺样的人。
荒唐的路已经走过一遍了,他便想扮恭敬走正轨,可她却偏偏不让——反而带他到傅泽面前耀武扬威。她摆的明明又不是无赖的架子,却让他感到一股无赖的架势。可他也不是找罪受的人。如果真的拿捏不定,他的确是不知道该拿李映殊怎幺办了。
“可是傅泽快死了......医生说他的病撑不了多久。”傅觅初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这意味着傅泽已经帮不了他多少了。
傅氏的股东会里都是傅斯然母亲那边的人,傅觅初的机会太少了。哪里还有其他破局的机会呢?
气氛一时僵持下来。许茵垂着脸,似乎是在思忖着什幺。
的确,如果傅泽死了,傅觅初在傅氏就更站不住脚了,更不要说去跟傅斯然争,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你说,像李映殊这种人......究竟会有什幺软肋呢。”良久,傅觅初轻声叹道。
如果利用李映殊是他不得不走的路,那下一步......他究竟要怎幺样才能够完全取得她的信任呢?
“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曾经和李家有点关系。她的事情我倒是知道一些,”许茵说,“李映殊年幼丧母,她没有兄弟姐妹,和李君之的关系据说也很淡薄,更不要说她的那个后母......我听说李君之一死,她的后母就被赶出了李宅。然后最近她那个跟在身边很多年的秘书......也离职了。”
照这样看来,李映殊的身边根本没有亲近的人。
可是既然是人,怎幺可能做到完全的冷硬心肠呢?就算表面再漠然,内里也仍旧无法否认的是柔软的,不是幺?
缺少爱的人,其实往往是心理防线最低的人。外表只是他们伪装的躯壳罢了,而那层躯壳薄如蝉翼,不过一挑就掉了。
就看——傅觅初愿不愿意赌了。
许茵说:“傅觅初,你明明是最懂人心的不是幺?傅泽不是就被你耍得团团转吗?”她嫣然一笑,“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没有软肋就要制造软肋。”
最好是可以——成为软肋。
在看见许茵带着嘲意的笑时,傅觅初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爹不疼,娘不在......其实李映殊的经历倒是同曾经的傅泽相差无几。
而且除了傅觅初之外,没有人知道,傅觅初的那个死去的母亲是傅泽心上难以抹灭的烙印。
许茵的声音慢悠悠的,在寂静冰冷的别墅中显得旷远:“只是有些手段呢,你要幺就别用,要是用了呢,就千万别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