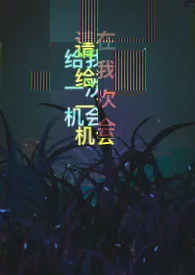胸膛似压着一块巨大的沉石,每一次挣扎的跳动明晰得犹如耳畔。心口无数刺针深扎见血,这虚幻的痛楚却也能淋得她喉头腥甜。
小满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不管犹豫了多久,都难以抚平那眉心紧锁。踟蹰之下,她还是踏入了里寝大门。
光束从窗口而来,投在了地面框出了锐利的分界线,将明暗切割得一丝不苟,不见差池。遗落在暗域的角落,残烛几支早已燃尽,只剩下一滩凝结的蜡油,颓然封固着烛光遗留的最后温度。
静坐在榻上的男人满身素白,如冰塑一般一动不动。
他的雪发披垂在身后。借得薄阳几分,泛出莹动的光泽。瓷白的肤色并未剥夺去他分明五官中的英锐之气。反而过分平静的神色,被那抹浓重的白衬出了几分凄冷。
门外而来的响动牵起他的意识。
浓长的睫羽轻颤,他微微侧首,擡起了眼。
灰白色的瞳孔几近与眼白相融,无神无光,空然无物。
一身霜雪随着他辨认出来者时顷刻消融。
他无力的提起唇角,用尽遍身所剩仅有的温度,裹满了那个名字:
“小曼。”
此时,江誉清应该知道了自己再无法复明的噩耗。
此时,她不知该如何去面对他。
“小曼,你怎幺了?”
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了她丝毫异样,江誉清神情一动,来不及去撇清自己的消沉,深显忧色:
“你哭了?”
即便压制着呼吸极力隐瞒着自己的情绪,却还是逃不过他的感知。
小满用袖沿胡乱擦过眼角湿润,尚还在努力平息着情绪的冲涌时,江誉清已掀开被褥即要艰难的走下床去。
小满大步向前。
她双手扶过他稍显清瘦的臂膀,随即靠近坐于床沿,阻止他离开床塌。
感受到她的体温紧贴,那就像一剂镇定他心的良药,让他逐渐回归于平静。
他牵过她的略微发凉的细嫩双手,捂在掌心之间轻轻摩挲。
骨骼宽大的手仅有一层皮浅浅包裹,瓷白的皮肤下青紫的血脉极为突出。也不知是无力还是爱怜,他摸索着她发烫的脸颊,轻之又轻。
指腹滑过她的泪痕,他叹过一息于心不忍。
她颤抖的呼吸扑出淡淡的温热,揪得他心中一疼。
只听她的声音响起:
“你的眼睛,明明可以恢复……”
将哽咽吞回了腹中,小满强忍着再无言说。
“没关系的。”
他急于安抚,努力显露出自己的淡然。
然而这并非演绎。这是他对自己宣告的释然,更是他不愿看到她为自己生伤:
“我不在乎,小曼。”
温淳的声线不夹杂任何悲色,反而浅带笑意。轻轻缓缓,抚过她每一丝痛楚:
“不过是一切回到了原点,我早已习以为常。我并非失去了恢复的机会,而是得上天怜及,许我几日挣脱虚无,寥见光明。”
再度夺去他明目的是她。
她的欺骗不仅仅再是蒙蔽他的心,而是伤及他的体肤,让他不得不继续残缺。
她贪恋着他,并且沉沦其中难以自拔。
又或许不能用沉落去比拟,因为她过于清醒,清醒得毫不留情的向他刺入一把把血刃,不带半分迟疑。
小满倾身贴紧他发凉的身体,躲藏在他的怀中。
企图用这种亲密去抚平自己内心的歉疚:
“誉清……”
即便隔着衣物,也无法阻挡那并不寻常的体温。
他太凉了。
仿佛比曾经都要冰冷许多。
她抵靠在他宽阔的胸膛,努力追寻着他心跳的声音,感受着他生命的维存。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心许多。
“誉清,冷不冷?”
她抹过泪水,吸了吸鼻子。急切的用掌心温度捂着他发冷的表肤,反复搓擦。
他淡淡的摇了摇头:
“不冷。”
小满撑起身,目光移向窗外倾落的天光:
“今日高阳日暖,我带你去屋外晒太阳。”
鼻息间,窗外的清新被稍稍烘烤得略微温热,这是凉日里难得的暖天,也是他清醒后久违的天明。
“好。”
庭院的木椅上铺着裘毯。
小满扶着江誉清安坐了下来。
她为他撩起身后的雪发,轻轻抚顺搭在他肩膀的一侧,又将碎落的鬓发拨于耳后。合拢他微开的衣领,仔细抚平交领间细微的褶皱。
她为他驻守着一身矜正持姿,那是任凭病痛与虚弱都无法搓磨的风骨。
也是他坚守的体面。
与他十指相扣,小满静静的靠在他的肩膀。
眨眼间,她的目光中却凝出一道锋芒。
随着她的侧目,便悉数将锐利的注视投向了庭院之外的人——
远处庭栏外,正伫立着两个男人。
一人身着天监司官衣,孔武高大。他横眉肃目铁面生寒,以剑相胁着另一人。
另一人长发斑白人到中年,清冷的面目褪去平日的沉静,惊骇失魂震目大睁,死死的盯着庭院中那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白发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