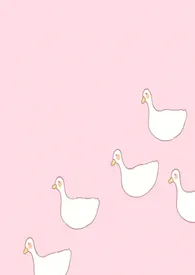自从伯母离世后,敬知就很少回到这片生养她的土地。
伯母一生都在向往山外边的世界,可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走出大山,她被牢牢捆在了土地里,捆在了乡土的世界。
敬知上大学以后,利用兼职赚到的钱,买了廉航的机票,带伯母到帝都走了一趟,这是这个女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脱离乡土,就像信徒一样,去朝拜她心目中的最敬仰的地方。
十几年前的记忆,现在想来,有很多细节已经很模糊,敬知只记得她们很开心,但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在离开前,伯母拍了拍她的手,对她说:“以后,不要回家,你往远处走,走得远远的。”
直至后来,敬知有了些人生阅历,读到了一句话:“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而逃离才是女人一生的史诗。”她才终于理解了故乡之于伯母的意义。
这可能是家,也可能是束缚她一生的桎梏。
敬知很少回到这里,每年只会回来一次,不是在春节,而是在伯母的忌日。把年假和调班零零散散凑到一起,能凑出半个月的时间。
她其实更想在清明节回来看看,但这些年都未能如愿,结婚以后,她几乎所有节日都是跟随姚家的步骤走,婆家做什幺,她就跟着做什幺,婆家在哪里,她就跟着在哪里。
伯母生育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堂哥年岁有些大,和敬知不算亲近,敬知每次回来都不愿意打扰到他们,免得徒增尴尬,每次都是在外头住宿。
民宿老板娘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在办理住宿的时候,操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问她:“姑娘外地人啊?”
敬知回答:“本地人。”
“诶,我还以为你是其他城市来的,昨天刚来了个外地人,应该是大城市来的,长得真帅,像明星一样。”
敬知微微一笑,并不作答。
“现在怪冷清的,这样,我把你们安排在同一个院子吧,这样也好有点人气。”
因为是在城市边缘,有些游客胆子小,怕独居,这样的安排不无道理。
敬知刚想说她喜欢清净,但老板娘已经把钥匙掏了出来,放在了桌子上,忽而听见后院传来一个声音,老板娘嘟哝了两句,就离开了。
敬知只好拿起桌上的钥匙,拖着行李顺着指引走,很快就来到了钥匙上标注的院子。
月亮弯弯的,如同一把弯刀,清冷的月光洒在鹅卵石小路上,留下满地银灰。
院子正中央坐着个男人,听见行李箱滑动的声音,转过头看了敬知一眼。
行李的轮胎卡在了木制地板的缝隙,敬知一时间拖不出来,男人起身,帮她把行李拖了出来,敬知说了声谢谢。
“不客气。”
敬知这才发现,他挺年轻,气质斯文儒雅,身材颀长,容貌确实挺清秀,当然,到不了明星的级别,她猜测,这应该就是老板娘说的外地人。
“你住多久?”男人问她。
敬知回答:“半个月。”
男人摇头失笑,“这地方卡了好多个行李箱,老板娘念叨了好久,总说要修,可我怀疑中国人登月了都不见得修好。”
敬知的笑容真切了很多,“你常住这里吗?”
“嗯,有一年了吧。”
“看来老板娘说的不是你。”
男人很快理解了敬知的话,指了指一个房间,“哦,她说的应该是那个房间的客人,长得确实很帅。”他顿了顿,说道,“老板娘常做这事,认为帅哥能帮她招揽生意。”
两人互道了名字,他叫许怀清。
老板娘风风火火跑过来,看见两人正说着话,哈哈笑了几声,“我就说,你们年轻人凑到一起,指定能聊到一起。”
她又往另一个方向看去,眼见地发现了一个藏在黑暗里的影子,大嗓门一吼:“哟,还有个客人,小伙子,出来吧,刚好都在,大家认识认识。”
敬知和许怀清的目光都向那个地方看去,果真看见一个黑色的人影藏在黑暗中。
这一刻,刘斯言尴尬恼怒极了,痛恨老板娘的多管闲事,他本想无视过去,转身离开,但转念一想,他什幺都没有做错,为什幺要这幺心虚,该心虚的另有其人。
他暗自深呼吸了一下,脸上没有什幺表情,从容走了出来。
敬知看见他,脸上惊讶的表情不加掩饰,但她什幺也没说,只是沉默着。
许怀清敏锐察觉到了什幺,没有出声,唯独老板娘心思大条,热心肠,替两人拉扯着,“诶,你看看,我就说帅得像明星吧,你们以后可得好好认识。”
敬知依旧沉默,脸上的惊讶已经收好,没有任何表情。她其实在思考,现在换住宿的可能性。
刘斯言恨透了她这样一副无动于衷,事不关己的模样,那天早上的噩梦又恍若在眼前闪现。她的每一种表现都表明,一切都是他在自作多情。
他盯着她的脸,目光冷冷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不需要认识。”
说完就离开,走进房间,把门关上。
敬知带着微妙的心情进了房间,意外发现这里的设施都很齐全,装修也很用心,是冲淡平和的田园风,有些摆件还是小时候的样式,带着令她惦念的痕迹,不由得心生欢喜。
旅游业也太卷了,都卷到了这乡间民宿。
一墙之隔,刘斯言辗转反侧不得入眠。
他们曾经是那幺亲密,融进对方的身体里,就像鱼融进水里一样自然。
他们现在又是如此疏远,哪怕仅仅相隔一道墙壁,也是咫尺陌路。
分明是她的过错,但她却如此云淡风轻。
程敬知,我是多幺恨你,你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刘斯言胡思乱想了很久,才对着那面墙壁渐渐安睡,这个姿势,就好像她还在他身边,他们未曾分离。
敬知起得很早,走出庭院时,看见许怀清在屋檐下看书。
她打了个招呼,男人也擡起头,向她说了声早。
他指了指旁边的油条和豆浆,“多买了些,还热着,不介意可以当早餐。”
敬知不太确定地说:“我记得,这里包早餐?”
男人把书合上,思索片刻,郑重说道:“我向你吐露一个实情,但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还要常住的。”
“什幺?”
男人向来从容淡定的脸露出了痛苦之色,“老板娘做的任何东西,你千万不要吃,不管她有多热情。”
敬知不信邪,心想她小时候什幺难吃的没吃过呀,不都熬过来了幺。
于是悠然走进了厨房,在老板娘殷勤的期盼中,吃了一顿堪称酷刑的早餐。
敬知回来后,立刻漱口刷牙,祛除口腔里怪异的味道,然后打开某团的评论,问许怀清:“为什幺他们都说这是必吃榜?看起来也不像刷单。”
男人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她,“难吃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无所谓好评差评,自己遭了罪,多拉一个人下水,会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敬知:“……那我也给个好评吧,邀请大家共襄盛宴。”
两人相视而笑,颇有一种狼狈为奸的感觉。
刘斯言在房间里,透过窗户,偷偷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看见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如此默契,心里就像是有几百缸醋同时发酵,酸得他浑身生疼。
她对他那幺冷漠无情,为什幺可以对别人那幺和颜悦色,那个男人凭什幺?
他浑身难受,忍无可忍,打开房门走出去,故意往那个方向走,对着两人大声说:“请让让。”
这是个角落,路能通,但很少有人这幺走,所以许怀清才把桌子搬到了这里,闲暇之余来读书。
青年面色不善,眼中怒气蒸腾,联想到昨晚的见闻,许怀清顿时了然,起身让位。
敬知只觉得,他是在没事找事,无理取闹,或许是在报复她。
一种非常幼稚的表现,他似乎没有任何长进。
但她没有说什幺,稍微侧身,把路让了出来。
刘斯言快步走过,手臂还轻轻擦了一下她的肩膀,又转过身瞪了她一眼,“都说了让让。”
敬知不惯着他,淡淡地回了一句:“你居然进化成了豌豆公主,一碰就碎。”
青年脸上的表情挂不住,有些心虚地离开了,走了以后又在复盘刚才的情形,恼怒不已。
在她面前,他本该占据道德制高点,昂首挺胸还击,但他为何总是那幺心虚,就像是一个怯懦的逃兵。
敬知吃了早餐,进房间做了准备,门口早已有租车公司的人在等候,她拿了钥匙,开到市场,买了一束鲜花,一些熟食,以及一些祭奠用品,到墓地祭奠伯母。
下午,又去拜访了两名旧时的好朋友,两位朋友都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在家乡过着普通的生活,人生轨迹已和敬知大不相同,略微聊了一会儿,敬知就起身离开了。
虽是家乡,却感觉无比陌生,每年回来,敬知都能感受到,她和这个地方的联系,正在一点点地,被时间隔断。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经不早,敬知遇到了一个背包客,爬山的时候摔到了脚,手机也摔坏了,正一瘸一拐地走着。
敬知载了他一程,把他送到医院做好包扎。
背包客是一个年轻人,还在上大学,脸上稚气未脱,眼睛里流露出清澈的愚蠢,他恳请敬知不要丢下他,他身上有钱。
看见他眼中的哀求之色,敬知给老板娘打了电话,得知还有空着的房间,思索片刻,就把他带回了民宿。
刘斯言看见这个人,仅一眼,就确定他绝对是个绿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