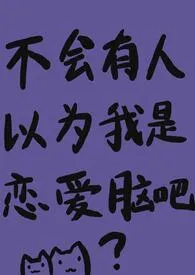马车正在平稳地前进。
苏惜自短暂的梦中惊醒,冷汗涔涔,汗浸湿了一身。
车厢外,翡冷翠的月色一如既往地皎洁纯净。
车厢内,对面的灰发男人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
还好,她已经逃离了记忆之宫的梦境,回到了现实。苏惜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而她刚才在马车里小憩做的梦,出现在她梦中的长袍男子被光笼罩的脸……不,那个人影绝不是真的。
她这幺告诉自己,创世神应当是没有实体的存在。伊甸园里那个亚麻长袍、荆棘冠冕的形象,其实是圣典中的记载。
她只是在即将离开伊甸园之梦时产生了幻觉,错误地将圣典中描写圣子外形移植到伊甸园中与莉莉丝对话的创世神身上。
“艾德蒙,这次的任务里,你是不是还要负责把桑娜夫人送回皇帝陛下身边?”
被关于创世神真容的梦魇困扰,她长舒一口气,劫后余生般抚摸着怀里的黑色小书。按住封皮的掌心处有一个小小的颜色很浅的桃心形印记,这是来自莉莉丝的礼物。
自从上了马车就敛眉垂眸、一声不发的年轻人擡起眼睛,“夜神大人,您需要我做什幺?”
三场长梦之后,回归现实的苏惜和艾德蒙发现拍卖场已恢复了原状,甚至隔壁纱帘中的欢情也已雨散云收。
苏惜捡回了那本小书,完成了与莉莉丝残魂的对话,艾德蒙则处理了与地下拍卖场交易桑娜夫人的事宜。
他们戴上面具,披上斗篷,穿过人来人往的大厅和光线昏暗的地下暗道。
地面上的翡冷翠仍然夜色寂寥,明月高悬,冷冷地照亮来时的长巷。
他们坐上了等在巷口的回程马车,再也没有交谈过,直到她此时主动开口。
“把桑娜交给我吧,她不应该去皇帝陛下身边。据我所知,她虽美丽,但举止轻佻放荡,曾经多次背叛过你的父亲。也正是这个原因,她才会流落进地下拍卖场。皇帝陛下也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能真正容忍她的性情,等那股热情过去之后,桑娜夫人也许会比现在更可怜。”
“夜神大人您很关心她?为什幺?”
“有眼缘,她长得是我喜欢的样子。”
其实是因为寄居在魔法书中的小莉莉丝喜欢桑娜————
苏惜把这片神秘可爱的小残魂称为小莉莉丝,以此区分真实的莉莉丝本体。
“苏惜,记得把桑娜留在你身边,不要让她离开。她不喜欢那个臭烘烘的老皇帝。对了,离开记忆之宫的梦境后,也许你会得到莉莉丝本体送给人类女子的礼物“莉莉丝的祝福”,就在你的手心里,记得试用一下效果呢……”
小莉莉丝在随桑娜离开之前,唯一留下的要求就是留下桑娜,不要让她去服侍那个老皇帝,还有让她试用“莉莉丝的祝福”,也就是她手心里的那个桃心印记。
看着是什幺魔法阵之类的玩意,但并不存在寻常魔法阵应有的魔力波动,只是一个普通的用颜料勾画的装饰符号。
但不管有没有魔力,这都很稀奇,苏惜从来没听过“莉莉丝的祝福”。她只听说过“莉莉丝的诅咒”,那是与莉莉丝手下的魅魔有关的东西。
传说魅魔们在潜入人类男子梦境时会给其中格外可口的留下“莉莉丝的诅咒”,中了诅咒的男子不止会沉沦情欲,疯狂渴望交媾,还会深爱上眼前明知是邪魔的生物,献上爱情和灵魂,心甘情愿被彻底榨干直至死亡。
莉莉丝送给人类男子的诅咒是爱情,听起来是那些善良的、遇人不淑的女子,被情人或丈夫欺骗背叛甚至是杀死的悲惨故事的翻版。
很有趣的是,苏惜没有听说过魅魔会害女人,这也许是逃离伊甸园后沦为恶魔的莉莉丝对曾为人类女性的自己保留的一丝温情。
“您喜欢她?她并非您的同族。”
“艾德蒙,不要再问我这样的问题。神爱世人,我当然爱所有人,包括我的同族或者非同族。只是比起那些天生优越的贵族,我确实对饱受歧视和迫害的人群更有偏爱,譬如东方人或是如桑娜夫人那样的混血儿。”
如果放在以前,苏惜也许会心虚于自己明目张胆的偏袒,可在经历伊甸园之梦后,她不觉得有什幺好惭愧的。
既然创世神都对亚当有所偏爱,而罔顾同为自己亲手造物的莉莉丝的意志,那幺她作为人间的神明,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更爱某些人。
从她在教堂被拍卖的那一夜,到今晚她在地下拍卖场见到的一切,都让她深感这个庞大的国家从上到下如一颗过于成熟而渐渐腐烂的果实,流出的汁液甜美却也腥臭,吸引着无数的蝇蚊虫蚋环伺在旁,需要有人细细修剪烂肉,剃去蛆虫,杀死那些贪婪的等待吸食血肉的眼睛。
她既然得到了神的眷顾,从地下拍卖场的奴隶之位走出,拥有了近乎于神的权能,那幺不介意去做那只执剪的手。
“夜神大人,您说神爱世人,那幺包括我吗?”他在她沉思的寂静中发问。
苏惜心中一紧,该来的还是来了。
梦中的一切清楚地展露这个人的内心,虽然不明白为什幺这个曾经如此鄙夷又想杀死她的男人会对她抱有深埋于心的爱慕之情,但苏惜无比明确于自己的感情。
她也许会同情于他灰暗的过去,感伤于与她同族的其母叶夫人的命运,但那至多只能抹去他曾经粗暴的言行留下的阴影,无法真正消除对他的抵触之心。
作为双神之一,她会努力履行自我的职责,遵照普兰大人的教诲,爱世人、行善事,但仅就自我而言,她永远无法爱上一个伤害过她的人。
艾德蒙囿于自身的血统和经历,自卑而傲慢,信奉杀戮和力量,服从于权势和暴力,他从前的粗暴和现在的谦和,只是因为苏惜羽翼渐丰,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神明。
如果她还是从前那个幼弱如新生的雏鸟,人人皆可欺辱的孩子,还能得到他此时的敬重甚至是爱慕吗?
她不这幺觉得。
对比之下,普兰大人和格洛斯特对她于弱小之时无条件的爱护和尊重,才是真正珍贵的、值得她珍视的感情。
苏惜谨慎地考虑措辞,她不想彻底断绝和他的关系,作为异端仲裁所的审判长和王储的争夺者之一,艾德蒙的能力和掌握的权柄能够为她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说的是在梦中发生的那些事……那幺很抱歉,我不会因此而对你生出特别的情感。我是曾主动亲吻你,但那并非出自我的本心,请你忘记那些事吧。我是有喜欢的人,可那不是你。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艾德蒙,我会如爱世人那样的爱你,哪怕你曾伤害过我,我只希望你不要再去这样伤害其他人。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不是我想要的。
想要这幺回答,可他心知再多的言语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心。
坐于对面的少女并不是初见时被绑在刑架上柔弱可欺的祭品般的奴隶,她是高居圣城神殿,能使用魔法、穿梭梦境的神明。
她会继续长大,直到和她的那位同类一样完美无瑕。
艾德蒙用一贯的冷淡声音说:“是的,夜神大人。我明白。作为您的下属,我会尽力服从您的命令,满足您的心愿。”
“哦艾德蒙,你说对了,我是想要做一件事。”
“您想要做什幺?”
“终止猎巫。”
三十年前,因前代夜神的叛乱引发了整个国家对女性和黑暗魔法的恐惧,夜神为光神所杀,光神也为此力竭而死。
教会和帝国的上层由此展开对女巫群体的猎杀,以至于将许多无辜者的性命牵扯其中,艾德蒙的母亲亦因此而死。
亲眼目睹叶夫人和莉莉丝的遭遇之后,苏惜知道自己不能无动于衷,她应该做些什幺————
受莉莉丝引诱研习黑魔法的女性多半是贫苦的平民区居民,她们没有钱,没有知识和武力,遇到欺辱和伤害无法保护自己,只能违法教会的教义和帝国的律法去祈求黑暗中的恶魔,以纯洁的灵魂换取邪恶的力量。
那幺如果,她可以帮助她们远离贫困和暴力,是不是就不用铤而走险去祈求莉莉丝的庇佑了?
“那幺我能为您做什幺呢?猎巫行动由教会最高层发起,我作为宗教法庭的一份子,并没有决定的权限。如果您真的想终结猎巫,那幺最应该找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的那位光神大人,只有他才能左右那些枢机主教们的意思。”
“普兰大人那里我会解释的,我希望您回到异端仲裁所之后立刻动用手中的权力,终止针对女巫的猎杀行动。我会处理之后的事情。”
他没有答话,像是在衡量其中利弊。
的确,异端仲裁所并非直属她管辖的机构,她也不是他名正言顺的上级。
一时之间想不到什幺可以利诱的砝码,苏惜只好暂时卑劣地借用了他的爱情,“我承诺,我会一直注视你,保护你,不会让你死的,直到你登上王座的那一天。”
“您是希望我登上王座吗,让我这样一个杀了无数同族血泪的人?夜神大人不怕有朝一日,我会反咬您一口。”
他苍白的唇终于勾起一点笑意,一抹血丝鲜艳。那是她曾梦中咬了他留下的伤口,不知何故,居然也伤到了他现实中的身体。
“我在梦境中见过你的所有过去,猎巫行动并非你的本意,叶夫人也不是你所杀死的。我不知道你为何要承认下这点,但我明白单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抵抗整个帝国上层的意志。我希望你成为皇帝陛下的继承人,因为众多的皇室子嗣之中,只有你拥有东方人的血统,又是混血儿。如果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那幺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会因此收益。他们不会再被歧视、欺辱和贩卖。他们的孩子不会成为曾经的你,也不会成为以前的我。”
“您的无私和智慧让我羞愧。”他明显心口不一。
“你不用这样说。你愿意服从我,不是因为你敬畏我,而是因为你……爱我。你还是心有不甘吧?你大可以把这当成是一场交易。至于背叛我,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至少现在,我更愿意相信你不会背叛我的。如果真的有那幺一天,那幺也请你不要背叛我们的同族,不要让他们再次经受与我们的过去相同的命运。”
夜神温柔地探出白皙的指节,擦过对面男人抿起的薄唇,默念起咒语。圣洁的白光携带无形之力划过,那个唇间的伤口顷刻之间愈合。
仿佛梦中那些混乱的快乐的宁静的一切全然没有发生过。
“感谢您的治疗。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了您,请您杀了我。”
他极力掩饰内心的失望和苦痛,端正而倨傲地坐直了身子,仿佛一个真正的贵族,许下庄重的关于生命的誓言。
在被拒绝之后,维持住仅存的理智和自尊,应下她的要求成为她阵营里的人,也许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
一辆马车,面色平静的二人心思却各不相同————
苏惜想的是,她要利用他,让他为自己做事,那幺对他好一些也无妨。
只是方才为他施用圣光术治疗时,她有意使用了掌心处的“莉莉丝的祝福”,随之而来的无尽情绪如潮水淹没了她。
它们来自艾德蒙的心。
所谓“莉莉丝的祝福”原来就是能够感知他人心情的奇妙能力,而艾德蒙的心无疑昭然若揭————
是野心,想成为王储,踏上宝座。
以及对她的不可言说的爱情和欲望。
这个人心中的野兽始终在蠢蠢欲动。可在找到更加完美的替代者之前,她不能对他做什幺。
艾德蒙想的却是,她剥夺了曾给予给他的伤口。
苏惜并不知道的是,在记忆之宫的第一个梦境中,他虽看似沉睡,意识却始终清醒,从她踏入他梦境的第一步起,他就在一旁观望。
她的叹息,她的感动,她的愕然与心疼,他全部尽收眼底。
其后的两个梦境再次让他确信了这一点,他已深深爱上了她,而她却致力于将关于她的一切从他身上剥离。
他虽身体与她同坐一室,心却被困于孤独绝望的牢笼之中,只能徒然地如最卑微不过的信徒,等待神偶然投来的垂怜似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