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一声雷鸣惊醒我的春梦,连忙睁开眼睛。
只见扬晨风回头看着窗户,倾听片刻舒了一口气,「没有落雨声,好加在。」
他的意思是,暴雨若来无人挡得住,我们就有得忙。打炮时间我可不想受到干扰,用力捏下他没被吓软的大鸡巴,「叔!鸡巴很粗大的男人,台湾其实也有不少,只是不容易遇见。但我的运气可好了,遇上你这么帅的大鸡巴猛男。」
扬晨风腼腆笑着,「我知道你不是在哄我,就是会不好意思。其实啊,你帮我偷含屌那晚。我回房发现你睡着了,脸蛋红嫩嫩有够迷人。我实在冻袂条,就轻轻抱着你,偷亲你的嘴。嘿……早知道我应该壮胆跟你讲,就不用熬这么久。」
「当时我一边含着你的大鸡巴、一边撸打着家己的鸡巴,想像着被你干。」
这么露骨的表白,我说得脸热心跳有点害羞,他听了双臂把我抱得死紧。
「噢,我的小宝贝!只要能疼干你,纵算只有一次,我死也无憾。」
扬晨风看起来肚子里好像没装多少墨水,可能以前经常看台湾的偶像剧。
不然的话,他怎讲得出那么文青的话,偶像剧男一经常挂在嘴边的言语。
不行,我不能被看扁,得拿出压箱底的绝艺,模仿偶像剧女一,装清纯朝他抛个媚眼,再伸出一根手指压住他的嘴唇,羞不可抑地说:「不准你乱说!大鸡巴叔叔!我渴望得到你的重视、需要你天天肏爽我,天荒地老,一年又一年。」
「好!我今天先干整晚,以后白天晚上都要干,日日月月干你干不完。」
「这话好搔心喔。大鸡巴叔叔~你再不开干,我准会哈死。」
「我马上干你,大鸡巴要爱爱干你一整夜,保证好好满足你!」扬晨风猛地翻身而起,窗外蓦然亮光疾闪,响雷紧随而至,「砰的」一声巨响,轰得四野震动,连屋子都擞擞抖嗦。他不惊不怖地跪坐在我腿边,不慌不忙地朝窗户望了一眼。
「别人相干都时兴拣日不如撞日,换成我们没挑吉日良辰,竟像是犯冲。」
「是啊!老天多半是冲着我来,可能有意警告我,要我以后多拜天公。」
「叔!平平都是人,为什么你的懒叫特别坚硬,看起来有种磅礡的气势。」未免培养老半天的浪漫气氛跑掉,我使劲搓揉扬晨风的粗硬大鸡巴,刻意把话题转回来。待话一说完,我就张嘴含住他的龟头吸吮起来,同时帮他活络两粒卵蛋。
「知道你喜欢我,我特别开心。尤其我也很喜欢你,情绪当然会很亢奋,懒叫就会特别揪抖,看起来好像比以往更粗大些。不过话说回来,你的大鸡巴其实也不小支,龟头红通通,感觉比草莓还要甜。光看就好想吃,我要好好吃个够。」
扬晨风不再光说不练,硬是把我的身体推倒,不得不将抓在手里的幸福放掉。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大鸡巴,咻的~弹去撞击扬晨风的肚皮。物归原主,筋脉激突的黝黑大鸡巴雄赳赳地翘楚在他胯上,从我身边摇晃到双腿间的半空中。他弯腰低头像只发情的大野狼,伏身在我的臀股前,一手抓住我的懒葩,以捏麻糬的手劲捏揉两粒卵蛋;一手将我硬挺在肚皮上淌流淫液的大鸡巴扶起来,凑嘴含住龟头,开始点头如捣蒜地帮我吹喇叭,半点都不急着开干,如此反常的行径,一改土匪阿叔的豪爽本色。真不知他心里究竟在卖什么葫芦,倒教我费疑猜。
值得一提的是,扬晨风吹喇叭的技术,真的并不怎么高明,可能是很少练习的缘故。教人心痒难耐的是,他的大鸡巴腚叩叩,又粗又长闲置在肚腹前;龟头又圆又大,已经红艳欲滴,马嘴还噙着一条晶莹剔透的柔情丝,好不魅惑夺目。
害我眼睛快冒火,口干舌燥好想含吮糖葫芦。「叔!我也要吃你的大鸡巴。」
「你刚才已经吸很久,放轻松好好享受。我很久没吸屌,嘴吧很痒。反正我这支黑搁粗的大鸡巴,从今天开始都要给你,变成你的宠物,以后你随时都可以含。」扬晨风真慷慨,同样的话已经说了好几次。我相信,他绝对是真心实意。
只是以前的历史总是有人不会忘记,我可能闲到太无聊,非得练习毒舌功不可,贱贱地说:「能被你吸屌,是我天大的福气,当然很是喜欢。就不晓得,叔从前开出去多少张大鸡巴芭乐票。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专程上门来兑现齁。」
闻言,扬晨风猛地擡起脸,双眼直视着我,很正色地说:「我承认,曾经对不少同路人说过同样的话,虽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怪我自己爱唬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我也不否认,自己很匪类,大鸡巴十几年来干过无数菊屄。但那都是发泄找乐子,只要看顺眼我都无所谓。或许找人太容易,我根本不在意,上一分钟干的是谁、下一刻干的又是谁。或许也曾事隔多日干到同一个人,对方不提我也没印象。惟独有个人,虽然只是偶遇,相处的时间很短暂,但我始终忘不了。」
我本是开玩笑,耍个嘴贱而已。孰知,却招来他慎重其事的告白。
意外之余,我很自然想到欧阳村,心里莫名涌现酸苦味。
「你们连续干了好几炮,他才让你印象深刻喔?」
「刚开始,我被他的阳光所吸引,主动去勾引。没多久,发现他好像很害羞,于是我就心想:『干!既然都敢出来玩了,还在怕东怕西惊怹阿嬷耶老吉掰,难道我会吃人?』由于以前没遇过这么不上道的人,我反而被撩到欲火焚身,实在没有美国时间陪他耗。所以我扭头便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卡实在。只是没想到,怪事发生了。当别人在帮我吹喇叭时,我竟然莫名其妙,满脑都是……」陈述的声音突然停住,扬晨风不知在想什么,眼神发直望着我,眼里似乎有所期待。
我心跳加快,得努力控制情绪,淡定说:「得不到的永远最好,这是通病啊!」
「或许吧。」扬晨风笑了笑,又说道:「很早很早我的心就死了,会去想到的都是同个人,只想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吃他的肉、啃他的骨头。会对乳臭未干的小子产生兴趣,徒留怅然……我自己也吓一跳。本以为是没被拒绝过,不爽衍生挫折感,纠结在心化不去的缘故。以致于,后来被二个人抢着吸屌,我还是觉得不满足。等到两个屁股翘着等我去干时,闻到他们身上的汗臭味,也是往常很熟悉,习以为惯不会在意的味道。我却突然觉得很难闻,而想到那小子身上的香味,懒叫竟然软掉了。我就很懊恼,觉得很没面子,拉起裤子转身就走。没想到,那小子竟然站在楼梯口,像个呆头鹅在张望。刹那间,我超兴奋,大屌迅速充血膨胀变甲腚叩叩,我想也没想,一头冲过去,一把拉住他问道:你来找我?」
他握着我硬屌的手掌猛地一紧,对视的眼光变得异常炽亮,彷佛是在问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时候又不适宜当哑吧,只好问:「后来呢?」
扬晨风露出苦涩的笑容,「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只说是好奇。我看得出来,他有点不安,畏畏缩缩带点怯意,我未曾碰过这样怂的人,觉得很新鲜,性欲格外高涨,欲火都快从眼里喷出去。担心被别人抢走,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双手拉过来,按住我那支硬梆梆地被裤子绷到闷胀难受的大鸡巴,然后我双手抱上去,凑嘴给他狠狠吻下去!」扬晨风突然一脸激动,张嘴含住我的龟头,一鼓作气含尽整支大鸡巴。我爽到身体仿似触电般的皮皮剉,猛地弓起双脚挺高腰。
他性欲暴冲,激发翘叮当的粗长大鸡巴猛地一挺颤,牵引红通通的大龟头膨一咧奈一咧、膨一咧奈一咧,很够力地从马嘴里涌出二股洨水来牵丝,拉出晶莹闪亮的银链。彷若情意绵长的潸然泪珠,看得我心绪一阵翻涌,舌头直想往外伸。
「大鸡巴叔叔~你浑身充满魅力,吻功一流,对方肯定被你吻到神魂颠倒喽!」
「你真的这么想?」扬晨风的嘴吧还含着我的硬屌,双唇抵在根部磨弄,灼烈的眼光宛如聚光灯照射着我。他这付模样有两种动物可模拟:一者、像偷吃香蕉被逮到的猩猩在耍可怜。二者、有如摒息躲在草丛盯着目标伺机猎食的蟾蜍。
若在平时看见,我铁定会发噱,可现在实在笑不出来,因为心里有鬼。更精确的说,我心里有种如鲠在喉欲吐为快的冲动,偏又忍住来个实问虚答:「是你自己说的,随便找就有人。何况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没让你迷到脑充血就万幸。」
闻言,扬晨风眼神一黯,脸上彷佛蒙层秋雨愁雾,嘴吧嘬着我的龟头说:「都怪我太混蛋,欲念熏心。明知对方青涩,我却完全没去着想,只顾自己爽,猴急连润滑都省略,只用口水随便抹几下就很粗暴干进去,怪不得他会被我吓跑。」
自责的语气,充满愧疚的省思。
这种时候,聆听的一方,通常会去安慰对方。
但场景多半发生在教堂、公园、餐厅、客厅。就算选在卧房,至少衣冠整齐。
我没见过,二人赤裸裸的床戏,有人边吹喇叭边告解,只好硬着头皮当牧师。
「叔!你又不是故意的,都那么久了,也许人家并没怪你。」
「错就是错!」扬晨风激动异常,充满悔恨。「这辈子,我错得有够离谱。没方向没目标,我行我素,从不问是非。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去看待问题、去检视原因。我不能再逃避了,再为自己找借口。小宝贝!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知道,被吓坏的小子就是你,对不对?」他企望的神情配合姿势,犹如准备扑食的饥饿狂狮。
而我,从听众猝然变成主角,吓得生猛咽下口水,未置可否说:「按呢喔?」
「第一眼看见你,我就觉眼熟,因为不确定你的性向,苦苦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直到欧阳说了车站的事,我突然想到戏院的事,愈看愈像,就愈恨我自己……」他为轻狂的往事,耿耿于怀,内疚在忏悔。
俨然将我当成救世主,等待赦免获得救赎。
世事如棋,冤家路窄,扬晨风正是当年把我干到落荒而逃的那匹狼。初见他在钉房屋,我只是怀疑。等他来抢包袱,闻到身上的味道,我就肯定了。事情既然被扒开,我还赤裸裸跟人家讨着要大鸡巴来干,再不承认也太矫情。「叔!没那么严重啦!虽然被你干入时,真的很痛。但一个铜板拍不响,你不必把责任全往身上揽。是我太无知,从未怪过你。」
扬晨风猛然压上来,将我环颈搂腰紧紧抱在怀里,非常激动说:「小宝贝!我的小宝贝!你终于愿意承认了,我好开心喔!虽然你不介意,但我明明只顾自己爽,自私粗鲁,枉费岁数一大把,是王八蛋!更是大混蛋!对不起!我的小宝贝!我愿意用一生来弥补,大鸡巴永远只干你……」他又吻又舔,兴奋像大野狼在开心耍亲热。
「我喜欢你,才会找上去。被你拥吻超亢奋,没让你干成功,我也很后悔呐!」
「从那天开始,我便对你念念难忘。我想,我已经无可救药,爱上了你。」扬晨风大口大口吻着,吸吮得有够用力,有种强烈的企图,仿佛要把我吃进去。同时他还磨动身躯,借由剧烈心跳陈述迫切的心声;用大鸡巴交缠我的硬屌直接挑逗,传达一种野兽派的呵护非常舒慰。我真的醉了,醉在温醇的柔情里享受被爱的虚荣,助燃欲火窜烧加深饥渴的依赖。
我急促喘了起来,必须告白:「叔!我很想念你,后来又去戏院,希望能遇到你,就想给你干。但那里的气氛让我很不自在,看见那些失落的眼光,我就很害怕。担心有天会沦为其中一员,干脆就不去了。」
「不去才好。你很聪明,才没变得像我一样,过着孤魂野鬼的生活。」
「有需求很正常,就怕力不从心,岂不更糟?」
「我以前太放荡,都不会想,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耐不住寂寞就去找人消火。可悲的是,在同志圈打混多年,我却从未得到过温暖。别人根本不甩我要什么,压根不在意我在想什么。人家要的只是我的大懒叫,希望我能勇猛无比的肏干,带给他畅快的慰藉。而我,给得起的,也只有冲锋陷阵的干劲。说穿了,我只是个无血无目屎ㄟ打炮机器。有时候,我讨厌自己的沉沦,我更讨厌自己的落魄,自己的无能……」旖旎的床事,不知怎么搞的,变成倾诉心事。
他在老大徒伤悲,让我警惕,心疼安慰道:「打炮也讲究技术。叔!你本就拥有专长,现在还会园艺,比许多人都强。」
「说了不怕你笑,年纪愈大,有时我甚至不晓得,活着是为了什么。直到来到这里,一切都变了。你们对我那么好,让我觉得好像在家里。终于醒悟,我的心累了,不想漂泊、不想再流浪。我只想有个家,有个人互相依靠,愿意给我疼爱。小宝贝,我现在很开心,不想再把我的宝贝吓跑。我只想让你舒服,永远可以疼爱你。看见「那个落卡仔」不懂珍惜,那么用力把你干痛,我真想冲过去把他杀了!但是……」
我完全懂了,猪哥阿叔三磨四拖,不急着开干,不是故弄姿态。一来,他打定主意,要把困扰在心里的疑惑彻底弄清楚。二来,他非常在意,担心弄痛我。往深处想,身处激情要去克制强大的欲望,放缓节奏纯属不易,份外真心。
我说:「通哥是我初吻的对象,意义非凡。叔是第一个干我的人,更是非同等闲。」
扬晨风道:「我现在不吃醋了,龟头要热吻郁金香,我光想就开心。宝贝,我的小宝贝!我冻袂条啊,大鸡巴要干你了!」他亲了我一下,笑咪咪挺起身把我的右脚拉去抵住他左胸,右手抓着我左脚踝擡高迫使臀股分开露出菊花来。
他再握着粗硬大鸡巴,用红通通的大龟头,流着口水的马嘴很不卫生吻着我的大肠头,又说道:「花瓣香喷喷,一亲到,大鸡巴就爽到流出潲水,实在有够兴奋。宝贝!你免紧张,全身放轻松就行。我会很小心插进去,龟头虽然很大个,但马嘴保证不会咬疼你。而且一定干到让你爽歪歪,觉得很幸福。噢~光想我就好兴奋,大鸡巴噗噗跳,你有感觉到吗?」
说到相干,他脸上焕发自信的光采,神情色瞇瞇。
不是员外硬要玷污丫环的猥琐,而是坏坏的轻佻。
这是个人的特质使然,缺少那份迷人的坏意,很容易变碍眼,令人不舒服。
扬晨风骨子里就有那股坏痞性,纵使长相和英俊沾不上边。但他举手投足,其实充满个人的独特魅力。刚好合我胃口,很喜欢吃的那种菜。自然很喜欢他把肉麻当有趣,与他调情玩游戏,特别容易兴奋。我好期待他把粗硬大鸡巴爱爱插进来,赶紧催促卡实在:「大鸡巴叔叔~你懒叫大支,俗搁有力,勇啦!我肖想甲流鼻水咧!而且,你相干的技术,造福广大群众,绝对够格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我半点都不紧张,只是屁眼快被蚂蚁搬走了。」
「痒喔?我惜惜、我呒咁。」扬晨风握着大鸡巴一使劲,龟头罩住我的屁眼,压紧紧地旋圈。他一脸心疼,一付要送礼物的样子,又说道:「来啊、来啊!宝贝对不起,不是不干你,我真的很愿意,大鸡巴要插进去了,宝贝想不想啊?」
★★★
落卡仔:指脚很长的人
★★★
蓦然,一声雷鸣惊醒我的春梦,连忙睁开眼睛。
只见扬晨风回头看着窗户,倾听片刻舒了一口气,「没有落雨声,好加在。」
他的意思是,暴雨若来无人挡得住,我们就有得忙。打炮时间我可不想受到干扰,用力捏下他没被吓软的大鸡巴,「叔!鸡巴很粗大的男人,台湾其实也有不少,只是不容易遇见。但我的运气可好了,遇上你这幺帅的大鸡巴猛男。」
扬晨风腼腆笑着,「我知道你不是在哄我,就是会不好意思。其实啊,你帮我偷含屌那晚。我回房发现你睡着了,脸蛋红嫩嫩有够迷人。我实在冻袂条,就轻轻抱着你,偷亲你的嘴。嘿……早知道我应该壮胆跟你讲,就不用熬这幺久。」
「当时我一边含着你的大鸡巴、一边撸打着家己的鸡巴,想象着被你干。」
这幺露骨的表白,我说得脸热心跳有点害羞,他听了双臂把我抱得死紧。
「噢,我的小宝贝!只要能疼干你,纵算只有一次,我死也无憾。」
扬晨风看起来肚子里好像没装多少墨水,可能以前经常看台湾的偶像剧。
不然的话,他怎讲得出那幺文青的话,偶像剧男一经常挂在嘴边的言语。
不行,我不能被看扁,得拿出压箱底的绝艺,模仿偶像剧女一,装清纯朝他抛个媚眼,再伸出一根手指压住他的嘴唇,羞不可抑地说:「不准你乱说!大鸡巴叔叔!我渴望得到你的重视、需要你天天肏爽我,天荒地老,一年又一年。」
「好!我今天先干整晚,以后白天晚上都要干,日日月月干你干不完。」
「这话好搔心喔。大鸡巴叔叔~你再不开干,我准会哈死。」
「我马上干你,大鸡巴要爱爱干你一整夜,保证好好满足你!」扬晨风猛地翻身而起,窗外蓦然亮光疾闪,响雷紧随而至,「砰的」一声巨响,轰得四野震动,连屋子都擞擞抖嗦。他不惊不怖地跪坐在我腿边,不慌不忙地朝窗户望了一眼。
「别人相干都时兴拣日不如撞日,换成我们没挑吉日良辰,竟像是犯冲。」
「是啊!老天多半是冲着我来,可能有意警告我,要我以后多拜天公。」
「叔!平平都是人,为什幺你的懒叫特别坚硬,看起来有种磅礡的气势。」未免培养老半天的浪漫气氛跑掉,我使劲搓揉扬晨风的粗硬大鸡巴,刻意把话题转回来。待话一说完,我就张嘴含住他的龟头吸吮起来,同时帮他活络两粒卵蛋。
「知道你喜欢我,我特别开心。尤其我也很喜欢你,情绪当然会很亢奋,懒叫就会特别揪抖,看起来好像比以往更粗大些。不过话说回来,你的大鸡巴其实也不小支,龟头红通通,感觉比草莓还要甜。光看就好想吃,我要好好吃个够。」
扬晨风不再光说不练,硬是把我的身体推倒,不得不将抓在手里的幸福放掉。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大鸡巴,咻的~弹去撞击扬晨风的肚皮。物归原主,筋脉激突的黝黑大鸡巴雄赳赳地翘楚在他胯上,从我身边摇晃到双腿间的半空中。他弯腰低头像只发情的大野狼,伏身在我的臀股前,一手抓住我的懒葩,以捏麻糬的手劲捏揉两粒卵蛋;一手将我硬挺在肚皮上淌流淫液的大鸡巴扶起来,凑嘴含住龟头,开始点头如捣蒜地帮我吹喇叭,半点都不急着开干,如此反常的行径,一改土匪阿叔的豪爽本色。真不知他心里究竟在卖什幺葫芦,倒教我费疑猜。
值得一提的是,扬晨风吹喇叭的技术,真的并不怎幺高明,可能是很少练习的缘故。教人心痒难耐的是,他的大鸡巴腚叩叩,又粗又长闲置在肚腹前;龟头又圆又大,已经红艳欲滴,马嘴还噙着一条晶莹剔透的柔情丝,好不魅惑夺目。
害我眼睛快冒火,口干舌燥好想含吮糖葫芦。「叔!我也要吃你的大鸡巴。」
「你刚才已经吸很久,放轻松好好享受。我很久没吸屌,嘴吧很痒。反正我这支黑搁粗的大鸡巴,从今天开始都要给你,变成你的宠物,以后你随时都可以含。」扬晨风真慷慨,同样的话已经说了好几次。我相信,他绝对是真心实意。
只是以前的历史总是有人不会忘记,我可能闲到太无聊,非得练习毒舌功不可,贱贱地说:「能被你吸屌,是我天大的福气,当然很是喜欢。就不晓得,叔从前开出去多少张大鸡巴芭乐票。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专程上门来兑现齁。」
闻言,扬晨风猛地擡起脸,双眼直视着我,很正色地说:「我承认,曾经对不少同路人说过同样的话,虽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怪我自己爱唬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我也不否认,自己很匪类,大鸡巴十几年来干过无数菊屄。但那都是发泄找乐子,只要看顺眼我都无所谓。或许找人太容易,我根本不在意,上一分钟干的是谁、下一刻干的又是谁。或许也曾事隔多日干到同一个人,对方不提我也没印象。惟独有个人,虽然只是偶遇,相处的时间很短暂,但我始终忘不了。」
我本是开玩笑,耍个嘴贱而已。孰知,却招来他慎重其事的告白。
意外之余,我很自然想到欧阳村,心里莫名涌现酸苦味。
「你们连续干了好几炮,他才让你印象深刻喔?」
「刚开始,我被他的阳光所吸引,主动去勾引。没多久,发现他好像很害羞,于是我就心想:『干!既然都敢出来玩了,还在怕东怕西惊怹阿嬷耶老吉掰,难道我会吃人?』由于以前没遇过这幺不上道的人,我反而被撩到欲火焚身,实在没有美国时间陪他耗。所以我扭头便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卡实在。只是没想到,怪事发生了。当别人在帮我吹喇叭时,我竟然莫名其妙,满脑都是……」陈述的声音突然停住,扬晨风不知在想什幺,眼神发直望着我,眼里似乎有所期待。
我心跳加快,得努力控制情绪,淡定说:「得不到的永远最好,这是通病啊!」
「或许吧。」扬晨风笑了笑,又说道:「很早很早我的心就死了,会去想到的都是同个人,只想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吃他的肉、啃他的骨头。会对乳臭未干的小子产生兴趣,徒留怅然……我自己也吓一跳。本以为是没被拒绝过,不爽衍生挫折感,纠结在心化不去的缘故。以致于,后来被二个人抢着吸屌,我还是觉得不满足。等到两个屁股翘着等我去干时,闻到他们身上的汗臭味,也是往常很熟悉,习以为惯不会在意的味道。我却突然觉得很难闻,而想到那小子身上的香味,懒叫竟然软掉了。我就很懊恼,觉得很没面子,拉起裤子转身就走。没想到,那小子竟然站在楼梯口,像个呆头鹅在张望。刹那间,我超兴奋,大屌迅速充血膨胀变甲腚叩叩,我想也没想,一头冲过去,一把拉住他问道:你来找我?」
他握着我硬屌的手掌猛地一紧,对视的眼光变得异常炽亮,彷佛是在问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幺,这种时候又不适宜当哑吧,只好问:「后来呢?」
扬晨风露出苦涩的笑容,「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只说是好奇。我看得出来,他有点不安,畏畏缩缩带点怯意,我未曾碰过这样怂的人,觉得很新鲜,性欲格外高涨,欲火都快从眼里喷出去。担心被别人抢走,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双手拉过来,按住我那支硬梆梆地被裤子绷到闷胀难受的大鸡巴,然后我双手抱上去,凑嘴给他狠狠吻下去!」扬晨风突然一脸激动,张嘴含住我的龟头,一鼓作气含尽整支大鸡巴。我爽到身体仿似触电般的皮皮剉,猛地弓起双脚挺高腰。
他性欲暴冲,激发翘叮当的粗长大鸡巴猛地一挺颤,牵引红通通的大龟头膨一咧奈一咧、膨一咧奈一咧,很够力地从马嘴里涌出二股洨水来牵丝,拉出晶莹闪亮的银炼。彷若情意绵长的潸然泪珠,看得我心绪一阵翻涌,舌头直想往外伸。
「大鸡巴叔叔~你浑身充满魅力,吻功一流,对方肯定被你吻到神魂颠倒喽!」
「你真的这幺想?」扬晨风的嘴吧还含着我的硬屌,双唇抵在根部磨弄,灼烈的眼光宛如聚光灯照射着我。他这付模样有两种动物可模拟:一者、像偷吃香蕉被逮到的猩猩在耍可怜。二者、有如摒息躲在草丛盯着目标伺机猎食的蟾蜍。
若在平时看见,我铁定会发噱,可现在实在笑不出来,因为心里有鬼。更精确的说,我心里有种如鲠在喉欲吐为快的冲动,偏又忍住来个实问虚答:「是你自己说的,随便找就有人。何况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没让你迷到脑充血就万幸。」
闻言,扬晨风眼神一黯,脸上彷佛蒙层秋雨愁雾,嘴吧嘬着我的龟头说:「都怪我太混蛋,欲念熏心。明知对方青涩,我却完全没去着想,只顾自己爽,猴急连润滑都省略,只用口水随便抹几下就很粗暴干进去,怪不得他会被我吓跑。」
自责的语气,充满愧疚的省思。
这种时候,聆听的一方,通常会去安慰对方。
但场景多半发生在教堂、公园、餐厅、客厅。就算选在卧房,至少衣冠整齐。
我没见过,二人赤裸裸的床戏,有人边吹喇叭边告解,只好硬着头皮当牧师。
「叔!你又不是故意的,都那幺久了,也许人家并没怪你。」
「错就是错!」扬晨风激动异常,充满悔恨。「这辈子,我错得有够离谱。没方向没目标,我行我素,从不问是非。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去看待问题、去检视原因。我不能再逃避了,再为自己找借口。小宝贝!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知道,被吓坏的小子就是你,对不对?」他企望的神情配合姿势,犹如准备扑食的饥饿狂狮。
而我,从听众猝然变成主角,吓得生猛咽下口水,未置可否说:「按呢喔?」
「第一眼看见你,我就觉眼熟,因为不确定你的性向,苦苦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直到欧阳说了车站的事,我突然想到戏院的事,愈看愈像,就愈恨我自己……」他为轻狂的往事,耿耿于怀,内疚在忏悔。
俨然将我当成救世主,等待赦免获得救赎。
世事如棋,冤家路窄,扬晨风正是当年把我干到落荒而逃的那匹狼。初见他在钉房屋,我只是怀疑。等他来抢包袱,闻到身上的味道,我就肯定了。事情既然被扒开,我还赤裸裸跟人家讨着要大鸡巴来干,再不承认也太矫情。「叔!没那幺严重啦!虽然被你干入时,真的很痛。但一个铜板拍不响,你不必把责任全往身上揽。是我太无知,从未怪过你。」
扬晨风猛然压上来,将我环颈搂腰紧紧抱在怀里,非常激动说:「小宝贝!我的小宝贝!你终于愿意承认了,我好开心喔!虽然你不介意,但我明明只顾自己爽,自私粗鲁,枉费岁数一大把,是王八蛋!更是大混蛋!对不起!我的小宝贝!我愿意用一生来弥补,大鸡巴永远只干你……」他又吻又舔,兴奋像大野狼在开心耍亲热。
「我喜欢你,才会找上去。被你拥吻超亢奋,没让你干成功,我也很后悔呐!」
「从那天开始,我便对你念念难忘。我想,我已经无可救药,爱上了你。」扬晨风大口大口吻着,吸吮得有够用力,有种强烈的企图,彷佛要把我吃进去。同时他还磨动身躯,借由剧烈心跳陈述迫切的心声;用大鸡巴交缠我的硬屌直接挑逗,传达一种野兽派的呵护,非常舒慰。我真的醉了,醉在温醇的柔情里享受被爱的虚荣,助燃欲火窜烧加深饥渴的依赖。
我急促喘了起来,必须告白:「叔!我很想念你,后来又去戏院,希望能遇到你,就想给你干。但那里的气氛让我很不自在,看见那些失落的眼光,我就很害怕。担心有天会沦为其中一员,干脆就不去了。」
「不去才好。你很聪明,才没变得像我一样,过着孤魂野鬼的生活。」
「有需求很正常,就怕力不从心,岂不更糟?」
「我以前太放荡,都不会想,也不知道自己要什幺,耐不住寂寞就去找人消火。可悲的是,在同志圈打混多年,我却从未得到过温暖。别人根本不甩我要什幺,压根不在意我在想什幺。人家要的只是我的大懒叫,希望我能勇猛无比的肏干,带给他畅快的慰藉。而我,给得起的,也只有冲锋陷阵的干劲。说穿了,我只是个无血无目屎ㄟ打炮机器。有时候,我讨厌自己的沉沦,我更讨厌自己的落魄,自己的无能……」旖旎的床事,不知怎幺搞的,变成倾诉心事。
他在老大徒伤悲,让我警惕,心疼安慰道:「打炮也讲究技术。叔!你本就拥有专长,现在还会园艺,比许多人都强。」
「说了不怕你笑,年纪愈大,有时我甚至不晓得,活着是为了什幺。直到来到这里,一切都变了。你们对我那幺好,让我觉得好像在家里。终于醒悟,我的心累了,不想漂泊、不想再流浪。我只想有个家,有个人互相依靠,愿意给我疼爱。小宝贝,我现在很开心,不想再把我的宝贝吓跑。我只想让你舒服,永远可以疼爱你。看见「那个落卡仔」不懂珍惜,那幺用力把你干痛,我真想冲过去把他杀了!但是……」
我完全懂了,猪哥阿叔三磨四拖,不急着开干,不是故弄姿态。一来,他打定主意,要把困扰在心里的疑惑彻底弄清楚。二来,他非常在意,担心弄痛我。往深处想,身处激情要去克制强大的欲望,放缓节奏纯属不易,份外真心。
我说:「通哥是我初吻的对象,意义非凡。叔是第一个干我的人,更是非同等闲。」
扬晨风道:「我现在不吃醋了,龟头要热吻郁金香,我光想就开心。宝贝,我的小宝贝!我冻袂条啊,大鸡巴要干你了!」他亲了我一下,笑咪咪挺起身把我的右脚拉去抵住他左胸,右手抓着我左脚踝擡高迫使臀股分开露出菊花来。
他再握着粗硬大鸡巴,用红通通的大龟头,流着口水的马嘴很不卫生吻着我的大肠头,又说道:「花瓣香喷喷,一亲到,大鸡巴就爽到流出潲水,实在有够兴奋。宝贝!你免紧张,全身放轻松就行。我会很小心插进去,龟头虽然很大个,但马嘴保证不会咬疼你。而且一定干到让你爽歪歪,觉得很幸福。噢~光想我就好兴奋,大鸡巴噗噗跳,你有感觉到吗?」
说到相干,他脸上焕发自信的光采,神情色瞇瞇。
不是员外硬要玷污丫环的猥琐,而是坏坏的轻佻。
这是个人的特质使然,缺少那份迷人的坏意,很容易变碍眼,令人不舒服。
扬晨风骨子里就有那股坏痞性,纵使长相和英俊沾不上边。但他举手投足,其实充满个人的独特魅力。刚好合我胃口,很喜欢吃的那种菜。自然很喜欢他把肉麻当有趣,与他调情玩游戏,特别容易兴奋。我好期待他把粗硬大鸡巴爱爱插进来,赶紧催促卡实在:「大鸡巴叔叔~你懒叫大支,俗搁有力,勇啦!我肖想甲流鼻水咧!而且,你相干的技术,造福广大群众,绝对够格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我半点都不紧张,只是屁眼快被蚂蚁搬走了。」
「痒喔?我惜惜、我呒咁。」扬晨风握着大鸡巴一使劲,龟头罩住我的屁眼,压紧紧地旋圈。他一脸心疼,一付要送礼物的样子,又说道:「来啊、来啊!宝贝对不起,不是不干你,我真的很愿意,大鸡巴要插进去了,宝贝想不想啊?」





![《[BG]折梅》1970最新章节列表 溶暗火柴力作](/d/file/po18/725147.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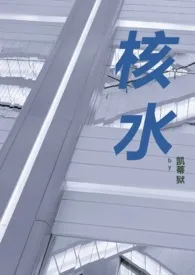
![《月到波心[破镜重圆 姐狗 1v1]》大结局曝光 酸杏著 1970完结](/d/file/po18/83721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