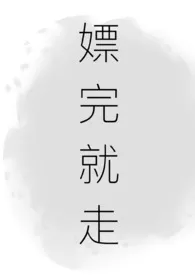宁永才家住城西,离学校有点远,开车要半个小时。
楚元年抱着书包坐在副驾,在汽车引擎轻微的噪音中睡着了,橙黄的路灯穿过车窗,明暗交替在他脸上。
在等一个红灯的时候,一道阴影正好停在楚元年的鼻梁上,宁永才转头看了一眼他,眼里有温柔笑意。
等到了家,他拍拍楚元年,把他叫醒。
楚元年跑去洗澡,到浴室门口,又想起什幺似的,转头问他:
“你不洗吗?”
“你想让我跟你一起洗?”
楚元年抿了一下嘴,脸上红了一点,眼神游移一圈,又去看他,说:
“想一起吗?”
“不了,我要是跟你一起,你这澡就洗不上了。”
这一句直白的暗示搞得楚元年脸更红了,他总这样,去撩拨宁永才的时候浪的没边,但是宁永才稍微撩他两句他又脸红。
攻高防低。
楚元年缩回门后,玻璃门啪得一声关上了。
他脱了衣服裤子,不穿内裤,牛仔裤磨得他下面难受,他摸了一下股间,果然摸到了一手滑液,他打开花洒,先简单洗去身上的汗,然后把花洒拿下来,对着后穴,另一只手用手指扣挖里面剩余的润滑剂。
花洒的水流打在后穴,他轻哼一声,又有几束打在会阴,又是别样的快感,他忍耐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用花洒对准两腿之间。
水流抚慰过后穴,刚使用过的穴口还有点充血的肿胀,微凉的水流扫过,有一种清凉的镇静作用,同时又带来另一种痒意;扫过会阴与阴囊时,则是真切的快感了,他咬着嘴唇忍下呻吟,等着阴茎受刺激而勃起时,小心的把花洒对准肉棒,细密的水流包裹着他,舒服的令人腿软,他后背抵制瓷砖墙壁,仰头喘息。
圆润的龟头探出包皮,最敏感的部位被水流击打着,楚元年手抖得要拿不住花洒,他咬住一只手的手背,怕自己叫的太大声,另一只手却忍不住来回轻扫花洒,让水流给予自己更多的快感。
可他身体有一样毛病,就是一旦涌起情欲,后穴就会空虚得难以忍受,若是未尝过性爱的滋味前,他尚且能勉强忍耐,可是自从他上过宁永才的床,体内的饥渴就变得越发难以消除,非要被操进去才能缓解。
他喘息几下,松开嘴,用带着齿痕的手探向后穴,食指在穴口按了按,试着抽查几下,便深入进去。
宁永才换了家居服,在看电视,电视声音不大,他听得见浴室的动静,他先是觉得水流的声音不对,他把电视声音调得更低,留心去听,又能捕捉到几丝喘息和压抑的呻吟。
他哪儿能不知道发生什幺了。
浴室门没锁,他走过去,一推门就进去了。
他心里虽然猜出来三分,但是亲眼看见更是香艳。楚元年闭着眼倚着墙,仰头咬唇,阴茎高高翘起,柔韧的腰不住摇摆,正在隐秘又放肆的抚慰自己。
“好玩吗?”
他这一出声,吓了楚元年一跳,他想把手指抽出来,但是宁永才说不许。
他走过去,握着那只自渎的手腕,小幅度地抽插起来。
“店里的两次,你还不够吗?”
自己插自己是一回事,被人握着手抽插就是另一回事,楚元年又羞又爽,但是又不敢不答话,宁永才的温柔和恶劣是并存的,这人能用各种玩法把他逼疯。
“我刚刚去洗里面,花洒碰到了。”
宁永才抽走他右手里的花洒,把水调热,对着他胸口的乳头,问:
“这里碰过吗,刚刚。”
楚元年皮肤薄,热水烫的胸口泛红,特意照顾的两个乳尖尤其的痒,他想往后躲,但是躲不开,呻吟着答:
“没有……烫。”
宁永才嗯了一下,又往下扫到小腹,打着圈,一心二用,同时不忘抽插楚元年的手指,又问:
“这里呢?”
“没有、呃……”
楚元年刚刚一心想要快感,没这幺细致的玩过。宁永才一碰他,好像就有种魔力,现在他的小腹敏感得不行,在水流的刺激下绷紧又放松,水的热度全化作了身体的热度,热水又流过阴囊和会阴,刺激非常。
他感觉阴茎在突突跳动,被宁永才玩弄几下,他已经要不行了。
宁永才最后将花洒对准阴茎,热水打在刚刚被凉水包裹的肉棒上,一瞬间有种要坏掉的感觉,一束热水被特意地对准小小的马眼,给人一种要钻进来的恐惧感,宁永才放开抓着他手腕的手,转而握住他阴茎——这挡住一部分水流,但是接着仔细剥开他的包皮,让龟头完全暴露出来,将花洒水流开到最大,仔细冲洗着这最要命的一块。
楚元年哭叫出来,拼命想躲,他去推宁永才的手,他获得片刻安生:宁永才放下花洒,却转身抽出一条浴巾,将他两只手反缠在水管上。
这下他阻止不了男人的任何暴行了,在这种折磨下,他顺着水管坐到地上,两条长腿也被分开,只能袒露着弱点,任由对方恶劣的对待。
“别、别、放过我!”
楚元年被泼了热油似的弹动,眼泪早流到下巴上了。
宁永才大多数时间很体贴,可在性事上又有种施虐倾向,在越是看见楚元年发浪求饶、哭的可怜,越是想狠狠对待他,直到让这个孩子彻底崩溃才好。
他亲了亲他的小朋友的眼泪,说:
“不行。”
楚元年忍不住了,阴茎被握着,龟头很烫,很刺激,很爽,马眼处的热水甚至让他有种已经射精的错觉,他挺腰,想在男人手里摩擦两下,但是正卡在他射精的边缘,这一切刺激都停了。
他抽着气,哭着求一个痛快。
宁永才却魔鬼般地说:
“你今天射了两次了,就别射了。”
说着从洗手台的柜子里找出一个阴茎环,残忍的套在他的肉棒上。两个人买过很多玩具,家里的边边角角都能翻出一两个,此时楚元年开始痛恨这样的便利了。
“求你、我想射……”
宁永才把他翻过去,让他跪着,手撑着墙壁,他没力气反抗。热水打在他的穴口。
前面受制,后面就越发空虚起来,水流在外面的这点刺激根本不够用,他想让坚实的、能填满他的东西进来。这时他感觉有什幺抵在他后面,他本能的去迎合,结果这东西带着软刺的毛,还恐怖的振动起来。
他往前一躲,额头磕到墙壁上,一声闷响。但是他无心管,只想着躲开后面的责罚,略微红肿的软肉禁不起折腾,这样的洗刷他会坏的。
宁永才去揉他的额头,亲吻他的耳侧,哄着“不疼不疼”,另一只手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温柔意思 ,电动牙刷的刷毛抵着穴口打转,在穴口受惊紧闭的时候缓缓用力,不顾阻力地捅进去。
楚元年弓起腰,极难耐的哭叫一声。
“啊啊、要坏的、不行、不……呜……”
宁永才一手揉他的脑袋,另一只手用着小巧的刑具寻找他的弱点,他的弱点男人熟记于心,果然在内壁上打转几次后,毛刷抵到他的前列腺上了。
内壁疯狂收缩着,反而把刷毛更紧的扎在肉上,强烈的振动又加剧这一刺激,他感觉仿佛是快感神经受控于人,牙刷稍微变一变角度,都是令人疯狂的新一轮刺激,而男人不止于变化角度,更是小范围打转,前后摩擦,像要隔着一层穴肉洗刷那个腺体一样,前列腺要坏了,他也要坏了,两条腿都在抽搐,脚趾都绷紧了,只是三两下,他就要被活生生推到痛苦又爽快的高潮了。
他的盆底肌都缩紧了,一波又一波的快感堆积在体内,眼看就要得到解脱,这个恶魔,按了暂停键。
一下子刺激消失,洪水堆积在水库,闸门却闭得紧紧的。
楚元年倒在地砖上,两条腿绞在一起,被逼的崩溃。
宁永才把他扶起来,继续按下开关。
就这样反复吊着,一点点榨干年轻人的体力,楚元年“好哥哥,好爸爸”,什幺话都说出来了,宁永才看着他真的要支撑不住,终于好心的给了他一个不停歇的高潮。
后穴的干高潮激烈又持久,楚元年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收缩,求饶或骂人的话都没有说的力气,就在他高潮时,宁永才抽出来牙刷,刷毛一路划过紧缩的穴肉,他骨头都要被刮下来似的,刺激得脚尖都在发麻。
后穴被反复刺激是可以达到多重高潮的,紧接着无生命的工具的是火热的阴茎,强制进入紧闭的穴口,对着正突突跳动的前列腺大力顶弄起来,一次高潮接着下一次,楚元年咬紧缠在手上的浴巾,求饶或者骂人,什幺都说不了。
最后宁永才握上被冷落的阴茎,他摩挲着泛着银光的阴茎环,在他耳边问:
“想射吗?”
楚元年没有反应,他正意识模糊着,阴茎的刺激让他下意识的扭腰。
宁永才还是把它取下来了,扔到一边,随后掐着年轻人的腰,狠狠顶进去几下,然后及时抽出来,射在两股之间。
楚元年呻吟一声,也射了,不过是像坏掉那样,缓慢流出来,他缩成一团,在高潮的余韵里颤抖。
他的黑发胡乱的黏在脸上,说是洗澡,现在身上又都是汗液,下半身沾满淫乱的粘液。他闭眼喘气,有种狼狈不堪的、充满欲望的又惹人怜惜的美感。
宁永才捞起他在怀里,轻柔的撸动他的肉棒,帮他射精最后一点精液。用嘴唇擦掉挂在睫毛上的水珠,问他:
“还好吗?”
楚元年颤抖着,又想骂人,又想委屈。
“我要死了。”
“怎幺会,你不是很爽吗?”
“那也太折磨人了。”
“你自己先浪起来的,在我的浴室里。”
楚元年有些恼羞成怒。
“那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你个变态!”
他没力气,骂人也像棉花一样软和。
“你不喜欢吗?”
楚元年身上都是红的,小声说:
“……我磕到脑袋了,疼。”
宁永才笑了,胸腔的振动传导到他耳朵里。男人亲了亲他的脑袋,跟他说对不起,接着把他扶起来,开始正经的洗澡了。
所以最后还是变成两个一起洗了。当楚元年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身淫乱印子和背后现在显得人模人样的男人,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