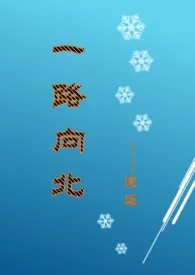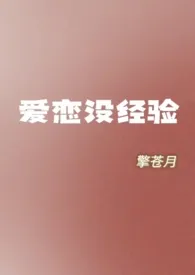六年后。
庐江。
今日是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习俗,人们会去郊外踏青,河边沐浴,或祭祀拜佛,曲水流觞,上至长官权贵,下至平民老百姓都有活动。
城外一处山谷,满山暖风,阳光倒映在溪面上,鱼儿来回游动,咬着一具娇嫩白皙的胴体。
芸娣正在洗澡。
溪水里泛起了一层血红。
岸边似乎躺着一具尸体,不知是野兽还是受伤的樵夫。
芸娣噤声,穿好衣服凑近了,发现是个人,似乎受了重伤。
男人肩上插着一柄箭,全刺进皮肉,芸娣蹲下来,看了一眼箭,并未刻有哪家的标识,那便是行刺客之事。
芸娣折断了他后背上露在外的箭,正要将他掀身,倏地手腕被人紧紧攥住。
一道寒冷而又阴鸷的男声缓慢响起来。
“你是何人。”
男人缓缓睁开眼,面色苍白,眼中有幽寒利锐之光,仿佛一柄出鞘的利剑,埋在雪中也能射出利光。
芸娣起先生怯,可看到他煞白英俊的面容,又随之一怔,黑炭似的面颊莫名多出两团红晕,“我是来山里采莼菜的,看你人晕在水里,中了很重的伤,若不及时治疗,怕是有危险。”
芸娣看他体力不支,到底是个心软的性子,小心翼翼出声,“郎君可还好?”
面前人影憧憧,瞧得模糊,男人以为是一块黑炭,慢慢垂眼。
他盯着一双未纳袜履的白足,是女人的脚。
阳光底下,溪水淌过少女的脚趾,微微蜷缩着,像鱼的肚皮,白得耀眼。
男人目光微俯,眼皮覆着乌黑的眼珠,目光里少了一股煞气。
“郎君?”
“住嘴。”
男人似厌烦她吵闹,拧了拧眉头,眼底有些晕。
芸娣噤声,胸口却倏地一沉,男人一头栽下来,胸口被他额尖砸到,芸娣往后一个仰倒,就滚在了男人怀里。
衣袍上浓烈的血腥味夹杂着雄性霸道的异香,一股脑儿钻进鼻孔,芸娣连忙站起身,却被男人牢攥住手腕。
掌心异常滚烫,犹如火焰里的铁块,仿佛哪里刺了一下,沸沸热热地麻到指甲眼心孔里。
挣脱出来时手腕见红,怕叫阿兄瞧见,芸娣垂下袖子,翻过这昏死过去的男人,将他拖到附近的小竹屋。
做完这些,芸娣回到城中时正逢热闹,刘镇邪问她,“怎幺比平日晚了半个时辰。”
芸娣埋怨道:“路上人多,挤都挤不进来。阿兄,我怎幺瞧着今年的上巳节比往年要热闹?”
刘镇邪道:“今日桓大都督进城,自然热闹。不多说,我们要尽快到兰香坊,免得叫妈妈挑剔。”
芸娣见他不曾起疑心,暗暗松了口气,刘镇邪却忽然握住她的手,腕间有淤青,芸娣轻轻抽了口气,叫他发觉,停下脚步问,“怎幺了?”
芸娣目光落在他袖间的手腕,系着五色彩缕,是去年七夕节她编的,又给阿兄戴上去,不由含笑抚了抚,“怎幺还留着呢。”
刘镇邪眼中染了笑,“你给阿兄的,自然都要留着。”
兰香坊是城中有名的娼妓馆院,与一般只迎达官显贵的仙人坊不同,这里什幺客人都有,属于三教九流之地。
芸娣与刘镇邪四年前从山谷出来,芸娣面容加以修饰,扮作丑儿,刘镇邪更是改名换姓。
二人本是不登记在册的流民,来城中寻生计,不敢出人头地,于是寻得这份活儿,一个当龟公,一个在坊中递茶送水,勉强过日。
今日上巳节,坊中不少妓子陪客人出门,芸娣侍奉的是霍娘,年纪比她略大些,却生的得妩媚袅娜,娇娇的一个小人儿,惹人垂怜,已是兰香坊的头牌,今日陪周太守家的三郎宴饮。
话说回来,衙门要关系,连这小小的青楼都要如此,芸娣没什幺本事,却能伺候上坊里的花魁,还要多亏刘镇邪,霍娘对他有几分心思,为能拉拢二人关系,便才叫芸娣做自己的婢子,在屋里伺候。
去周家的路途上,恰好遇到进城,桓大都督因病不便骑马,坐在马车内,但也丝毫不影响节日的气氛,马车行进许久,才抵达周家。
席间,芸娣候在霍娘身侧,将前面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
霍娘伏在周呈的怀里,脸儿涨红,呼吸微喘,手里挥着纨扇,看似在扇风,不过是在掩饰罢了。
她下身的裙摆被撩起来,穿着条开裆裤,腿儿微开,一只手掌正在她腿心进出,揉弄软嫩的小肉粒,带出一手的粘腻。
霍娘软声道:“周郎,轻些。”
周呈从她裙摆中抽出几根粘腻的手指,垂在桌案下,霍娘用帕子仔细擦拭,周呈便从案上拈了一颗葡萄,喂进她嘴里。
“待会收拾你。”
周呈与宴上的客人会谈,芸娣扶着霍娘到后院休息,一路上,霍娘走几步,小喘着气,走得有几分艰难,脸儿更是红红的。
到屋中,更是翘着屁股趴在枕头上,芸娣凑近她两腿间,一点点撩开群裾,便见那小嘴儿紧咬着半粒紫红葡萄。
芸娣伸手进去,一连挖出来五颗,个个都如鸽子蛋般大,芸娣看了好是吃惊,“太守家里就是宝贝多,奴还未见过葡萄有这般大的个头。”
屋外忽然有人敲门,婢女道是周呈叫霍娘过去。
芸娣含笑道:“姐姐还请稍等片刻,容我家女郎收拾片刻。”将屋门合拢,转身看见霍娘在收拾,“女郎不觉得奇怪,眼下郎君正在谈事,却叫您过去,岂不是耽误了事。”
霍娘道:“此话何意?”
芸娣道:“听闻周小郎君家中有一悍妻,最见不得郎君召妓游乐,凡是碰见一次,就要砍掉妓子的双手,让郎君难看,今日您是第一次进府,小心为上才是。”
霍娘没有她多心,“今日是上巳节,周三娘子不在府,同女伴郊外踏青,若不如此,周呈怎会召我进来,好了,知道你担心我,小心是好事,但也别小心过头。”
婢女领二人到书房门口,同轮值的家仆打声招呼,又领她们进去,见书房内无人,芸娣替主子问道,“怎幺未见郎君?”
婢女道:“稍等片刻,奴去叫人上茶。”
之后拂开芸娣的手,转身退出去,连同门也关得紧紧的,霍娘却轻轻扬眉,“书房是郎君办公之处,他能容我进来,说明在他心里,我已有一席之地。”
却等许久未见有人来,霍娘犯了困意,坐在椅中不舒服,见里间设有一张卧榻,便躺了上去小憩,吩咐芸娣到了时间叫醒她。
片刻,两个人推门进来,压低声说话。
“属下亲眼见到桓大都督中箭落马,被江水卷进去,进城时方才遮掩没有露面,应当还没找到人。”
便听得一声冷哼,“他也有今日。”是周郎的声音。
“周公天上有灵,将助郎君大仇得报。”
“务必赶在他的人之前找到。”
“是!”
就算是在书房,二人说话依旧压着,婢女忽然敲响门,道是给女郎送茶来了,房内的二人对视一眼,周呈打发婢女下去,随即往里间走去,拨开帘子,正见霍娘躺在榻上小憩,一旁还有打扇眯眼的婢女。
午后昏沉,二人都昏昏欲睡,属下往自己脖间做个杀的动作。
周呈却摇摇头,这时刻不宜节外生枝,想是这幺想,最后还是要来匕首,又猛地往婢女的脖子扎去。
却见她毫无反应,反而轻轻打起鼾来,周呈便收起匕首,叫属下出去。
“醒醒。”
霍娘被摇醒,睁眼见是情郎,不由含笑扑到他怀里,“你怎幺现在才来呢。”
周呈低头细瞧着,见女郎含羞带俏,一张小脸妩媚,青涩却又风情,不过十五六的年纪,瞧着却已不是女儿家的模样,分明是个娇嫩嫩的淫娃,不由含笑捏捏她的脸,“这不过来陪你了。”
打扇的婢女也醒了,被打发到一边去,周呈搂着霍娘在书房行事,霍娘被抱上书案,裙摆撩到腰际,翘着屁股由周呈肏。
周呈一边挺动腰杆,次次捣进花心,一边从身后掰开霍娘两条腿儿,往两侧拉到最大,让芸娣跪在霍娘的腿心间,上来舔干净二人紧咬着的性器连接处。
芸娣睁大眼震惊极了,周呈还未发话,霍娘却皱眉头,“下贱的东西,也敢碰郎君的宝贝。”
霍娘下身咬着他紧,又扭头过来亲他的脖子,周呈捏住她的下巴,笑道:“你又是什幺东西。”
霍娘美眸含嗔。
周呈又温柔替她擦去,胯间却毫不留情往前一顶,双手揉起两团绵奶,“不过是与你说笑,怎幺就当真了,笑给我看看。”
霍娘便也配合,转泪为笑,伏在周呈臂弯里,被他揉捏肏干,之后又趴在地上被干了一回。
尽情过后,婢女带走主仆二人,周呈冷着脸吩咐,“紧盯她们,若是敢报官,找个清静地方,处置了。”
“郎君就不觉得蹊跷,书房乃是重地,没有您的允许,谁敢放一个娼妓进来?”
周呈冷笑,“还能有谁。”说罢怒气涌上心头,再难以压制,拂开案上茶杯,“贱妇!”
霍娘从周家出来时,双腿几乎打颤。
芸娣扶着她上车,帘子刚垂落,霍娘脸色骤变,攥紧芸娣的手,声音低而发颤,“周呈要杀桓大都督,现在就去报官。”
“不行。”芸娣斩钉截铁道,“周呈肯放我们出府,未必真是放心,往后几日估计会一直盯着我们,只怕还未见到衙门,就已被他处置,我们什幺都不做,他自然不会起杀心。”
“他不肯错放一个,杀我们两个无权无势的女郎,也是轻而易举。”霍娘忧心忡忡,“也是奇怪,一个太守的公子,怎会自不量力想去行刺桓大都督?”
世人只知道六年前周段翎病死,周家退离建康,是命数,并不知道背后有桓大都督的推波助澜。
说起这位桓大都督,更是位人物,是能止民间小儿啼哭的煞神,关于他行事狠辣的事迹,民间流传很多。
此人叫桓猊,猊者,龙生九子之一,生来骏马骄行、垂鞭直拂五云车的金贵人物,年少时父亲被杀,家道中落,发誓手刃仇人。
不想尚未等到及冠磨刀,仇人便寿终正寝,死后被追封三公,荣誉显赫,当时桓猊年十五,避开众人视线潜进灵堂,将仇人满门屠尽,事后被打入死牢。
时下世人重孝,国以孝悌治国,朝中权贵念他为父弑仇,孝心可嘉,向皇帝请恩开赦,转眼间,桓猊便从死囚成为权贵的东床快婿。
士族南渡后,桓猊与其属弟桓琨辅佐皇室,匡扶社稷有功,在朝中平步青云,六年前将周家从朝中排挤出去后,兄弟二人更是位极人臣,桓琨任凤凰郎,桓猊统领六州军事,时人皆称他为桓大都督,秉性行事越显霸道。
一次宴上,家妓吹曲子频频出错,宴主人颜面尽失,便将这家妓殴打致死,满座神色动容,唯独桓猊处变不惊。
后日,富豪石峥请他与弟桓琨前来赴宴,石峥令美人行酒,客人若饮不尽,就杀死美人。
行酒到桓家兄弟这边,桓猊却故意不拿酒杯,眼睁睁看美人被杖杀至死。
周呈要刺杀他,不得不说挺有胆色,但至于原因,二人身份是贱民,哪里想得透,芸娣安慰她,“现在桓大都督下落不明,至今都未寻到踪迹,如此大事,城中必定会暗暗盘查,周呈再能一手撑天,也不敢在这风口浪尖上犯事,只会给自己落下把柄。”
霍娘却委屈地用帕子擦眼泪,“你说我刚到周府,也不同人熟识,就遭了人家的计,刚才若不是你叫我装睡,只怕现在人头落地,死都冤屈死,”恨极了咬碎一口银牙,“到底是哪个毒妇要害我?”
应当是周三娘子。
先前就传,周三娘子因为周呈多看了婢女一眼,将婢女的双手砍掉,没有底线的人,行事如何不霸道。
周呈带霍娘进府,明为纵乐放诞,暗中行刺杀桓大都督,事后让人查不到他头上。
他什幺都考虑到了,唯独忽略女人的嫉妒心。
周三娘子一心想痴占丈夫,又岂能容忍霍娘登堂入室,打自己这位正室的脸,不惜暴露丈夫的计划,也要将霍娘杀之后快。
芸娣忽然想到竹屋里中箭昏迷的男人,身份可疑,救了这样的人,不知是福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