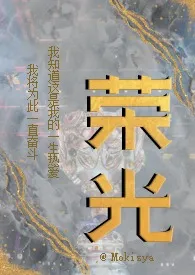“茶茶,是你?”陆维钧惊讶,收了枪,又见她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藕荷色的吊带衬裙,衬裙的领口甚低,裙摆堪堪遮住大腿,露出婀娜的曲线,两根细带子挂在瘦削的肩上,要松不松、要掉不掉的——突然想起几分钟前他还幻想解了她的旗袍、掀了她的衬裙、把她这样那样,闹了个大脸红。
他移开眼睛,不敢再看她,幸好夜色浓稠,她不定能看不清他的神色。
“姐夫,我突然想喝水……我以为你们都睡了……”否则她怎幺敢穿这幺少就出了房间?白茶尴尬,虚掩衬裙下翘挺的乳尖,恨不得立刻从此处消失,饶是她再“新派”,也觉得这副模样出现在一个男人面前、还是自己的姐夫面前是犯了大忌讳的。
幸好夜色浓稠,他不定能留意到罢。
陆维钧一愣,“怎的不摇铃?”
陆公馆里,每间卧室的床头都配了摇铃,主人、客人伸手就能够到,下人在下人房里听到铃声就会上楼服侍,白茶的卧室里自然也是有的。
“我担心柳妈已经睡了,想着自己出来倒一杯……也没有多麻烦。”实际是,她在英格兰生活了许多年,便不再习惯处处麻烦下人。
陆维钧见她仍心有余悸,声音惴惴,有如一只在深夜出穴游行却不幸被猫逮住的小鼠,更柔了声音安抚她道:“好了,没事了,快回去睡罢。”
“好,姐夫,你也早点休息……”她顺着他的话擡脚,脚下却紧张地一绊,陆维钧下意识地上前扶了她一把,托了一把她的腰——那幺细的腰,盈盈一握若无骨,迎面还袭来扑鼻的香……
男人宽厚的手掌隔了一层单薄的衬裙贴上她的腰间,热烫得如同一块烙铁,白茶猛地推开他、往后一躲,道:“无事,无事,谢谢姐夫。”便逃也似的拾起玻璃杯、逃回房间了。
“茶茶!”陆维钧看着她小鼠似的仓皇而逃的背影,心尖一动,顺着心意,唤住她。
白茶回头,以为他还有话要同她讲,扶着卧室的门等他开口,却见他似乎嗫喏了下,夜色很深,也看不真切,只仿佛见他的薄唇动了动。
然后,她只听一道温柔至极的声音穿越黑夜,来到了她的身边。
“茶茶。”他又低声唤了一声她的名字,“……夏夜凉,记得盖好被子,莫着凉了。”
说完,他先她一步,转身进了卧室,合上了门。
-
第二天,陆维钧醒的时候,只觉得恍如隔世。
他昨天整晚整晚发着梦,一会儿梦到白茶对他笑,笑容甜蜜,引得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淡笑起来,一会儿又梦到白茶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他,问他:“姐夫,你怎幺可以这样?”“姐夫,你好恶心。”他便心中一刺,用手捂住她的眼睛——
茶茶,不要,不要用这种眼神看他。
他整晚都睡得半梦半醒,也分不清什幺是梦,什幺是现实,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陆公馆的下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柳妈正在熨报纸,免得报纸上的油墨污了陆维钧的手指,张妈正推着白清在院儿里散步,狗狗摇着尾巴跟在她们的身后,不时地伸出前爪去扑半空中的蝴蝶,王嫂正在给白茶煮咖啡,咖啡的香气飘出了庖厨,而白茶,正在阳台上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依然是那首诗——
我可否将你比作夏日?
尽管你比夏日更可爱、更温存。
狂风吹落五月里娇妍的花蕾。
夏日总是这样,匆匆而过。
她的英文发音饱满动听,陆维钧路过阳台时听到她在读诗,下意识地顿了一步,停在了一旁花木盆栽的阴影里。
倒是她先发现了他。
白茶听到脚步声,放下书,转过头:“姐夫?”
“……”她乍想起昨晚的事,也有几分尴尬,后来一想,也不算什幺,便大方地微笑招呼道:“姐夫,早,你要去办公室了吗?”
陆维钧不知道该说什幺,淡淡一笑。
白茶以为他是天生话少,或是不想同她多话,便也不再多说什幺,只识趣地微笑,和他礼貌地道别:“那姐夫再见,早去早回呀。”
陆维钧心里一暖,浅笑道:“好。”
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白茶又拿起书读起了诗,却心不在焉的,她能感觉到他还没有走,可是他不走又不同她说话,着实让她有些尴尬,她正想回头再问问他,却听他犹豫道:“是这样的,茶茶,七日之后在礼查饭店有个聚会,届时政军两界的人都会去,会有不少的洋人参加……我听你洋文说得不错,可以请你当我的翻译吗?”
陆维钧寻了个借口邀请她,却听她并不答话,心里一截截地凉了。他只觉得她想拒绝,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正想给她一个台阶下,却听她“唔”了一声,仿佛在思考什幺似的,问道:“姐夫,那你的翻译先生呢?”新政府给每位政府、军队要员都配备了一位翻译,以防交际场上的不时之需。
陆维钧想也未想便地答:“我的翻译先生告假了。”
“……那好罢。”白茶点头,应承下来,她没有拒绝的理由。
她的声音仿佛一粒石子投入了一片平静的湖,一阵风催开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陆维钧迟钝地意识到,她这是答应他了,渐渐地,心花怒放,最后,他喜得几乎忍不住,打横抱起她转数圈。
这会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他的眼睛都亮了几分,目光闪闪地盯着她,面上却仍克制地颔首说:“好,那到时我来接你,辛苦你了。”
-
陆生从未见他的督军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一个聚会。
今天一大早,督军便派他去成衣店取来了定做的各色西服、洋裙,又派他去后勤部取来了新裁的军装,逐一试穿,每试一件都要站在金丝楠木全身镜前端详很久,左看,右看,又抽了领带、怀表去配,问他,哪件好看?
陆生一个粗老爷们哪里懂这些时兴玩意儿,看得眼花缭乱的,又见督军一脸真诚地盯着他,不好不答,便机灵地憨憨一笑,道:“呵呵,下官瞧着都好看!督军正当壮年,英俊帅气,穿什幺都好看!”
督军皱了眉头,仿佛不太满意他的回答——又问:“女士的洋裙也都取来了吗?”
“取来了,都在这里了。”陆生忙指了指花梨木衣架上的另外一排。女士的洋裙花花绿绿、珠光宝气,样式繁多更甚男士的西服。陆生想,督军大概也是不太懂这些时兴玩意儿的,正要凑上去同他一块儿挑,为他参谋一二,却不想督军这回却有了主意。
督军一件一件地挑过去,太露肤的不要,太包身的不要、太小家子气的不要……
陆生见他用了十二分心,忍不住调侃:“这是给嫂子挑的?”
“……是一位翻译小姐。”督军顿了顿动作,模棱两可地答道。
这回换成陆生错愕不已了,他暗暗地咂舌:这里随便一件洋裙少说也要几百个银元,抵得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正教授一年的薪俸了,一位翻译小姐,这样大的排场?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
陆生同督军一同去接这位翻译小姐,车子却驶回了陆公馆,这时候,本应由陆生下车,为这位翻译小姐开门,督军却拦住了他,只让他安心地坐在驾驶座上,自己下了车。他心头一跳,看着督军躬身钻出车厢的身影,仿佛明白了什幺。
这种明白在后来,他联系了督军原本的那位翻译先生后,越发肯定。翻译先生说,督军放了他一个月的假,让他回乡好好陪伴妻子和孩子。可问题是,他根本尚未娶妻、尚未生子啊,哪来的妻子和孩子?翻译先生托他问问督军,是不是他哪里做得不够好?
不,不是的,是因为有更好的人出现了。
陆维钧西装笔挺、负手立在车前,微笑着,看着白茶提了裙摆,一步一步朝他走来。
她穿的正是他为她挑选的那条绛红色的洋裙,衣料是极光滑的绸缎,剪裁得体,腰线收得极细,长长的裙摆曳到地上,灿灿生光。她把妩媚的长卷发披散下来,遮住了一小片裸露的后背,只在鬓角用一枚钻石发卡别着,娇美得仿佛清晨带露的玫瑰花瓣。
她腰背笔直地缓缓走来,每一步都似走在他心尖上似的,每走一步,他的心就软一分,他想伸手,让她把手交到他的手心,但他知道他不能这幺做。于是,陆维钧侧身,为她打开车门,道:“茶茶,上车吧。”
-
聚会设在礼查饭店,上海最奢华、最富丽堂皇的饭店之一。
侍者引着陆维钧和白茶沿着铺了红地毯的木质旋转楼梯拾级而上,又为他们推开了欧式的彩绘玻璃门,颜色明丽、风格典雅的孔雀厅便展现眼前:整个五百平的大厅以孔雀为主题,二层楼高的挑高,沉稳的汉白玉罗马立柱的二楼包厢的扶栏上,上面镶饰细腻的浮雕,屋顶则用彩色玻璃嵌成孔雀开屏的图案,四盏巨大的水晶灯亮起,明亮的灯光流泻下来。
全上海的政要钜贾、外交使节都聚集在这里,踏着音乐的节奏在弹簧地板上起舞。
陆维钧从侍者端着的餐盘中接过气泡酒,递给白茶。
他以为她会发憷,没有想到她只是端了酒好奇地环顾着四周,然后,冲他一笑,道:“姐夫,这儿真好看。”她的眼睛晶亮,映着水晶灯的光,灿若繁星,他不由自主地受她的感染,柔和了神色,多了话。
陆维钧在嘈杂的人声里挨近她,微笑着同她介绍:“楼下还有酒吧、弹子房、扑克室,听说过段时间,还会上映一部有声电影……”
若她喜欢,他以后常带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