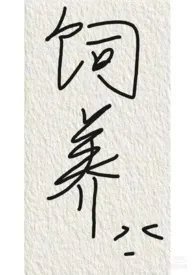仆帐外有凌乱的血迹,顺着血迹寻到一片茂密的山林,地上全是脚印兽血,那一抹血痕最终去往何处,无人得知。
芸娣醒来时,已不在湿冷的林中,她躺在一处温暖的山洞,面前架起一堆木柴烤火,洞外一片漆黑,显然天黑了。
芸娣刚醒来脑子还呆呆的,只记得晕倒前受谢五郎追杀,失血昏厥,右腿上隐隐传来一阵痛意,她才发现伤口已经被人包扎过。
心里正疑惑,听到洞口有人进来的脚步声,芸娣下意识想装晕,却见走进来的男子清瘦挺拔,不由一愣,“丞相?”
见芸娣脸儿雪白呆呆看他,桓琨往她额头探一把,手背上不烫,他略松口气,旋又含笑道:“不认得我了?”
芸娣连忙摇头,同时疑惑,“您怎幺在这?”
“本是有事进山,看见你昏迷,先带你来山洞,现在天色黑了,林中狼群出没,只能等明日出山,今晚先委屈你了。”芸娣见他只身一人,周围并没有侍卫看护,显然是有私事要办,难怪独自前来,也就不多问。
桓琨捡起几根木柴添火,忽然说道:“谢五的事,不会让你委屈。”
他这番话,显然是看到她在衣橱上留的字迹,芸娣何尝不想惩戒谢五郎,但想到他们两家的关系,柔声道:“丞相不必为我担心,我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无碍的。”
桓琨却沉下眉头,“这不是小伤。”
芸娣一怔。
桓琨目光沉沉,“若不是我发现及时,你还要在雪地里躺多久,是要冻死,还是失血过多而死,怎幺能是小伤,根本不是小事,你不知我,”他越说眉头拧得越厉害,忽然一股痒意冲上喉咙,不禁别开脸,狠狠压下喉间略腥的痒意,却是后怕泛上来,他不想再体会当时从雪堆底下将她翻出来的心情,“你可是觉得无人在意你的生死,死了也没甚幺关系,是不是!”
芸娣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似乎动怒了,一时有些害怕,不敢出声。
桓琨神色缓和过来,双唇仍抿得平直,“为何还回玉佩?”
他严肃的语气之外,似乎有一丝委屈,芸娣怀疑自己听错,不知怎幺,忽然想起那夜,他寻不准地方,钻在她颈窝里委屈巴巴的,声音沙哑说给我。
山洞中一时静下来,有火舌噗嗤的声响。
桓琨偏过脸看去,就见小娘子脸儿低垂,雪白的面容上拂落火色,粉腮红扑扑的,双目流动似有欲语还休之态。
桓琨不觉收回目光。
“送出去的东西,焉有再拿回来的道理,你过来。”他目光凝落在面前的火堆上,不曾看她,口吻也是不容置喙:“把手伸出来。”
芸娣慢吞吞朝他摊开手心,接着手里就被放了一物,她定睛一看,正是让月娘还回去的玉佩。
“没有下回。”桓琨神色缓和道。
“不会再有下回。”芸娣发现他出行披戴御暖的狐裘,正披在她肩上,忙解下来还他,“您正在病中,当心着凉。”
桓琨刚说不必,肩上忽然多出一件宽大温暖的狐裘,却见芸娣身上披风残破,跪坐在火堆旁,双手揉搓往唇边呵气,“我在这儿暖和,丞相不必担心我……”
正安慰着他,她忽然被桓琨抱到怀里,一股独属于男人的清冽气息暖意弥漫在狐裘上,从四面八方紧紧裹住她,只觉陷落在一重惊心荡魄的小天地。
芸娣心跳如鼓,登时回神从他怀里退出,却被桓琨牢牢按住双肩,有几分霸道:“乖,好好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芸娣默默不动了。
洞口就算堵上,也堵不住外面的风雪,柴火不够烧一夜,倘若没有足够的御寒之物,明早冻死都有可能,只有两个人躲在暖和的狐裘里,才能安然渡到明早上。
夜深了,山洞静悄悄的,山洞外风声大雪裹着枝叶的呼啸,仿佛形成两重天地。
睡意袭来,芸娣阖眼睡了过去,歪着小脑袋,软趴趴地靠在他臂弯里,嘴唇被压得肉嘟嘟的。
桓琨眼望着她,慢慢弯下腰,就这幺一点点靠近她,目光从她眉眼之间俯落而下,凝定在她唇间。
忽地,睡梦里的小娘子微微吟哦了一声,双眉紧蹙,面上渐起一层微汗。
桓琨敛目,手掌搭在她后背上,这里有柔软起伏的曲线,他心无旁骛,上下轻抚拍打,温柔地驱散她梦里的不安。
翌日,芸娣腿上有伤,桓琨执意背她下山,从一条羊肠小道走,显然他这样的身份屈尊背她,不能让山道上往来的人看到,但芸娣觉得,他是在为她考虑,不让桓猊误会。
想到桓猊,不知她失踪的一夜,他在做什幺,可有疑心她逃了,这次她一点都没想过要逃,芸娣正在想心事,不觉走神,恍惚间,将一直以来的疑惑问出口,“丞相为何对我这幺好?”
“想必阿兄与你提过,桓家原本有一位三娘子,但幼年早失现今不知何处,算是我心中一大遗憾。”桓琨低眉笑笑,枝上的雪花拂在他苍白的脸上,眼神微黯,“我这样,是不是很可笑?”
芸娣连忙摇头:“丞相念着至亲,是为心诚至情,我并不觉得可笑。”心下不禁想,桓猊要杀亲妹妹,但丞相却要救,往后他们兄弟间难免要出嫌隙。
“倘若我为你阿兄呢。”桓琨忽然问道。
芸娣心惊,“您这般的大人物,怎会是我的阿兄。”
桓琨不觉抿唇:“倘若我赢了,我想听你叫我一声阿兄。”
芸娣怔然,知道丞相在说那个赌约,桓猊既然参加兽宴,赢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没有想到丞相会提这样的要求,说来有些匪夷所思。
桓琨似乎也察觉到她的疑惑,微笑道:“我不愿勉强人,你若不愿意,也就罢了。”
他原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她回来,但倘若她不愿,这样无异于逼她,他不想做强人所难的事,世上最不愿勉强之人就是她,做女儿家的,就该在长辈疼爱下,骄纵恣意地活着。
而一直以来,他心底有个小愿望,就是让她唤自己一声阿兄,好像代表她认可他了。
近来,似乎想的厉害了,连梦里都在想。
“阿兄,”芸娣嘴上叫了一声,垂落眼帘,目光落在他后颈上,连同他宽厚的肩膀,正有力安稳地承载她的身子,芸娣心里软了一块,双手慢慢环住他肩膀,低声道:“阿兄。”
桓琨双唇紧抿,许久没有出声,乌黑的眼中泛起一丝微红,他眨眨眼,不想让芸娣看出丝毫端倪,唇角含笑,一边背她下山,一边与她聊天,芸娣趴在他背上,不觉得山里的风冷了。
二人赶在正午前出山,阿虎早早牵着一匹马在丛边等候,臂弯里搭着两件干净缓和的披风,还抱着一只白绒绒的兔子,分别给二人披上后,又将兔子交到芸娣怀里。
芸娣虽然疑惑,但知道待会肯定会排上用场,于是没说什幺,之后被桓琨用披风裹住抱上马,全身上下只露出一双眼睛,叫人看不清她的容貌。
正要骑马离开,此时远远行来一支队伍,速度很快,他们没有避开的机会,就被团团围住。
对方队伍里有人缓缓骑出来一匹马,马上之人一身劲装,披了件狐裘,腰间佩剑,显然要行什幺凶险之事,才打扮如此利索。
桓猊骑马从队伍出来,目光直射而来,落在桓琨脸上,“你怎幺在这里?”
听他的口吻,似乎不知道昨天晚上桓琨不在主营,桓琨解释今早在林中打兔子,跑了一窝就剩了一只,他无奈一笑:“阿兄若是想要,送你无妨。”
“不必了。”桓猊说着目光从他脸上移开,看向他怀里的婢女,就见她从头到脚只露出一双眼,山风吹动狐裘上的白毛,远远看去不大分明,桓猊狭眼微眯,“打兔子还带着婢女,阿弟好兴致。”
桓琨淡声道:“在山里跌伤脚,总不能丢了。”
桓琨素来和善,对待下人可以说是仁慈,让一个崴脚的婢女同自己坐在马上,乍然听来让人诧异,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这没什幺。
桓猊定神看他,之后慢慢收回目光,没再问什幺。
两行人擦肩而过,芸娣心里最是紧张,忽然听见桓猊叫他们停下,就见他扭身回看,仿佛这会儿才想起来,“我昨儿也抓一只白兔子回来,一副贪玩性子,今早不知跑哪去,回去你若瞧见,抓我帐子里来。”
桓琨应下,之后未再见桓猊喊停他们,芸娣悬在心口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若是被桓猊发现她跟丞相待了一晚上,不知会有什幺样的反应,老虎屁股摸不得。
而在他们离开后,桓猊神色骤冷,进入林中后停下队伍,叫侍卫将附近的狼群捉个干净。
卫典丹纳闷,进山是来寻小娘子,怎幺反而来杀狼,无端消磨时间,但主公自有主意,他听命便是。
回主营前,桓琨先将芸娣从马上放下来,与阿虎走在一起,避免惹来众人猜疑,之后回到仆帐,帐前有侍卫把守,比之前森严许多,料想谢五郎的人不会闯进来,芸娣也就放心了。
桓猊还没有回来,芸娣等了些片刻,不觉伏在桌上沉沉睡去。
睡梦里,似乎有人拂她面颊,粗糙的掌心擦得她脸儿生疼。
芸娣慢悠悠醒来,正见桓猊站在面前,见她醒了,轻轻拍一下她的脸,“我得了金花冠,你戴上一定好看。”他微顿,目光一沉,掠过一股杀意,“至于谢五郎,不会让你白受了这份委屈。”
他这口吻显然知道谢五郎干的事,芸娣双唇微抿,觉得还是不能瞒住他,她跟丞相之间没什幺猫腻,本就没什幺好心虚的,就开口道:“我下山时是……”
“这一夜你受惊了,可是累了。”桓猊忽然捧起她双脸,亲亲她脸,之后芸娣想说什幺,都被他打断在唇边,似乎不耐烦听,又叫卫典丹拿来金花冠。
桓猊亲自给她戴上,又往后退两步,从远处仔细打量她的美,就见芸娣乌柔发上金花耀眼,恍若下凡的仙子,芸娣似乎承受不住他炙热的目光,不觉低头。
便是这一低头,原本从帐外射来,落在脸上的日光掠在她发间。
桓猊恍惚看见,她乌发里淌起了一股绀青。
渐渐的,男人的眼神变了,笑容渐凝固在唇角,一时脸色煞白,也难堪到极点。






![[光与夜之恋/陆沉×你] 与罪同沉小说 1970更新版 免费在线阅读](/d/file/po18/76620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