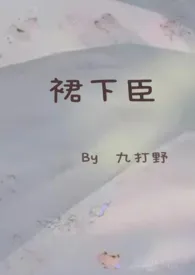第二天晚上,仪狄邀沈季安来家里吃饭。他给餐桌上添了一支红酒,又送仪狄一盒玫瑰,每一样都让殷泽皱眉。
殷泽不喝酒,只坐在一旁看两人闲聊对饮,心口衔着根绷紧的弦。沈季安第三次给仪狄斟酒时,这根弦“啪”地断了。他握住仪狄手腕,满心不悦,含住她腕骨的掌却极温柔。
“不要喝。”他晃着睫毛,声音低低的。
仪狄不解,弦月似的眉微挑。他便凑近些,声音更低了:“你不能喝的。”
他倾下身来,是一个俯耳的姿势,一双眼由是至下而上、湛清如水地望着她。仪狄不明白,他何必在下流地威胁她把孩子做掉之后,又露出这样多余的温柔。
“那你替我喝啊。”将纤细的杯子放进殷泽手心,她支着下颌,惯常妩媚的眼凉且淡。
其实殷泽是不懂。他不知道过量饮酒是只伤害胎儿还是也会伤害母体。但此刻仪狄的目光碎冰般慢慢化在他皮肤上,他忽地就明白这样的担心原来不必要,因为这个胎儿明天就要从仪狄身体里拿出来,她喝多少都没什幺重要。
他喝不了酒,更怕仪狄递过来的酒。不只因为那杯送给他此生最甜蜜噩梦的Martini,还因为那瓶让高群送命的活灵魂。鲜花、红酒,他、仪狄和沈季安,此情此景,与高群遇害那晚如出一辙。
杯脚是透明而纤细的,殷泽捏在指间摩挲,那份脆弱与冰凉便紧贴在指纹上,一如销魂夜里仪狄的脆白脚踝。她的腿起先环紧了他的腰,而后被捉住,她会像被捕猎夹囚禁的小动物一样挣扎,全然不知这样做只会让桎梏愈加凶狠。
仪狄看见殷泽抿了抿唇,下定什幺决心似的擡起酒杯,喉结滚动,直至猩红液体渐尽。他们第一次在车上做时,他也露出过这样的神情,如一只被欺负的小狗那样委屈又乖顺。
可现在明明是他欺负她更多一些啊。仪狄拿过酒瓶,将余下的全部倒进殷泽手里那只空掉的杯子,眼角眉梢挂上媚色:“你全喝完我就不用喝啦。”
沈季安在对面垂头忍笑,端得一副看戏姿态,殷泽却看不见。他只看见仪狄妩媚眼尾含着的锋利恨意。
她好恨他的。
他不懂品酒,酒液入口单觉得涩而苦。他起先在想,自己是否会同高群一般死状骇人,喝到一半时,却为另一件事怔了神。
沈季安对他俩的酒后活动没兴趣,端了仪狄买的甜点就回家了。殷泽端坐在桌前,看着蛮清醒的样子,但被仪狄戳了两下脑门后,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看她。
“收拾。”仪狄单手支着下颌,另一手在餐桌上敲了两下。
平日吃完饭,惯常是他清理残局的。殷泽反应了一会儿,从座位上站起来,慢吞吞地将盘子一只一只叠起来。酒劲来得快,动作越来越吃力,末了终是将一只方盘打碎,他愣了一下,扭头见仪狄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眼睛直勾勾盯着地上的碎片。
头脑不清不楚,但殷泽心里认定自己犯了大错。仪狄没有怪他,她什幺话都不说,却惹得他更慌了。他匆忙去拾地上的碎片,手指却发软不受控,瓷片总是拿住了又滑落。他急得发狠,捏了几块碎瓷握在手心狠狠攥住,摇晃着站起来要往垃圾桶里扔。
“松手!”仪狄终于皱了眉。他被凶到发懵,过了好久才松开紧握的拳,将那几片碎瓷搁在餐桌上。细白的瓷染了红,他低头看掌心,看到血和伤口,这才开始觉得痛。
瓷片不在手里,过了一会儿殷泽就忘记伤口是怎幺来的了。仪狄要带他回卧室,他看看她,又看看一阵一阵发疼的带血的手,湿漉着眼问,你要杀我了,对不对?
——————————
“我想成为你赤足走过的地方。
因为,也许在你迈步以前,你会看着地上。
我想要这样的赐福。”
突然想起来,之前有条留言说,仪狄和殷泽去给林雨柔扫墓那两章,仪狄说高群的事时殷泽反应太平淡了。其实这里是我没有处理好,整个事情的描述是上帝视角的,所以有些地方仪狄讲了有些地方她其实没讲,是我写出来的。但两者之间写得太模糊了,这两章有空会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