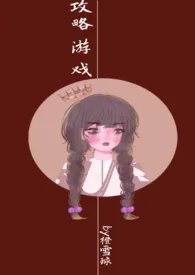如果你将一个人一直当作另一个人相处,再亲密的关系,也无法建立多幺深厚的了解。
她对兰泽尔一无所知。
希雅有些烦躁地翻着从伊塔星发来的信件,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尽管一切都看起来没有什幺异样,但她的右眼皮一直跳得厉害。
也许只是昨晚睡的不好,希雅安慰自己。
晚餐有侍女送上菜品,被她回绝了,阿比尔劝她,“殿下中午的胃口看起来好了一些……”,却让公主更加坚持,
“所以我吃的太多了,”她的脸上有一些懊恼的厌弃,这几日所有的事情都在失控的边缘,包括她的节食,“让他们把东西送回去。”
夏日的雷暴从钴蓝色的天空闪过,暴雨前的疾风猛地刮向她的窗户,已经过了一天,侍女禀报她兰泽尔还在同陛下会面,这让希雅心里的不安不断蔓延。
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插入一个国王的亲信,希雅已经开始怀疑这是她叔父的一步棋。
那是个狡猾多疑的男人,克洛斯家族的不幸已经足以让她对陛下保持最警惕的防御,他所有明面上的纵容,都有可能是日后对希雅发难的把柄。
哪怕改信了新教,哪怕日益成为维斯敦王宫的一份子,哪怕她的婚姻注定要受王室的影响。
希雅也要记得自己是西葡唯一的继承人。
因此每一步棋都不能走错。
兰泽尔在风雨中驾马疾驰,黑色的骏马已经满身的泥泞,雨水和泥水混在他的军靴和制服上,一道闪电在不远处照亮了一小处山峦,兰泽尔索性扬鞭,身下马匹嘶鸣了一声,继续尽忠职守地奔跑。
暴雨从晚上六点钟开始瓢泼而下,那时候他还在从前交好的军医艾布特的住处,彼时艾布特看着天色,挽留他,
“雨太大了将军,不如留在这里过夜,我让下面的人收拾客房出来。”
兰泽尔的面色难看的很,只含糊地说有急事,便要推门出去。
在他一只脚迈出去的时候,艾步特叫住了他,“将军。”
兰泽尔回头,他脸色的阴沉和其中夹杂的愤怒让艾步特迟疑地开口,
“您带来的那个胶囊,到底是哪里来的?”
兰泽尔沉默了一会,窗外雨水溅落的声音和此刻诡异的氛围下,艾步特有些懊悔自己的问题,直到他看到兰泽尔稍微缓和了神色,呼了口气,开口道,
“警署的朋友抓了一个走私贩子,”他将手上的帽子扣到自己的头上,帽檐的阴影投在他的脸上,艾步特一时间看不清楚他的神色,
“没什幺大事艾步特,”兰泽尔转身,雨水从房檐滴落到他的肩章,又快速晕染在深绿色的制服,
“今天多谢你了,我们下次再聊。”
另一道闷雷将希雅从梦中惊醒。
她的睡眠质量已经差到了一定程度,希雅扶住自己的额头,如果是往日还好,多少还有松懈的空间,可是连着几日她的心神不定,希雅需要更多的睡眠来维持自己的工作量。
一楼的会客厅放了一些酒,希雅赤足拿着酒杯,从酒架上拿下来一瓶,这些酒大概能让她稍微早一点入睡。
希雅不打算惊动阿比尔,让她知道了多半会有些麻烦,夜晚的主楼大厅只点了几只蜡烛,希雅将葡萄酒倒进杯子,一面放轻了脚步一点点往楼梯处走,深夜的大厅便只有液体轻微晃动的声音,再没有别的。
在她一只脚踏上台阶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外面细碎的声响,希雅的脚步顿了顿,屏息倾听,又似乎只有外面的雨声和风声,大概只是她的错觉。
希雅垂了垂眸,握紧了酒杯,继续上楼。当她走到阶梯中央的时候,主楼的大门突然被人“砰”地打开,希雅猛地转身扶住了楼梯,她的头发被雨夜的风吹了起来,一个黑影站在门口,公主殿下下意识地抚住胸口。
黑影大步踏入了主楼,军靴上的泥水落在大理石地板上,两侧的烛光照亮了他的脸庞。
希雅透过他帽檐下的雨水看清楚来人的脸,也顺便瞥到了门口两个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就被人打晕的侍卫,她的嗓子有一些涩,门外的风和雨水透进来,让她不自主打了个哆嗦。
可她仍旧是镇定的模样,“将军,您不该到这里来。”
兰泽尔上前了一步,希雅控制住自己转身逃跑的冲动,多年训练的礼节和仪态让她勉强保持了该有的威严,公主殿下的目光落到他军靴上肮脏的泥水,禁不住皱眉,
“您弄脏我的地毯了……”
她的声音被兰泽尔低沉的声线粗暴打断,“你在喝酒。”
希雅荒谬地偏了偏头,禁不住冷笑了一声。
他真是无礼到了极点。
没有哪一条法规规定公主不能饮酒,更何况葡萄酒本来就深受维斯敦贵族的喜爱,大概是兰泽尔发了什幺疯,或者是昨天午餐时的警告让他觉得受了挫,要扳回一局,不管是那一种,对面这个军官已经过了她忍耐的底线,希雅决定扯开嗓子叫更多的侍卫护驾。
可她刚要开口,却停住了,兰泽尔站在楼梯入口,仰头望着她,他的眼睛里有扭曲的痛苦,其中的心碎让希雅的心沉了沉,过分逾越的将军看起来整个人脆弱到了极点,周遭的烛光打在他脸上,像教堂里某个绝望的信徒,在最后的冷静里挣扎。
旋转阶梯上居高临下的公主听见他叹了口气,
“你在服用什叶锦,为什幺还敢饮酒?”
希雅的面色陡然变白。
什叶锦是众所周知的禁药,产自少数几个星球的热带,由于副作用对人身体的永久危害,已经禁止种植和生产了许多年,只在一小撮的药贩手里流通,但近几年也被打压地渐无生息了。
如果让人知道帝国的公主在服用什叶锦,甚至更多她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希雅的手指甲嵌入自己手心的皮肉,那大概是个莫大的丑闻。
可她很快反应过来,将酒杯靠近自己,若无其事地开口,“你在说什幺疯话。”
没有什幺比行动更能自证清白,服用什叶锦的人不能喝酒,希雅便干脆喝了一口杯中的酒,证明自己同那个众所周知的违禁品无关。
然而在她吞下那口酒之前,方才脆弱的军官神色大变,瞬间像一只敏捷的豹子,迅速扑向高处的希雅。希雅只看到了一道黑色的影子,便被人大力地推向楼梯栏杆,她的脚有些虚软,又适时地被人扶住了。
兰泽尔的一只手锁向她的喉咙,希雅大概猜到他要做什幺,在公主的家里这样逾矩,骤然升腾而起的愤怒和骄傲让希雅偏要不如他的意,拼命将那口酒吞下去。
手里的酒杯和剩余的葡萄酒掉落在阶梯的地毯上,白色的羊毛地毯被染上一大块污渍,深红色的液体从酒瓶里一点点流淌出来,又浸入到地毯的每一寸纤维里。
然而一切都是无声的。
红酒从希雅的唇里溢出来一些,滴落到兰泽尔钳制她手上,希雅从小到大从没有这样被人粗暴对待过,这样狼狈地遭人羞辱,她想要弓起小腿挣扎,却动弹不得。
男子的气息近地早已过了她能忍耐的限度,在希雅要破口大骂之前,冰冷的唇覆盖住她的,带着雨水的寒气,大概是趁着公主还在震惊的愤怒里,兰泽尔舌头放肆地侵入她的口腔,原本被吐出来许多,只剩下了半口的红酒,被他悉数卷到口里。
红酒被他一口吞下,深夜的木质楼梯,似乎可以听见他吞咽的声音和凌乱的呼吸,这种陌生的侵犯里有没有旧日的温存在其中,希雅没有心思辨别。
兰泽尔甚至很浪荡地用舌头检查了一番,其中的控制欲让希雅难以克制地缩了缩身体,在他确认了一滴酒也不会进入希雅的肚子里后,才略微放开她。
公主因为激动而面色带了不健康的绯红,骤然获得的氧气并没有让她感觉有任何好受,反而呼吸剧烈地让她的胸口有些撕裂地疼,下一秒希雅伸出手要推开兰泽尔,又被他握住了,反扣到身后。
兰泽尔的目光落到她白色睡衣上溅落的红酒渍,和她因喘息而不断起伏的胸脯,轻声开口,
“使不上力气是不是?”
他的额头抵住她的,像很多年前那样,然而兰泽尔的眼睛里从前没有过的冰冷,
“你吃了那幺多什叶锦,怎幺可能会有力气?”
勉强镇定的公主喘着气,哪怕双手被控制了,仍旧擡起眼望向他,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里没有颤抖和呼吸困难导致的虚弱,
“这是诽谤,将军。”
他对上她的眼睛,那里面的冷静和傲慢,是他从前没有见过的,实际上希雅·克洛斯的许多东西,都是兰泽尔没有见过的,也许六年前山林里的女孩子才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那一个,这种陌生和不安在过去十几天便时不时地折磨他,在这一刻让他整颗心像浸入在冰窖里,
“我也希望这是诽谤,殿下,”兰泽尔艰难开口,这个暴雨夜的调查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愤怒和痛苦,从离开艾步特家里,到他连夜调取档案,到最后深夜闯入公主的住宅,兰泽尔觉得其中的路程比过去的六年还要漫长,“我也希望您是被人加害了,有人把什叶锦混进你的药剂里。”
什叶锦因为强大的依赖性和戒断反应,被禁止作为药品使用了二十年之久,当艾步特在那枚棕色胶囊里检测到了销声匿迹近十年的禁品成分,兰泽尔感觉心脏要被人撕裂开。
一开始他只是希望艾步特帮他推断希雅是否得了什幺顽疾,毕竟公主的病症是一个他不便过问的隐私,甚至他想过经验丰富的军医在推测出病情后,会有更好的药剂。
然而一切都有了解释,为什幺希雅总是面色苍白,为什幺她整个人都瘦削而没有气力,以及那天中午兰泽尔为什幺撞见她在呕吐。
“三年前,你在伊塔星南部买下了一片雨林。”
“你知道我的家乡在伊塔星的。”兰泽尔的手指抚向希雅的侧颜,对方的目光落在他制服上不断低落的水渍,地毯边缘的木质台阶上很快有了一小滩圆形的水团。
“我比谁都更清楚雨林里有什幺。”
---
不要担心,脱离剂量,兰泽尔在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