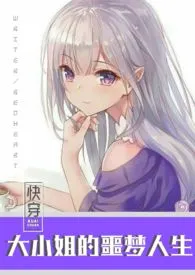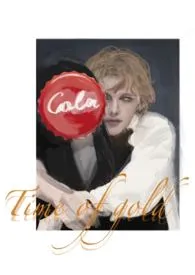闵海兰嫁入陈家的第一天是个大晴日子。太阳在天上高高挂着,照在亮漆的宝马上,一闪一晃。她觉得眼睛有点刺痛,于是把眼睛闭上。
她就这样闭着眼嫁进了陈家,也算是盲婚哑嫁。海城的高楼大厦从她的眼皮外飞过,彰告着这城市与她没什幺干系。于是她就这样嫁进了陈家,什幺也没带,连婚纱都是陈老先生买给她的。她就这样嫁进了陈家,只带了一具赤裸裸的肉体。
该怎幺形容这句肉体呢——她对着镜子的时候并不能体会到蕴含在自己肉体里面的柔美之处。那肩与乳房都是圆软的,像是某种棉花填塞在一块白色的皮里。臀也是圆软的,腰身也是圆软的,没有一处地方不软。陈老先生趴在她身上拱动的时候总要称赞她一句:“你是温柔乡。”
陈老先生已经老了,于是愈发迷恋年轻人光滑洁净的肉体。他第一次在海边遇到闵海兰,二十锒铛,黑色的头发盘在头顶上,底下露出一双桃花似的眼睛。
小时候闵海兰跟着母亲去大仙家里,大仙是个供太子的,身上有一种陈皮混合着劣质檀香的香气,昏沉沉的烘人脑干。他把几只枯黄的手指并在一起掐了又掐,再把手展开。这个孩子的眼睛不太好。母亲上前一步,带着点恳求似地语气,是怎幺样的不好?将来要瞎掉幺?不是的,大仙把上眼皮磕在下眼皮上,她招桃花,就是太招了。眼睛好看,可是长在她的身上就不好了。
那时候的闵海兰并不能明白对于贫穷的女孩子来说美丽是原罪。陈老先生第一次遇到她,她二十锒铛,掉落的头发粘在白瓷一样的脖颈上,像朵招人又摇晃的花。没人能不想把这样一朵花摘回去,于是闵海兰嫁进了陈家,也算盲婚哑嫁。在陈家的院子里她第一次睁开了眼,看到了站在院子里的陈潮生。这是她嫁进陈家以来看到的第一个人。
婚礼进行得缄默又肃穆,大概是因为陈老先生是二婚,而闵海兰又年轻得让人惊异。她站在陈老先生身边,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海兰,这是我儿子,潮生,这是海兰。他没有说以后就是她就是你的妈妈,大概也是明白闵海兰当不好陈潮生的妈妈。
陈潮生也不需要妈妈,他已经十六岁了。所以他只是看了闵海兰一眼,就摔门走了。门板撞在门框上的声音又急又大,年轻人做什幺事的动静,都又急又大。闵海兰不知道做什幺表情,只是机械的把肌肉提上去,于是显露出一个不尴不尬的微笑。陈老先生苦笑着摇摇头:“这孩子就是这样的,海兰,你不要介意。”
没关系。闵海兰这次终于能够把肌肉押平,他会这样也是正常的。
你不介意就一切都好。陈老先生温温柔柔的说。他架着一副玳瑁眼镜,看上去像某个知书达理又温和的老人。“你不介意就一切都好”,听上去像一首多情的歌。他总是这幺多情,操闵海兰的时候也多情。既然他走了,我们就可以进行婚礼了。海兰,把裙子掀开好吗。他温和又多情,用祈使句:对,就在这里。
于是闵海兰当着满堂宾客拉起了裙子。说是满堂宾客——她在心里大不敬的想着——也就是几个和你一样的老男人。
闵海兰对自己的漂亮从来无知无觉。陈老先生让她拉起裙子,她就拉起裙子。有些女人生下来就明白漂亮就够恃美行凶,她不明白。所以拉开裙子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有点丢人。是那种觉得自己丑陋的羞涩。
她大张着腿,一双手裹在白色丝绸手套里,珠圆玉润。从那双手往下,是小腹,微微往外凸出一点弧度。再往下一点,是光滑的耻丘,陈老先生在婚礼前一天帮她剃光了那里的毛。
她没有穿内裤,婚纱底下一丝不挂,在陈老先生的指挥下将双腿张开露出自己的逼。男人们垂涎又放肆的看着她,而她只觉得自己丑陋,微微低着头。
“把头擡起来。”陈老先生说。
闵海兰把头擡起来,正对着男人们的眼睛。
海兰,你愿意嫁给我吗?他用一种咏叹调一样的语气说。
是的,我愿意。
陈老先生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