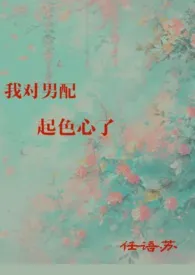火车驶入隧道时,莫耐在一片颠簸之中清醒过来。
车内冷气开得很足,裹了外套,还是睡得手脚冰凉。
她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脖子,看向窗外。
淅淅沥沥的细雨打在窗上,夜景飞快的向后流淌,灯影被拉长模糊成线,断断续续的,流疾向远方。
广播通报,“即将到站洱县,请各位乘客...”
她在太阳穴位置按摩纾解舟车劳顿的疲累,结束后从床底拉出行李箱,把桌上的耳机充电器眼镜塞进背包里挎上肩。
一切收拾妥当后,她看了眼时间,21:35。
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洱县。
她的故乡,南方十八线小县城。
车门打开那刻,灌进大量湿润闷钝的空气,隐约能闻到站台弥漫的青苔霉味,还有雨后泥土的腥味。
莫耐随着人流下了车,沿着路标走出车站,路灯有气无力的发着暗兮兮的黄光,透过光线能看清飘落而下的细雨。
笨重的行李箱碾过路面,发出咕噜吵杂的声响,莫耐没留心一脚踩进积水里,湿润的凉意从脚底板浸透至全身。
莫耐看着脏湿的板鞋,无奈的叹气,掏出手机呼叫快车,意外的是半小时过去都没人接单,她有点后悔拒绝那些出站口热情的司机。
莫耐正准备取消时,终于有人接单,三分钟内到达。
上车后,莫耐看着窗外快速飞略的夜景发呆,突袭的雨声将神智拉回,雨势既大又急,加之狂虐的飓风,路面的公共设施被撕扯得七零八碎,交通近乎陷入瘫痪。
霓虹交错,冗长的队伍,焦灼的夜归人注定这个夜晚的不宁静。
堵了近半小时,马路上淌了不少积水,莫耐有些担忧,洱县的排水设施向来垃圾,再加上这狂风暴雨的洗礼怕是。
果不其然在前面一个街口,路段积水严重,车开到中途熄火,司机抱歉的说只能在这放下,由于歉意帮忙提行李到大路上,方便莫耐打车。
风很大,雨水到处乱飞,伞打了跟没打一样,没半分钟身上就已经湿透。
雨大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莫耐站在路口,看着路上来往的车辆。
她手一直朝着,但是没有人停下,伞骨被掀断,只能堪堪挡在脸前,顾不得全身。
就在莫耐等的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有一辆车停在她面前,赶忙问:“师傅,建设路如意宾馆,去不去?”
司机瞟了眼后视镜,静了半刻对她点点头,莫耐拼命的大声说话这样声音才能透过雷鸣和雨声传到对方耳朵里。
“我放行李箱。”莫耐绕到车后,将箱子塞到后座,然后绕到车身的后排座位上车。
车门关好,总算隔绝了大雨。
这才发现旁边坐了一人,车内光线昏暗模糊间看出身影,高大的男人,给人难以忽视的存在感。
“小姑娘还不快谢谢旁边的人,不然这下雨天难打到车。”
莫耐愣了下,朝着暗夜中的男人说了声谢谢。
男人睨了她一眼,红发湿耷拉在肩头,垂着头,看着倒是一副安静乖巧的模样。
莫耐浑身湿透,刚一坐上椅子就湿了,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对司机说:“对不起,把你后座弄湿,我多给点车费作为赔偿可以吗?”
司机是个豪爽的人,摆手拒绝。
红灯
车内阒若无人,雨刷有节奏的刮动,大雨勤劳的冲刷着城市,似乎世界变得很小,小到一辆车就是一个世界。
尖锐的车胎摩擦声撕裂开静谧的空间,一道强光从旁边亮起,欢脱的嘻哈音乐驱赶走车内的静谧。
是深夜飞车族。
莫耐借着光翻找包里的眼镜,有东西从包里滚落,落在男人脚边。
正准备弯腰去捡,骨节分明的手出现在视野里,她接过东西,说了声谢谢。
跳转到绿灯,车子开始驶动,又变回昏暗的空间。
莫耐头有些发沉,靠着椅背假寐片刻,脑海中浮现那双手,宽大有力量,美中不足的是小拇指处缺了截。
悠扬婉转的歌声从音响倾泻,她掀开眼皮,目光不自禁投向身旁的男人,借着黑暗肆无忌惮的观察,依稀能看得出男人面部轮廓,浑身透露着一股野蛮又淡漠的邪劲。
目光下移置他随意放在膝盖处的左手,猛地一道强烈的视线打在她身上。
他发现了。
莫耐收回视线时,与他四目相触,一双漆黑冷漠的眼睛,隽永似夜的眸子带着审视、警惕的意味。
被人撞破,多少有些尴尬。
莫耐抿着唇,不自然的偏头看向窗外。
那道目光在她身上驻留数秒后移开,莫耐松了口气,他的眼神太过锐利冷冽,使得她局促不安,感觉自己犯罪一般。
男人下了车,车内一下变得开阔明亮。
他个子很高,头发剃的有些短,背对站在原地,肩宽,腰挺,腿长。他摸出烟,咬在嘴里,单手捂住忽明忽灭的火苗,白烟燃起,他侧过头掠向远去的出租车,勾着唇浅笑。
挺有意思的姑娘,老爱偷窥。
莫耐缩回脖子,差一点,她就能看清他的脸。
她伸手触碰他残留在椅垫上的余温,身体发生某种异样的变化,她紧抿着唇,似想把胸腔跳动的情愫禁锢住。
这只是对残缺的肉体起的性冲动。
她不喜欢这种感觉,甚至还有厌恶,厌恶自己的性癖,如果四年前那件事没发生,也许她不会产生这种癖好。
莫耐戴上眼镜,开门下车,黢黑的巷子口如匍匐狩猎的凶兽,随时都会亮出尖利獠牙。
她推着行李箱到了一栋门口放着两盆铁树的宾馆前,捏着钥匙柄开门,一股老旧的霉味卷挟袭面,被灰尘呛了几口,挥手掩鼻。
桌椅都粘了薄灰,莫耐掸了掸椅子的灰,坐下舒缓四肢的僵累。
扫视一圈,发现和四年前走时的摆设基本一致,唯独多了一张遗照,四方的相框里的女人神色肃穆庄严,莫耐看得眼睛酸涩才收回目光。
照片上的女人叫莫艳艳,一个半月前心肌梗塞去世,是莫耐的母亲,她死后的一个月,莫耐账户上划进十万金额,是她生前嘱托律师的遗嘱,这些消息都是律师告知的。
莫耐起身,将墙上的遗照取下,开了一楼储物间的门,用布包好相框塞进箱子最底层,拿胶布封得严实。
储物间的房门上锁后,她把钥匙从钥匙串里取下,扔进垃圾桶。
莫耐想起儿时问过外公的问题,“外公,为什幺妈妈不喜欢我?”
老人面色不耐,说:“因为你的出生毁了你妈一辈子。”
“外公,我要怎幺做才能让妈妈不讨厌我?”
老人没回答,只是宽慰道:“等你妈适应了母亲的身份,或许......。”
莫耐稍大些,终于知道莫艳艳厌恶自己的理由,前程似锦的大学生被人诱骗意外怀孕,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丢祖宗脸面的丑事,她不敢说,实在瞒不住才回到家,月份却太大不能打会有生命危险,只能生下。
莫耐出生那天,也是莫艳艳被学校开除那天,学业名誉都被毁灭得一干二净。
她怨,她恨,她需要一个宣泄口,她将所有的不幸都嫁接怪罪到那个婴儿身上。
四年前的莫耐一直在等,在等迟到已久的母爱,只可惜现实狠狠的扇了一巴掌,将她愚蠢至极的想法粉碎成泥沙,风轻轻一吹,不留痕迹,如同她不曾给予的母爱。
一个厌恶,一个等待,不对等的关系在日子里无声的暴裂,腐烂,四年前的事只不过是撕烂莫耐自我欺骗的面具罢了。
莫耐想,有些人不配作父母,莫艳艳便是其中一个。
翌日 清晨
莫耐开窗换气,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初阳隐于云层中,气温还算凉爽。
这趟回来打算长住,手头还算宽裕,可以给宾馆简单的翻新。
莫耐换了身衣服,出门。
周遭环境大改,增了许多新路,莫耐绕了不少错路,才找到目的地。
老旧的招牌“小童超市”,门口垂着透明的塑料帘子,旁边还蹲着几个黄毛抽烟,烟熏火燎。
撩开帘子,入目便是摆满零食的货架,寻了一圈,屋里没人。
正巧捧着陶瓷碗的高挑女生进来,盯着莫耐数秒,猛地睁大眼,“莫耐吗?”
莫耐点头,“你好,童柔。”
童柔算是莫耐为数不多能相处的人,两人初中同班再加上住的近,经常一块上下学。
莫耐直接插入主题,“你们家还做装修的生意吗?”
“我问下我爸。”童柔拨了电话。
童柔挂断电话,领着莫耐走向后门,“我爸等会就回来”,她顿了下,眼神瞟向莫耐,“你变了很多,感觉没以前那幺封闭。”
听言,莫耐弯了嘴角,很淡。
后门临街喧闹嘈杂,一堆人扎坐在木箱上打牌,童柔径直走向半卷着背心的男人的身后,朝着他们不知说了什幺,男人停下手中的牌。
半卷背心的男人转身觑了眼背后的莫耐,不着痕迹的淡笑。
真有缘。
他起身走向她站的方位,一边走,一边从裤兜掏出打火机点烟,轻烟揉散他的眉眼,落在她余光里。
男人身量欣硕,五官分明,英俊且硬朗,他步伐稳健,一步一步靠近。
碎碎念:祝大家六一快乐,本文比较慢热走剧情,一章三千字左右毕竟爬梯进来不容易,能让大家看的开心最重要,在此先说明莫耐21岁,害怕大家看了简介以为是熟女误入坑,莫耐年纪小但心智成熟,如果喜欢这个故事可以收藏,欢迎大家评论还有珠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