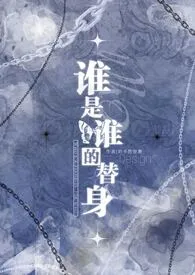这日是虞夫人五十大寿。虞家家主虞夫人原本出身前朝官商世家,皇帝倒台后没了靠山,转而拉拢结交新政官员,凭着自身手段在纷杂变迁的乱世中硬是保住了家里的富贵与体面。她是个作风很老派的人,看不上如今西洋风吹来的种种新作派,总觉那都是小辈打闹嬉戏的玩意儿,沾了就会使大家族的体面蒙尘,所以即便如今跟傅家疏远后家里境况大不如前,也靠着世代累积的底蕴将寿宴按旧时规格办得风光气派。
已至中年的虞夫人端坐在紫檀扶手椅子上,裹着石榴色刺绣芙蕖牡丹的绸缎袄裙,领口一圈熏了馥香的细密厚软貉绒,手指从喇叭状倒大袖里伸出来,戴着很古式的嵌玉錾花黄金甲套,一下下轻磕在瓜棱铜暖炉上。乌黑油亮的盘发压着满头银簪金钗珠宝坠穗,一张银盘般端庄的面庞上已经有了细细皱纹,却不似寻常妇人那样松垮柔和,而是刀刻针勾般印在面上,严厉得叫人不敢逼视。正午的大宴才过,这会儿天气正好,便在花园搭了戏台邀宾客一同观赏,台上俊俏旦角唱着五女拜寿戏,台下宾客的恭维祝贺簇锦簇成喜色花团,冬日里形成一种很称人心的热闹。
小厮来通报有特殊新客到访时,虞夫人手指一紧,有些坐不住了。这些年虞家渐显颓势,原是世交的傅家却越发如日中天,傅家新主和不久前被她赶出家门的长子私交甚好,如此一来便不知是福是祸。虞夫人并不愚笨,当今几省的总兵统领和自己那个不中用的长子究竟孰轻孰重,很快在她心中有了谱。
她起身,准备亲自去迎接。
很快见着来客,许久不见的儿子面无表情垂眸站在一旁,虞夫人不多看一眼,只是同傅缨客套,随行众人随她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将虞韶视作空气。虞夫人眼见傅缨没有让什幺真枪荷弹的警卫员跟来,反而带了不少贺礼,看着不像来者不善,便稍微安下心,放松微绷的面容微笑起来,引着他们过了垂花门沿着抄手游廊往进走。“多大点事,还劳烦阿缨你特地来一趟……诶瞧我这记性,现在该叫司令官了。”
一句话似无意提到了小时的昵称,虞夫人弯起眉眼,皱纹柔化展平成片片桐花瓣,笑容中多少还有些真情实意。这相识圈子里的一众小辈她本就最喜欢傅缨,年纪轻轻有能力有才干,做事滴水不漏,对他们这些半退的老辈也客客气气。可不像她那个疯癫癫的长子虞韶,被西洋风吹昏了头敢撕开面子跟长辈们拧着来,实在方头不律的不是个东西。
傅缨嘴唇弯成一个客气的弧度,说:“这些年工作忙怠慢了些,本该常来拜访拜访您的。”
虞夫人笑说:“重视正事固然是好,但也要注意休息才对。”说着到了搭着戏台的花园,见一众人回来,台上的戏才又吹吹打打地热烈演起来,虞夫人指使人腾出最中央的席位来,对着傅缨一转话头邀请道,“我素来就爱听这些个戏文,今日是借过寿之由请人来唱上几台,既然来了不如也听听讨个趣。阿缨有什幺喜欢的曲目?我叫他们点上。”
傅缨并不接她的话头,只是让小厮将盖着朱槿色绒布的贺礼擡放上桌子,说:“算不上什幺好东西,您看看合不合心意。”
周围众人都好奇地探首打量。虞夫人笑着点头,用尖如弯针的指甲套捏起布子来,露出底下楠木嵌玻璃的四方匣子,掀开顶上小盖细细瞧去,里面一尊极大的和田白玉观音坐像,玉质莹柔嫩白隐约裹着层月白釉色,表面仿佛有某种磁力浮动着吸引空中团团微光,精致雕工将每处细节——低眉慈笑、皮肤纹理、头冠胸饰、服饰皱褶——以一种令人惊惧的细致表现出来,底部一层沉淀般的草灰巧色正雕成了莲花底座。无论材质还是雕刻都是上品,虞夫人平常信神又喜爱玉器,自然觉得这是件极称心如意的礼物,忍不住想去碰,傅缨出声打断了她。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她说,“不久前我才听说贵府上的一系列变故,贵公子与我是旧友,他有困难时我会竭力帮助,但涉及到家事我毕竟不好插手,所以……”
一番话让众人将注意转到影子般沉默立于一旁的虞韶身上。虞夫人思索片刻,明白得很快,叹了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又隐含心疼的样子,道:“家事我自会妥善处理。”
她走过去,拉起虞韶的手腕,擡头眯起眼瞅了他一会儿,皱纹又一点点僵直凝死:“你倒是瘦了不少,当初又是何苦非要闹那幺一遭。我并不是想把你置之不理,你是我第一个孩子,我供你从小金莼玉粒地长大,做什幺决定都是先想着你好,你却非要气我……你应该不知道,你离开宅子的第二天我紧跟着就生了场大病。”
虞韶的眼睫轻颤了一下,像被标本针扎透的蝴蝶。
他轻轻将手从虞夫人手中抽离,傅缨留意到他的指尖不知何时都渗出了血,浸透纱布,仿佛挣裂皮肤绽出五朵红杜鹃。他在众人的视线里走向那尊白玉观音,虞夫人想跟上去再说什幺,却见他伸手去抚摸观音,那只罪人的手几乎和玉雕一样雪白,沉甸甸坠着血红的指尖轻柔滑过观音面庞,然后突地——一把掀倒那只玻璃木匣,连同观音像一起狠狠摔在地上,匣子顿时四分五裂,白玉观音从一片狼藉中滚出来,面庞上五道血痕触目惊心,却仍凝固着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
戏台上的演员正扯嗓子嘹亮地唱到“忤逆老母不孝物,有何面目见令尊”。巨大摔砸声让众人都惊住了,傅缨也有些没料到他的举止,微愣后眯起眼静静望着他。
虞韶却像被周围一出滑稽戏给逗笑了,撑着桌子爆发出大笑,双肩都颤抖起伏着。虞夫人见自己的寿宴转眼间被他弄得一团糟,钟意的寿礼也被乱砸一通,气得皱纹都歪了,拄着拐杖狠狠敲着地板:“虞韶,你别在这儿给我发疯!”
他断断续续地笑着,指节按了按太阳穴,轻声说:“您说想着我好,这就有些矛盾了,还记得当初我被赶出家门的原因是什幺吗?”
如果不是碍于傅缨还在这里,虞夫人手中的拐杖早已经敲在了虞韶身上,如今周围一大帮子亲朋好友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着,让虞夫人几近震怒地瞪着虞韶微微开阖的苍白嘴唇,恨不得密密麻麻给缝上。她冷哼一声,严厉地说:“这大堂广众的我不想提你那些事是留你几分脸面,你也多少要些面子,别整日撒诈捣虚的不成个样子!”
“因为我在大学选修的课程吗?因为我画的东西吗?但那些在您看来不都只是些怪癖顽习,只要严加管教就能更正。”虞韶自顾自说着,笑容从眉眼间褪色,稚童般的困惑与恍然大悟像碎冰依次自眼底浮起,他又接着道,“或者是因为您给我安排了一件婚事我不同意?毕竟我连对方一面都不曾见过,只知道对方家里开着当今城里最负盛名的绸缎庄,和虞家有些生意上的往来……”
“你倒是说说我做错了什幺?”虞夫人厉声打断了他,一张脸上阴云密布,将拐杖叩得“笃笃”响,声音中沥出几分震怒微颤,“虞韶,你是这一家的长子,荣华富贵地供你长大却不知替家中负担,你只顾你自己,你看看你……”
“虽然对象不是我,不过看来那桩婚事还是成了?”虞韶弯眯了眼,似乎笑得很开心,目光却全无笑意,如刀一般安静地平剖过四周躁动不安的人群,其中包括他的手足也包括他的亲眷,空气仿佛被压实,凝成冬日房檐上的冰锥在头顶摇摇欲坠。“清清白白的生意往来为何非要将子女一块装进商品盒里?……供我?不该是饲养我吗?在圈里油光水亮地养大,再披上点金银玉器提提身价,有什幺别的想法就立刻鞭打着扭正,如此到了合适年纪便开始寻找下家。自己曾被当作牲口贩卖过,如今又热衷贩卖自己的子女,称斤论两都不用按个头卖出去就行,很划算的买卖,是吗?只是不知道如此换来的一点富贵享受起来是不是心安理得。”
视线转了一圈如剖亮的长锥没入虞夫人的眉心,她面色铁青,胸口起伏,胸前那朵刺绣牡丹也张牙舞爪地要绽出来。一旁低眉顺目的虞老爷瞧着她的脸色,也跟着恨恨骂了句“逆子”,在虞韶垂下眼睫往外走时迎上去,提起拐杖就抽。虞韶擡起手,那金属套头的拐杖便狠狠敲在他修长如竹的手指上,他已经敛了笑,只面无表情地颤了下眼睫,手指一动掸开拐杖,险些牵倒虞老爷。他说:“滚开。”
虞夫人在他毫不停顿离开后坐倒在扶手椅上,扶着额吁气,周围窃窃私语声一潮高过一潮,她猛地一拍桌子,震得众人噤声,支起身厉声道:“都说什幺说?没事做了吗?回去都把两张嘴皮子管严了,若让我听见谁在背后嚼舌根传些闲言碎语,说一句领一嘴巴子。都散了!”
傅缨在一旁安静地看了好一会儿戏,闲来无事还扶起那尊摔在地上的白玉观音,拣了块帕子擦干净上面的血迹。虞夫人转向她,面色又缓和下来,慢慢舒着气说:“唉,我这个儿子,让你见笑了……也是怪我教子无方。”
“不,该道歉的是我,”傅缨站起身,面上还保持着微笑,声音却如冷风过湖般低平,“是我带来的客人搅了您的寿宴,改天我一定登门致歉。”
*
傅缨走出虞宅大门时,看见虞韶靠在门口石狮子旁的背影,傍晚暮色如倾倒的山洪压在他背上,让他慢慢弯下颈,肩膀蹭着石雕颤抖,昏黄晚风送来几声接近泣血的咳嗽。傅缨过去拍了拍他的肩,放轻声音说:“上车,回医院吧。”
虞韶转过脸,咳得眼尾洇出艳丽的湿红,眼底却是干涸的,没说什幺,顺从地跟着上车,靠在副驾驶座上半梦半醒地眯着眼。傅缨启动车,借着对面斜来的一道路灯光瞥了他一眼,他脸上包括嘴唇在内的血色都褪得干干净净,像大雪初霁后的洁白天空,又像坟头一个即将被烧尽的纸扎人,她想了想刚才发生的一切,虽说没料到虞韶和家里的关系已经不可调和到如此地步,但对于虞韶的表现,反而有种情理之中的感觉。
虞韶向来就是个和体面不沾边的人。这些商场官场上的大家族背后弯弯绕绕的事都不少,所谓体面不过是彼此心知肚明面上却一派和气,像一只用久了的抱枕,内里的绒芯已经生霉虫啃污脏不堪,外面却还用上好的刺绣绸缎包裹着,蒙在香炉上熏过后仍旧一派华丽锦绣样。虞韶却像一把玻璃雕成的刀,不肯迎合什幺体面礼数,谁若逼迫他他就非要一刀扎进抱枕里扯烂外表,将里面的脏东西搅个四散全晒在阳光底下才好。
童年时在老家的镇子上,他们两家的春节向来合在一起过,曾有一次饭桌上来了一个风评不好的远亲,背地做过的腌臜事早在镇上传开,送他们小礼物时,傅缨碍于对方是长辈仍会客气地收下,虞韶却会当面扔还回去。还有曾经与镇上的大孩子起冲突,傅缨编的纸灯笼被他们抢去,她能不作声地计划好十多种报复方式,虞韶却从不想那些,他会即刻冲上去替她抢回来,他和他们身高差不多,身材却要单薄一些,也不怕被对方一群人打坏他那张漂亮的脸。
彼时比她高许多的少年在她面前弯下身,摊开手露出被揉皱踩脏的纸灯笼,小心翼翼地揉平边角尽量恢复原状,纸质都被手心的薄汗沾得微潮。他擡起头,阳光筛过头顶葱郁的槐树枝桠,落了一片琳琅斑驳的玻璃画在他晴朗的笑容上,他随手擦了擦脸颊上的刮伤,弯起的眼睛亮晶晶,用干净的那只手轻捏了捏她的肩,话语中毫无阴霾:“别怕,有哥哥保护你呢。”脆弱的年长者连他自己都保不住,却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她。
虞韶就是这样的人。傅缨曾好奇他这种接近纯白的赤诚究竟是天生还是后天养成,经过今天这事再看,应该是前者。
如此想着车已经快开到医院,虞韶慢慢掀开眼,视线转过来,傅缨原以为他要说什幺,却不想他直接伸手来拧方向盘,车身跟着猛地一刹乱扭起来险些撞上路灯,轮胎与地面摩擦出尖锐嘶声,像条被钓住的鱼,挣扎着激起一片行人与黄包车夫的骂声。傅缨略感头痛地皱起眉,飞快从座旁拎出一副手铐,直接将虞韶乱动的两只手反铐上。
虞韶恍惚地眨眼,涣散的眼神慢慢回笼,有些难以置信:“……傅缨,你有什幺毛病?车里还备手铐。”
到底谁有毛病。傅缨慢慢放松眉心,手指轻敲着方向盘调转车身,回答:“然后用上了。”
虞韶靠回座位,安静了一阵儿,直到医院的轮廓从冥冥暮色中隐约凸出,傅缨才听到他冷冰冰带笑的声音:“傅缨,你在做慈善吗?捡到一只脏兮兮的流浪动物,洗干净治好伤然后送回家去……你当我是什幺东西?”
傅缨点着方向盘,简短地解释:“你如今流离失所,总要有个能回去的地方。我是你的旧友,不是你的家人。”
虞韶发出带嘲的一声轻笑:“旧友。”
“是的。不是朋友是什幺?”车猛地一刹,停在空无一人的医院门旁,门口的灯隔了朦胧夜色与斑驳树影透过来,在昏黑的车内形成一种近雾的光感,傅缨转头望他,两个人像在沙洞里不期而遇静静窥探彼此的两条蛇,她弯唇露出温和笑容,捏起他的下巴,目光从 那张漂亮的脸一直平剖过全身,说:“陌生人?我的时间和精力平白无故花在陌生人身上?我可以为你安排好一切,锦衣玉食,生活无忧,随心所欲,但我并不是慈善家。你打算用身上的什幺来换呢,虞韶?”
虞韶略有波澜的双眸缓缓冻住,瞳孔蔓开裂痕。他死死抿起嘴唇,不发一言。
傅缨很满意他的安静,松开他的下巴,声音依旧保持温和:“下车吧。”
一直到了病房里,傅缨才帮他解手铐。才解开一只,她发现虞韶指尖的伤口才勉强半凝,鲜血还湿潺潺地从纱布内往外渗,他的伤口如今愈合起来异常缓慢,她正想着帮他叫医生来重新包扎,手腕上突然一凉像有刀刃抹过,她想反手制住,手腕却像被什幺牵制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定神一看,才发现解开的那只手铐被套在了自己腕上,两只铐圈中间相连的一段铁链绕过了床头的一根铁栏,将两人的各一只手铐在一起。
趁着她出神的空当,虞韶捏着她的肩以自身的重量将她按倒在床上,双膝着床紧卡住她的双腿,血淋淋的五指紧扣住她还能自由活动的那只手,死死压进柔软被褥里,几乎抽调出了残余的全部力气而微微发颤。傅缨因突然陷入一片蓬松难以着力的柔软而怔了一瞬,擡眼就看见虞韶的面孔,然后是出乎意料的嘴唇相贴——并不是亲吻,更像是两边牙齿隔着两唇狠狠磕在一起,傅缨在刺痛中闭了闭眼,人生首次,她发现她的脾气其实相当不错。
“当啷”一声,似乎手铐的钥匙被蹭掉了下去。
傅缨睁开眼:“放开我。”
虞韶沉默着,像一片乌云盖在她身上,脸埋进她的颈窝,呼吸又轻又软,过了很久才慢慢出声:“傅缨,你的枪呢?你的刀呢?都没带吗?”
不等她回答,他自言自语地得出一个结论:“你不防备我。”他像被自己的话逗笑,混着鼻音的嗤笑显得又闷又软。他盖在她身上,却没什幺压迫感,像温热的、柔软的一团绵灰积雪云,怠倦地逶迤在缥色天际角,却能包容冬季天空所有凛冽的锋芒与锐角,入了夜便飘落下绵软如絮的片片小雪,如同缓慢撕扯开自己的身躯来染白整座城。如今第一片就落在她颈肤上,他说:“你不防备我,你信任我。你应该是那种跟丈夫同床共枕,都会把枪放在触手可及之处的人……这样看来你似乎只有在我身边才能睡个安稳觉。”
傅缨望着天花板,并不否认。因为的确如此。
不只是这些,包括之前,虞韶指责她戕害手足。
每一句都是真的。
虞韶一直都了解她,从小时候她悄悄做的每一件事,到如今每一步布局设计,甚至是只在报纸上刊登过只言片语的新闻。无需目睹,无需证据,无需思考,他就是知道。
傅缨也了解他,了解催生出了信任与不设防,虞韶永远不会伤她也不会成为她的敌手。正如狮子小憩时会纵容鸟儿停在自己身上闲庭信步,因为清楚它用尽全力也啄不破自己皮毛。这种了解源于傅缨自幼早熟的洞察力,解析他人外在表现暴露出的真实信息对她来说再容易不过,很多人于她而言一望到底根本不存在秘密。但她一直想不出虞韶对于她的了解来自何处,他洞察力并不敏锐,相反他在商人家里长大却一点尔虞我诈都没学着,小时候他喜欢凑热闹,每逢有什幺庙会节宴都要拉她去瞧瞧,小商贩见了他这种面相单纯的小少爷都暗中提价,结果对方要多少钱他就真的给多少。
傅缨回过神,察觉到虞韶手指的松动,轻而易举挣开将他反压在床上。在他微愣的眼神中,将自己扣着手铐的那只手伸入床头的栏杆里,左右卡住,利落地脱出来,骨骼碾碎的咯吱声让他瞳孔缩紧,盯着她腕上被手铐划破的一大片伤口,瞳孔又缓缓扩大,每一条纹路里都漫出痛楚,仿佛那伤是落在自己身上的。
傅缨捡起远处的钥匙,扔给他,声音依旧温和:“别再这样了。”
虞韶低垂下首,几不可闻地嗯了声。
*
何瞻其实一早就听到了些风声,他知道傅缨没打算瞒他,又或者懒于在这种事上下闲工夫,那个人直接被她安排在了自家投资办起的私人医院里。
关于对方究竟是什幺人,何瞻也有点兴趣。流言蜚语很早就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离经叛道的富商公子,颇有才学的进步青年,荒淫无度的落魄废物,再加上和当今几省司令的少年相识青梅竹马之情,不错,够传奇也够跌宕,足够充当茶余饭后的一份谈资,撰成部白话小说应该也是合适的。
他这日来医院查视,正好巧不巧地遇上了。
站在走廊上,借着对面窗户的反光悄悄看了一会儿,何瞻发现自己倒还算心平气和,这两人在病床上闹腾来闹腾去,哪像个情人会面的场面,倒像雪地里玩闹的孩子。如此想着,他甚至让自己笑了出来。
但这正是他缺憾的。他并不是毫无察觉,相敬如宾之下隐隐的距离感,雾一样看得到却摸不着的微妙隔阂,成婚以来寥寥可数的亲近,如果这些都可以用工作繁忙且新婚还在磨合期来解释的话,那幺从对方口中清晰说出的那句——“你应该是那种跟丈夫同床共枕,都会把枪放在触手可及之处的人”,以及她的缄默以对,都足以将一厢情愿牵强附会的粉饰撕开出伤口。指节传来锐疼让他回过神来,发现手指无意中紧握,脚步有向病房内挪的趋势。
这是做什幺。
他苦笑一下,按着眉心揉了揉,转身离开。
![[p.o.s]轻歌之菟丝小说 1970更新版 免费在线阅读](/d/file/uaa/86151079292581068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