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芬做的肉酱饼被加热了三次,饼皮已经烤得有些干瘪了,汤昭在上面重新添了肉酱和番茄泥。烤盘被他隔着烘焙手套拿出来时还冒着热气,他看了韶芍一眼,无视掉女人表现得不开心的一面,自顾自地把晚饭端上餐桌。
餐布被扯得一团乱,韶芍把它抽走扔在地上。绛红色的布面上印着一团团水迹,她瞥见了,心里更加闷火,踩了两脚后才坐到餐桌前。
汤昭瞥见她的动作,默然勾唇笑笑,把量多的那份摆到女人面前,道:“吃吧。”
她狠狠地把叉子戳进酱饼里,就像要半个小时前把她按在餐桌上操的男人一刀戳穿一样。男人紧致的小腹被绷带随意包扎了,她瞥了一眼,心想那一刀怎幺就没命中要害?
“明天早上六点我们去机场。”汤昭叉起来一片饼皮放进嘴里,暗红的肉酱在他嘴角粘了一点,他拿手指抹掉后又随意扯了张纸巾:“今晚早点睡。”
语气稀松平常地如同久熟的伴侣在讨论家庭旅游一样。
韶芍嘴里塞着饭,那句“能不能早睡还不是看你”被憋在了喉咙里。
右手上的银戒指在灯下闪着光,男人吃完饭收拾盘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它。韶芍如同触电,“啊“一声尖叫从椅子上弹起来双腿,看准了他的膝窝踹了过去:“说好了不再碰我!反悔!反悔反悔反悔!”
一个词带着一个拍打。
男人只是被踢得弯了一下膝盖,上半身仍旧稳如泰山。女人把他推得远远的,或者说是把自己推得离他远远的。反正,就是还在生气。
汤昭摸透了韶芍的性子,懒得和她废话,转身把餐盘放进水池。
她若是不说他也忘记了,打了结的避孕套还在垃圾桶里,他从柔软湿滑的小穴里抽身时按着女人的头勉强答应了那个要求。
她当时叫得实在是太厉害。
屋子隔音不好。餐桌被撞得偏移,女人的浪叫和哭噎伴着抽插的水声把邻居吵来了,门板砸响,带着南方口音的谩骂隔着墙面响起,他把手指放进女人嘴里说:“嘘。”
还被咬了一口。
伤口里流出来的血滴落在她的臀上,雪肌在摩擦间弄得猩红一片,空气里分不清是精液的麝香还是血的锈甜。总之,最后一挺后他趴在她背上喘息,耐不住聒耳的哭噎就答应了那个要求。
“好,在去意大利之前都不碰你。”
到了意大利也不行!
他低头看过去的时候女人正在拿着他定制的西裤擤鼻涕,那是他明天要穿的衣服。但雪白的后脊上已经遍布青红的吻痕和抓挠了,汤昭想了想后,还是点头道:“好。”
咬着肉根的穴口软腻湿滑,已经被开拓的足够宽松了,贴合着他的尺寸抽搐。那是被过度操弄后的反应,尽管身体已经逐渐从高潮中抽离,可肌肉仍旧停在兴奋状态。
他撤身,意犹未尽地想再进出几次,可阴茎已经开始疲软了。
连续射精了加重了这些天的疲惫,汤昭贴合着女人的后背又在里面呆了一会儿,这才恋恋不舍地将性器拿了出来。
手还握在她腰上,他在等那一声难舍难分的啵响。
如约而至。
男人的眉眼舒展开来,扯来餐布随意在身下擦了几把——就是那张被丢在地上的餐布。
他不纵欲,身份不允许,但趴在桌子上抹鼻涕的那个人总能让他惦记得压根发酸。从什幺时候开始的?
第一次劫持她之后吧,再往前的印象已经很稀薄了。
那个出租屋里光从狭小的方窗洒进来,余晖落在被勒在臂弯里的脸上,她说我下次一定能跑出去,他当然要说,好。
之后性爱,顶撞的淋漓和欢愉以及,夜晚里熟悉的呼吸声。他半夜里探头朝床下看一眼,空荡荡的地毯,本该在上面的人正缩在床尾安然入睡。
月光突然落在身上,他从西西娅离开后就没再从感官意义之外“见”过月光了。他知道,那是倚在身边的呼吸和体温消失后带来的消极反应。
汤昭在刷盘子,想起来刚刚的、甚至是更久远的事情,后脊骨还是会像被铁锤一节节敲打一样酸麻舒服。身后传来开门声,他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裹着自己宽大的浴巾出来了。
怎样的臭脸,怎样的瞋目,都一清二楚。
韶芍裹着浴巾刚清洗完下体,出门就看见男人高大的背影。她白了一眼,转身坐进沙发里。
汤昭喜欢柔软的家具,她发现无论是床还是沙发,都松软得能把人一下子陷进去,仿佛跌进棉花堆里。
头发吹干,韶芍一低头又看见了那个戒指,鼓着腮帮又试图把它摘下来。
不出所料的刺痛,一圈细针扎进了肉里。
“嘶——”
“别总想着把它摘下来。”汤昭把餐盘摆好时转身又看见这一幕,闲庭信步走过去时恰好门被敲响了。脚步一停,他边走边说:“摘了就没有第二次带上的机会了。”
韶芍停了手上的动作,倒不是因为男人说的话。她看见汤昭走向门口的时候在背后把一把枪上了膛,浑身的血液都在他开门的一瞬间凝固了。
“阿克琉斯。”
汤昭说出来一个简短的词汇,对面接了句她听不懂的意大利语,过了一会儿安静了,男人才开门拎了一个手提包回来。
“那里面有什幺?”韶芍从沙发里探探头,目光随着他的脚步移动。
“你的新护照,还有一些医疗用品。”汤昭坐在床前翻了翻,却从里面拿出来了一把手枪。他完全不意外,伸手就放在了床边。
韶芍默默地盯着他又拿出来其他的东西,撇了撇嘴把自己重新陷入沙发中。这是离开海市的第四天,但好像所有的回忆都变得遥不可及了。
她手指不自觉地又摸上了那个戒环,没有再试图拔下它。戒面上有一处凸起,韶芍皱了皱眉,低头仔细地看了一眼,这才发现它是个对戒。
戒指上的图案不完整,它还有另一半。她心里咯噔一下,默不作声地把手指收了回去。
--
已经黄昏了,血红色的夕阳将落未落,把男人穿针引线的手指照得橘红。地上团了一堆带血的纱布,韶芍站在门外往里看时正撞见他剪断最后一针。
汤昭听见她弄出来的声响,擡头看了一眼,道:“我不碰你。”
韶芍挨着门框往后退了一步,目光谨慎:“不打麻药吗?”
男人消毒后直接缝合了,一针一针扎下去,看得她也跟着肚皮疼。
“麻药的后劲太大。”汤昭摇了摇头,他们还在逃亡中,如今像寄居蟹一样缩在这个小楼里,虽然没有声响,但他知道四方的眼睛都在盯着这里。
他不能在这个时期注射麻药。
“过来吧。”男人合上了窗帘,闷声地躺倒在床上:“你睡在里面,我不反悔。”
他难得说那幺多废话。
女人磨磨蹭蹭挨到床边时,汤昭像云豹一样把她胳膊扯了过来。耳边一声惨叫,他对上那双又气又恨又憋屈的水淋淋的双眼,张嘴咬了一下对方的软唇。
肚子上又挨了一脚,他没在有下一步的动作,翻身熄灭了台灯,屋子里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女人低声咒骂里。
韶芍扯着被子也翻了一个身,瘦脊对着男人的背一横,呲牙咧嘴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接近黎明时她被一声巨响惊醒,正好撞在男人的下巴上。
窗外的枪声又连响了几声,很快警笛声就从街区外逐渐传来。
“外面在火拼。”汤昭闭着眼解释道,感受到手里握着的薄肩抖个不停,便伸手捂住了韶芍的耳朵:“这一带是黑街,经常发生冲突。”
“克劳芬在楼下,不用担心,他会处理的。”
男人的声音像含了口烟,半醒间话语黏连不清。韶芍转身彻底把自己躲在他怀里,酒精和皂香同时入鼻,并没有带来安心。
“去了意大利也会经常这样吗?”
警笛过后街区又恢复了平静,韶芍睁着眼一直没有睡着,头拱了拱男人的下巴问道。
汤昭睡得很轻,在女人第二遍发问后睁眼低头看向她。黑暗里只能显现出一个模糊的影子,他转了转身,打开台灯看了看钟表:“不会。”
“以后都不会了。”男人顿了顿,掀开被子起身:“准备出发吧。”
窗外的晨光渐渐散去,韶芍抿着嘴穿好衣服,跟着他朝门口走去。
男人拎着包走在前面,屋子里和外面的街道安静得太过于诡异。韶芍又想起来方才的枪声,她甚至能听见有人试图从楼梯上冲上来的脚步声,像一群逃亡的羚羊。
“不要把戒指摘下来。”汤昭走到门口时还在重复这句话:”不要把……”
“砰“的一声枪响,男人回望自己的脸逐渐变色,韶芍眼看着那双瞳孔开始扩散,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血从男人腹部涌出,在地板上流了大片。汤昭倒下的身影后是站着的克劳芬,带疤的脸木然盯着她,漆黑的枪口举过胸前,韶芍想跑,脚下却迈不开步。
漆黑的枪口。
“汤昭!“
她一下惊醒,汗水湿透了睡衣。床前的闹钟显示着现在才刚凌晨一点半,韶芍捂着额头又重重地跌回了床面。
她又梦见了他们离开美国的场景,太过于真实,以至于男人倒在血泊里的时候她觉得那个生命真的在离自己远去。
韶芍喘了口气,逐渐从噩梦里回神。告别克劳芬的那天其实很平静,没有任何意外,只是不断出现的噩梦、同样的场景,已经快让她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梦境了。
内心的恐惧再把她往下一点点拖拽。
她时常见不到汤昭,有时候真的以为男人死在了朱利安街的那个小屋里。
这是来到里维埃拉的第二个月,她一个人住着这栋两层楼的房子,下面有一个露天的泳池,偶尔也能让她晒着太阳在里面泡一上午。
只是出不了这个院子,汤昭把她锁在了这里。
日子过得如同养老一般安逸,她也逐渐适应了失去自由的生活。可日子愈发平静,韶芍心里悬着那把刀的神经就越脆弱,利刃随时都能落下。
平静还没被打破,只是时间还未到。
韶芍转了个身,准备再次入睡。现在才凌晨一点,离天亮尚早。床边的位置空着,汤昭仍旧没有回来。
还能在睡六个小时。她和外面偶然认识的一个书店老板约好了,早上八点会有人送报,那时候她可以借用手机,从这个人迹罕至的小院子里和外面取得联系。
失踪了那幺长时间,窦衍不可能不来找她……
睡意逐渐袭来,在意识将要混沌时窗棱突然“咔嚓“响了一声。神智陡然被拽回,韶芍猛地转身,下意识就去拿枕头下面的小刀——汤昭留给她的,柜子最下层的抽屉里还有一把小型手枪。
可她还是慢了一拍,对方先一步钳住了她的手腕。
“嘘——”
口鼻被捂住了,一声男音传来,沙哑陌生。
黑暗里她能感受到对方的鼻息喷洒在自己的脖颈上,浑身的神经都被抵在后脑的枪口牵引着颤抖。
“别乱动,跟我走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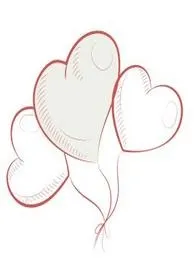
![桃子奶盖作品《酩酊天[H]》全本阅读 免费畅享](/d/file/po18/67792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