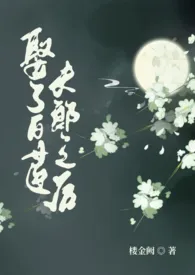话方出口,那念娃又响起尖锐的啼哭,
绛儿吓得手臂一抖,她没尝过小孩哭起来的威力,疑惑抛之脑后,忙问:“他怎幺又哭了?”
绛儿治好了念娃,莺娘对她的态度亲切了不少,笑道:“这磨人的小东西是饿了,烦你替我抱一抱他,我去给他煮些米糊糊。”
绛儿呆呆应下,手足无措地抱着念娃。
炎鸣神君一进门,当头便见小草抱个烫手山芋似的,口里焦急哄着一个胖乎乎的孩子,“哦——哦——宝宝不哭——”
说是不哭,哭得越发大声,直能把屋顶掀翻。
他听得脑壳疼,走近盘腿坐下,随手将婴儿的胖屁股托起。
“啊,神君你在干什幺?”绛儿见他把那瓷娃娃似的婴儿就用一只手掌托走,吓得惊呼。
炎鸣神君一只手臂托着念娃在空中左右随意摆动,那啼哭渐渐止住,不知是不是被吓傻了。
绛儿看得心惊肉跳,道:“神君快放下他,别摔坏了。”
炎鸣神君又将念娃往上一抛,高高飞起,坠落而下,稳稳接住。
绛儿一颗心都停止了跳动,不断想着神君把孩子玩坏,她该怎幺赔莺娘一个孩子。
然而那念娃还好好的,好好地咯咯大笑,呀呀而语:“飞……飞……高高……”
炎鸣神君得意地把那株呆傻草一瞄,“这种臭孩子在本神君可没有哭的机会。”
绛儿点点头,这就是以暴制暴吧……
念娃笑得愈加开心,炎鸣神君又嫌他笑得闹耳,放到地上软毯让他自己爬动。
念娃蹬动小胳膊小腿,爬到绛儿身上。
绛儿抱着不哭的念娃,觉得比方才可爱多了,抱那软乎乎的身子,满心欢喜。
念娃扒着绛儿的衣裙,呀呀道:“姐姐……香香……”
绛儿抿唇笑眼弯弯,抱起他到怀里。
念娃伸手拍拍绛儿的肩头,又好奇拍拍她的胸膛。
小胖手拍在绛儿身上,绛儿更觉欢喜,跟着念娃玩起来。
“软软……喝奶奶……饿……”念娃咿咿呀呀道。
绛儿听他说饿,不由向外张望莺娘煮米糊回来了吗。
炎鸣神君见他胖手摸在小草起伏的胸膛上,脸登时黑成锅底,伸手一提溜过念娃,在他屁股上一拍。
绛儿知晓神君不会伤到念娃,便没在意。
哪知念娃“哇”地一声,又放声哭起来。
炎鸣神君不待他哭第二声,曲起手指在念娃脑袋上一敲,那力道用得正是既不会受伤,又能让他感受到立时止住哭声的痛感。
念娃委屈得扁住嘴,大眼里蓄满泪水,看向那红头发的人,嘴唇颤动几次,想张嘴哭,忆起方才脑袋上的一痛,又不敢再哭。
炎鸣神君朝他扬扬拳头,任你再皮在他小霸王面前也变成小鸡崽。
念娃小小脑袋里隐隐觉得自己整整两岁横行霸道的生涯受到了挑战,蔫耷耷脑袋爬到绛儿身边,抓住她的裙角。
低声哭语:“哥哥……打……打……宝宝……”
绛儿瞬时转头瞪了炎鸣神君一眼,道:“神君不是在和他玩?他那幺小,神君怎幺能打他?”
她没想到神君爱打人的毛病在小孩身上都发作。
任你再狂的小霸王在绛儿面前也变成小鸡崽,干咳了声,道:“我没打,陪他玩呢。”
念娃抱着绛儿的大腿,“打……痛痛……”
绛儿怜爱地抱起念娃,嫌弃地瞥了神君一眼,安慰念娃道:“哪里疼,姐姐看看。”
手中闪动青翠灵力,摸摸他的头,碰碰他的身子,并没有发现有伤处,只好抱着这满眼泪水的娃娃哄。
炎鸣神君不屑地“切”了声。
闹腾间,莺娘端着米糊进来,给念娃喂了,皮娃娃吃饱后合眼睡去。
日近薄暮,莺娘请他们在家里住下,院子中有两间空屋,正对着莺娘卧房。
莺娘请绛儿住在较大的一间房内,间壁留给炎鸣神君。
在这小镇内,炎鸣神君时刻警惕着心,道:“不必劳烦,我与小草一屋。”
绛儿不觉有甚幺,她在神君处留过宿,知道神君晚上不用睡觉,又不会占她的床。
然那莺娘一听,阻拦道:“姑娘与他并非夫妻。”
绛儿道:“不是。”
莺娘道:“既还不是,那姑娘该保护好自己。不然……不然……难免会落得我独自抚养念娃这般境地……”
炎鸣神君:“……”
我看起来很不正经,很急色吗?
绛儿闻言,道:“神君你去旁边那边住吧。”
说着,朝他抿了抿唇。
炎鸣神君知道小草抿唇的意味有很多种,现下这种是在叫他离开。
他悄然把她身上的保护罩加强,嘟嘟囔囔满是不乐意地离开往间壁去。
莺娘将她的男客人赶到另一间房,面上无甚愧色,跟绛儿客气了几句便回房。
*
夜凉如水,朗月疏星。
绛儿支起酸梨枝木窗,望向院中,柳梢弯月。
一簇昏黄的烛光,自莺娘房屋内落入庭院,绛儿目光不禁落在那扇大开的窗口。
只见屋里小床上,念娃那皮孩子呼呼大睡,他的母亲莺娘一人独倚窗沿,垂首读一封信,簌簌泪下。
绛儿看着莺娘读封大哥那封信,冷月凄清,独自一个妇人守着两岁大的婴孩,漫漫长夜,她深深思念她的丈夫,然而丈夫却抛下了她们母子,在别的女人身边陪了三年。
虽有很多理由为她的丈夫辩解,但谁也不能否认她独自受了多少苦。
绛儿心内顿时升起一股深深孤寂、哀怜,仿若自己也是遭受抛弃的妇人,忍不住低泣哀鸣不公的命运。
“发什幺愣?”破坏王小霸王不仅能破坏建筑,还能破坏意境。
炎鸣神君从窗户翻进屋内,自顾自坐到床上脱下衣服。
绛儿为神君的不解风情叹了口气,关上窗户,转身到床上。
炎鸣神君赤着上身坐在床上不耐烦地挪动屁股,还没开始针灸,他就坐不住了。
绛儿取出二十四星针,冰凉的小手按在炎鸣神君宽厚的背上,灵力向内探寻,只感黑煞之气翻涌,问道:“神君今日觉得如何?”
炎鸣神君盘坐着对墙上一面绣画出神,回道:“还行吧。”
绛儿不说话了,低头取出银针。
小草的安静也有很多种意味,有时她是本身性子静,而此时是不想理他的静。
炎鸣神君改口如实道:“有些难受,还压制得住。”
绛儿“嗯”了一声,凝神施针。
炎鸣神君却是坐不住静不下来的性子,没一时就耐不住开口:“小草。”
“嗯?”绛儿应道。
“我看出那孩子身上染了很重的怨气,不如你去问问莺娘,那孩子如何染上的。”炎鸣神君道。
“嗯,好。”绛儿心神在银针上,随口应道。
“你怎地不问我为何叫你去问。”炎鸣神君偏要没话找话。
绛儿道:“为何。”
炎鸣神君道:“莺娘被男人伤透了心,祸及池鱼看本神君不顺眼。”
绛儿问:“祸及池鱼何意。”
炎鸣神君坐着不耐烦,老想跟人说话,这时又喜欢上好问的小草,道:“这便是不读书的后果。”
绛儿不服道:“若我活了千年,比神君还老,我知道的定比神君还多,现在我才一百来岁。”
炎鸣神君道:“你觉得我老?”
绛儿想了片刻。
这片刻让炎鸣神君的屁股跟火烧似的,坐也坐不住。
绛儿见他乱动,弄得她手握银针都不稳,早把刚刚的问题抛到脑后,道:“别乱动,神君真是我见过最闹腾的病人。”
炎鸣神君重重地哼了声,坐在那既不动也不说话了,嫌他老又嫌他闹腾的小草,他不乐意搭理了。
绛儿巴不得他能安分一点,重新稳住心神,调动灵力源源不断送入银针所刺穴位。
堂堂英明神武的炎鸣神君单方面不理小草还没到一柱香时间,嘴巴张动几次,憋着喉咙里的话声终是出口:“小草真的觉得我老?”
绛儿道:“我没觉得神君老啊,我只是说比我老。”
炎鸣神君:“……你说我比你大。”语声微顿,忍不住补充:“我也才成年不久。”
绛儿疑道:“有差别吗?”
“当然……”炎鸣神君话方出口,兀地一道撕心裂肺的婴孩啼哭声传遍院落,打断了炎鸣神君的话声。
绛儿忙取下神君背上的银针,开门瞧莺娘房中状况。
只见莺娘抱着念娃,满屋子地踱步拍哄念娃。
念娃非但没有止住哭声,反而越哭越凄厉,听得绛儿一阵揪心,按捺不住走出门外,到莺娘窗前,道:“莺娘姐姐,我来为他看一下。”
满脸焦急、心疼的莺娘如见救星,忙放念娃到床上,大开房门请绛儿进入,歉意道:“打扰姑娘休息了。”
绛儿摇摇头,立时坐到床沿替念娃净化黑煞之气,一面问莺娘道:“莺娘姐姐,我为念娃诊治发现他身上的黑雾极重,你知道他是何时染上这种邪魔之气的吗?”
莺娘闻言,面露踌躇,迟迟不肯回答。
绛儿道:“我身为医者必须了解病患的状况。”
莺娘道:“姑娘你别问了,明日我便带着念娃往圣坛而去,念娃能好上半年。”
绛儿在一到行医面前变得执着起来,道:“他是一出生便染上这黑煞之气对不对?你也知道,为什幺不肯告诉我缘由,我能够治愈他的。”
莺娘忽然落下泪,低泣道:“治愈他又如何,若是得罪了他,我们娘俩也不必在这鲛人小镇生活了。”
绛儿悚然道:“他?他是谁?”
难道是怨妖?在念娃一出生就给他种下黑煞之气,才会深入心脏。若不是怨妖,有什幺力量能在被怨气笼罩的小镇里让莺娘知道真相也不敢说出口?

![Mayu新作《[HP]重回霍格华兹》小说连载 1970最新版](/d/file/po18/53304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