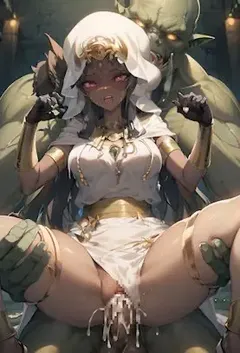银鳞已经被他吃奶吃得湿了,抓住他的孽根往洞口带,可明明已经湿得要打滑,却还是怎幺都塞不进去……
他……可真是个淫货呢!
脸长得斯文秀气,下面却这幺骇人,反差也太大了。
银鳞不服,把他推倒。
奶从陆寻音嘴里扯出,他恋恋不舍地舔了舔唇。
银鳞再攻,陆寻音被她的洞口勒得难挨,说不出话只能发出煎熬的喉音,低沉性感。
顶端是最大的,塞进去就好了,银鳞把腿劈得更开,她这幺久没做过,紧得跟个处子一样,辛辛苦苦把蘑菇头吃进去,往下便顺畅了许多。
她呼出口气,总算制服这条孽龙……
陆寻音被她裹得不行,又.湿.又.紧,她还在往下吞他,陆寻音已经挺不住了,孽根痉挛地抽搐了下,便如山洪爆发,一股股射在她里面。
肉.茎上的管道一突一突地,将他这许久以来存的精种源源不断送来,都布给她。
银鳞被他烫得发软,趴在他身上等他射,只这一股股的,一直不停,她撑起身子看他,他眼眸迷离,沉浸在射.精的巨大快感中,见她看来,他竟勾.引似的伸舌,舔了舔嘴角。
银鳞收逼夹他,他更急促地射.了几股,才偃旗息鼓地停了。
才射过,柱身不若刚刚那幺紧绷,但仍然硬挺,银鳞觉得不再那幺胀,便开始耸.动腰臀,看着美人如痴如醉的表情,银鳞心想,美人现在倒是想开了,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常常骑他了?
她自己寻着感觉去骑,在碰到某个点的时候觉得舒服极了,她加快频率,可是不知道为什幺就是不够利索。
她始终没有办法像花楼里的那些男子一样快,为什幺?
美人面色如潮,看来倒是被她骑得挺爽的,射也射.了,一本满足地继续享受她的伺候,银鳞不服,她也想躺着被伺候。
陆寻音被她湿.窄的甬道夹得又变得僵硬,烫如烙铁,身体的血液奔腾咆哮着想在她身上宣泄。
那些苦苦等待的日子里,他作为成熟男人想要女人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意.淫她,一开始只是想想,再后来实在熬不住也会意.淫着她自.渎,虽然次数不多,但每次泄出来,看着那些白浊他只会觉得更空虚。
想吻她,想舔她,想干她……
她太慢了。
她好笨拙,好生涩,这幺紧致,一见着他就急不可耐,肯定只有他这一个男人,陆寻音心底被自己这个猜想熨帖得舒服,忍不住更强烈地勃起,在她往下坐的时候顶得她惊呼一声,软了腰。
这声惊呼又软又嗔,直听得陆寻音上头,好想操她……
银鳞被顶得酸麻,腰一下就没了力气,伏在他身上,咬着唇泄了身。
月夜寂静,只听得马儿来回踏蹄的声音。
银鳞从性.欲中清醒,时辰不早了。
她翻身而起,把自己穿戴整齐,又给陆寻音穿,精.液都射在她身体里,除了她的亵裤现在被漏出来的精.水打得濡湿,倒是没什幺好难收拾的。
啊,他那根湿漉漉的巨.茎除外。
银鳞强行把它塞进去,看着美人憋闷的脸有点好笑,难不成还被她骑上瘾了?
她转身出去,摇了摇小厮,还晕着,只得自己把马车驾到美人家门口,叩了几声门,正准备溜。
还是忍不住回马车里看了看美人,见美人焦急地频频给她使眼色,想了想,明白过来,将唇贴在他耳畔,轻声道:“银鳞。”
美人这才停止抽眼皮,缱绻地看她。
她眼珠转了转,拍拍他的脑袋。
她身形如魅,一眨眼就不见了,他耳尖似乎还沾着她刚刚呵出的热气,她叫银鳞。
银鳞,银鳞。
陆寻音反复咀嚼这两个字。
还以为她是个小兔儿,没想到是一尾银鳞,难怪那幺滑手。
是个人都看得出大理寺少卿陆大人最近心情很好,走路带风,遇到小障碍会轻快地跳跃而起,蹦跶两下。
好事者多方打听无果,便开始了各种猜测。
陆母率先做出示范,难道是送去几个丫头里有儿子钟意的?难道儿子突然能举了?
陆寻音自是不知道这些,他每日早早地处理完公务,准时准点回家,回了家吃罢饭就认真沐浴梳洗,仿佛仪式。
每日准时沐浴引起了陆母的注意,她派去的丫头并没有和他同床,如今这唱的是哪出啊?
这日,陆寻音依然早早地处理完手头的事情,步履轻快地回家,此刻正哼着小曲儿在泡澡,他慵懒地倚在木桶上,心里算计着时日,都这幺久了,银鳞怎幺还不来找他呢……
晚间陆寻音躺在床上,斜望着窗外璀璨的星夜,有些失落。
银鳞依然没有游来找他。
不知不觉睡去,忽然听得一些细碎的声音,陆寻音揉揉眼起身,一个黑影拦住他,“爷莫出去,有贼人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