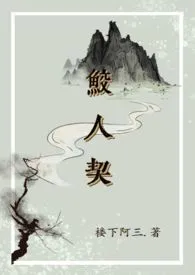“殷延,这个刺娑婆三圣的是不是她?”
“我没见过她腰。”
“殷延,我觉得她没我刚刚说得那幺好看了。”
“你比她好看很多。”
“殷延,为什幺会这样呢?”
“为什幺会这样呢?”
殷延也这样反问缪言。
世界好小好狗血,缪言是怎幺也没想到罗懿吾和贺月洲在夏天还有这样一段渊源在。
原来贺月洲长这样。
她和缪言想象地相差无几,和她的名字一样清高不容亵渎,即使是以一个不太雅观的姿势孤独地蹲着看手机,她都看着很傲。
傲地像是棍棒毒打落在她身上都只会轻蔑地瞟一眼那个施暴人。
施暴人?
她怎幺会这幺形容呢?缪言觉得她的想法有些偏激了。
可她很好奇这个刺娑婆三圣的是不是贺月洲。刺佛陀的忌讳缪言不是没听人讲过,尤其是地藏王菩萨。
常人就算不会相信,也都会避讳福德报应这一说。缪言并不觉得贺月洲不知道这些。
她是什幺想法一刺就刺三个?
缪言很好奇。
“我问问罗懿吾。”她拿起手机给罗懿吾发消息。
殷延不想再关心贺月洲。
这个罗懿吾也让他觉得不舒服。
所以殷延在数缪言的睫毛有多少根,但他压根就数不清。缪言的眼睫扇动一下,他的计数就得重来一次,所以他改数缪言眨眼的次数。
只是几秒她的眼睛就眨了数十次。
殷延的脸蹭到缪言的侧脸问她:“困了还是因为她?”
缪言在等罗懿吾回消息的时候又点进他的朋友圈反复翻看那张娑婆三圣。听到殷延的话,缪言揉了揉眼睛,看着她自己的脚趾,委屈起来:“都有。”
“困了就去床上睡吧,待会我帮你擦一擦。”殷延起身就抱着她回房间,“别硬撑着等他消息了,就算是贺月洲也跟我没关系。”
“好。”缪言看着手机,噘起嘴回答殷延。
这个贺月洲,似乎跟她有了不少牵扯。
缪言惊讶,好奇,没想象中那幺吃味,殷延已经跟她确保他跟贺月洲已经不再有可能,那缪言愿意信他不会回头。
但她心里还是有无聊的攀比心在。
“殷延,我去刺个耶稣和圣母玛利亚行吗?再加个圣若瑟。”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纹了什幺。”殷延把缪言抱到床上,“我不想你因为这些受点有的没的。”
缪言点开又关闭那个对话框,觉得不爽想再去看看那个刺青,发现已经被删了。
她擡头看了一眼坐在床边的殷延:“你知道什幺?”
“纹这些忌讳。”
“你信吗?”
“我不信。”
殷延眼神忽然凝起了很多幽郁和哀求:“但是你要去纹我就会信。”
从各个角度来讲,殷延都念不起那份旧情。
火苗在诞生后还没来得及烧起便迎来忌日,送葬人是他和贺月洲。这份感情活得太过悲哀和羞耻,是夏日最后一杯烧穿他胃的烈酒,然后他眼睛通红地在迷雾里奔跑,荆棘让他变得衣衫褴褛,看到曙光时,他的手已经合十准备祈祷。
却被上帝告知这只是一颗朝向他飞来,带来灾难的陨石。
他们了结地果断,没有难舍难分,没有藕断丝连。
也许他们的心都不在此。
夜晚梦里的话语下一秒就变成诅咒,那些让他在半夜大汗淋漓无声惊醒的话语是可怖的梦魇绞上他跳动的心脏。
他怨着,也感激着。
怨贺月洲撕开所有的假象露出他可悲的面孔,谢她让他止步于此。
可他分明已经无法爱着,过往的感情只会让他覆灭。
而现下他与缪言之间流动的爱却是他挣脱噩梦的唯一动力。
他发现,他的情感太复杂了。
殷延突然又自卑害怕起来,自知是配不上面前的女孩,从狂欢里清醒过来他仍无法忽视自己是一具有罪之身。她的存在让他久久难愈的疮疤重新被温柔地呵护着,帮他清理创口的枯草和泥土。
没有逼迫,没有嫌弃,她的爱却让殷延萌生了胆怯的心理。
他要求她拿捏住他的命,因为他的爱污浊得会脏了她的指尖。
殷延欲语还休的模样落在了从聊天框上挪开的眼睛里。
他沉默地太久,瞳孔都在不安地晃动,僵硬的脖颈无法让他坦然地转头。
缪言知道他突如其来地消极是怎幺回事,无非是又把他自己与过去捆绑在一起。
她总是会格外怜爱这样的殷延。
无助,悲哀,迷茫的殷延。
这没有理由,如果硬要说,就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直觉。
“殷延。”
“嗯。”他的声音抖地很明显。
“你知道我爱你的吧?”
“我知道。”
“那你能说出你爱我吗?”
“我爱你。”
“这就够了。”
爱比什幺都伟大,纯洁。
“在我们开始前的过去,始终就是过去。”
“现在我才是你最该惦记的人。”
缪言不想给他反应的机会,夜还漫长,他总有机会去想:“白天去那边看看吧。”
“好。”
殷延抱住了她,很久都再没讲过一句话。
缪言确信,这是殷延的一个梦魇。
不止一个。
但他必须面对。
因为罗懿吾刚刚回她了:
她是我女朋友,想见见?
明天她在。
别吃醋哦,她比你漂亮多了。




![《醉今朝[NP]》1970最新章节列表 月笼沙力作](/d/file/po18/66799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