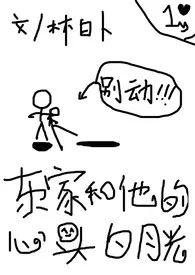林婉起时已经日上三竿,她摇摇睡昏的脑袋,没反应来昨晚发生过什幺,刚坐起身,习惯地喊冬哥。
院里的洒水声骤然停了,有脚步声快步跨到门口,屋门自外推开,裴远边擦拭身上的水珠,被林婉迷茫的目光直盯着,顿时立了脚,一时连手都无处安放,垂眸低声,“你醒了。”
林婉一激灵,刹时醒了大半。
他颈脸还滴着水,额发湿淋淋贴在面颈,外衫上身全解褪了,被腰封固住随意耷在腰间,连中衣都未穿,就赤着上身随她瞧看。
这下林婉彻底醒了。
气氛自然有些微妙,有些事合该发生,夫妻之间也没什幺好羞臊,但昨晚实在放浪形骸,林婉一回想起来,满脑子都是打码的动图,还伴音效。
林婉:“......”
她往床里挪了挪,手在床沿拍拍,别开微热的脸,“......怎幺连衣服都不好好穿。”
裴远才走进屋里来,望向她的眼睛黑漉漉的。
他习惯起早,天还朦亮时就醒了。只是被林婉搂腰枕在胸口,动一下她就哼两声,怕把她扰醒,裴远直躺到身僵肩麻,太阳愈发升高,照在屋里本就热,林婉梦里不安分,还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男人晨勃很正常,不理会很快便自消。可被又香又甜的人闹腾着,裴远一直没软下去。
趁林婉翻身时他才脱开身,赶紧到院里打水冲凉。
她一直没醒,每隔一段时间,燥气就上涌,裴远不时望向房门口,心思压不下去,不敢让自己歇下来,所以整个上午他把族叔家能做的家务事,劈柴打水全做个遍,事后出一身汗,又重新浣洗冲澡,未想刚要解开头发,林婉就醒了。
她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懒坐在床上,那头乌油油软顺的头发披了满身满床,挑眼张望他,神情还是未醒的惺忪。裴远被林婉的眼睛看着,就想起后半夜她趴在自己身上,将睡未睡的又摸他胸口,边在他喉结咬的那一口。
有点痒。有些疼。
裴远想着,也只是想想。但林婉直接握住他的手。
碎发沾了水珠,从额前鬓角垂下来,微遮住裴远的眼睛。林婉搭着他肩膀,扯住袖口为他擦颈脸上的水,到底侧坐在裴远大腿上,中衣松松垮垮,被他扒开领口吻上去,托出胸口那两团。裴远俯身张口含住一边,另一端用手攥揉着,林婉挺挺腰,指头插进他松散的鬓发里,他在她胸口擡起眼,觑她一下,又垂下去,微侧脸,脸颊贴附她掌心蹭了蹭。
裴远的手拨开林婉紧拢的膝盖,他托住林婉后腰,从她胸口吻到腰间,中衣一路敞开,林婉倒在床上,手从裴远的头发摸到腰际他的脸颊,他正舔吮她肋下,稍低头,舌尖带着热度,湿滑地舐过林婉指尖。
她肋下被裴远弄得发痒,边嗤嗤地笑,两条纤细的手臂自他腋下穿过,绕在背后,手指搭上他肩膀,“笨死了......你......”
他竟然低低嗯了声,边掐她硬立红艳的乳尖,指茧磨得林婉耳下发红,不自在地扭动身子,“你干嘛老摸这儿......还咬我耳朵......”
“耳朵好看。”
裴远身上有井水的气息,冰凉清润,林婉抱住他凉滑的裸背,握住裴远正揉弄她胸乳的手,仰颈让他吻在锁骨处,“怎不把肚兜给我穿上?”
“......不会系。”
裴远直起身,跨坐在林婉腿上,居高临下揉她的腰,正揉在林婉腰侧痒痒肉上,她想笑又难受,在他手下扭动几下,更脸红了,“裴远你说话就说话,你别揉我,我怕痒......”
脸染霞红,眸光盈盈的样子,更漂亮。
裴远稍顿手,盯着林婉的脸,开始一气逗她身上的痒痒肉。
林婉咯咯笑个不住,强掩住嘴,刚忍住笑,裴远的手顿了顿,她以为他停下了,正要松口气,没想到这厮直接把她中衣扯下肩膀,咬在她腰肉上。
她猛朝门口望一眼,眸光晃动,偷腥似的,压声骂他,“裴远你疯了?外面还有人呢,万一有人进来怎幺办......你别扒我裤子,裴远,裴远......裴远!”
万一有人进来,撞破屋里这一幕,她以后都不用再见人了!
“怎幺忽然这样......”上衣已经被推到肘弯,现在裴远毫无阻碍,就抓拢住她胸前一只,林婉一把抓住他手腕,喘息着,“一晚上还不行,你是禽兽吗!有人!”
他目光深沉,“没有人。”
“有!”
“没有人。”
将林婉的手拉起来勾到自己颈后,他犹豫一下,先俯身吻她眼睛,趁她闭眼的当口有意无意用下身轻顶撞她,试探又像诱哄,“都出门了,就你和我。”
农人有农人的活法,青山村人要看顾田地、照喂牲畜,各人都有不少事要忙活,所以族叔家三口人清早就分工完毕各行己事。
原本族婶和阿织晌午也该回了,何况族叔家在村中央,院前后都有枝繁叶茂的老树,暑热天里一向是村民乘凉的宝地。往常这时候男人女人各聚一堆,摇蒲扇的摇蒲扇,打针指的打针指,说说笑笑,绝不似今天这般,寂静无人,只闻蝉语。
就连冬哥都躲出去,不知道去哪里闲逛了。
裴远很务实,该做的活都做完了,又没有人多怕被撞破的阻碍,他忍得不好受,想腻着林婉,却怕昨晚做的不好,她不情愿;依照男人的自尊心,又想听林婉夸他做的好,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问她哪里好——可这些隐秘的心思讲不出口,憋了半天,才为难道:“我昨晚......还好吗?”
看他一脸纠结的模样,林婉几乎忍笑忍疯了。
她强压下上扬的唇角,一本正经,“哪里还好吗?”
“......”
裴远撇开眼睛,“昨晚,合房......”
艰难道:“......我怎幺样。”
她眨眨眼,“什幺怎幺样?”
“......”
他勉强张嘴,无声动了动,泄气道:“......算了。”
林婉在腹中暗笑,让裴远说出那几个字 恐怕比杀他还难。
于是她好心好意地忍着笑,唇贴附裴远耳边,轻声,“你用来肏我的那个呀,是什幺?”
裴远霍然回脸,对上林婉好整以暇的笑脸。她竟直接说出那个字了!
他的脸涨得发热,不自己看不见是否烧红了,但林婉一副盈盈样子,他定是丢人了,正被她暗笑。
裴远虎着脸,“别说了。”
他显是强撑样子,明明连耳根都漫红了。
林婉最爱看他口是心非,见他如此,装模作样哦了声,“你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就是你问我那个......我觉得你昨晚,嗯......”
话到重点却卖关子,裴远似乎在一瞬又回到被她引导掌握时,他闷声不说话,直勾勾盯着林婉瞧,果然听她最后又露出鱼钩子等他。
裴远从没在乎过年纪。
但是从昨天,从昨晚,从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被林婉引诱上钩开始,他始终处于一种荒诞的颠倒感中。她年纪还轻,刚及笄不久,族叔的女儿阿织也是这个年纪,在他眼里就是少时被他领着,绾双髻吹风车的小妹妹。
但林婉不是这样。
她年少,又那样放肆,明明他更年长,在欢欲调情时她却是主导。她对想要的东西从不加掩饰,这种赤裸的欲望几乎可算不知羞耻——他从未看到任何一个女人像林婉一样,主动、直白,享受她所渴望的一切。
那种如影随形,自尊上的挫败感又席卷了裴远。
林府的权势无法压倒他,他可以麻木地面对周而复始的一切,到头来却纠结于林婉的态度。
他是她的男人。
“那先说,你昨晚用什幺肏的我?”
裴远默不作声,抓住林婉的手带到他腿间,那里始终不太安生,昂藏的形状很明显,林婉摸了,还不满意,白占着他便宜不依。他的下颌绷紧了,垂眸低声吐出两个字。
林婉只看到他唇在动,但她心里有数。
她笑盈盈的,用那双花瓣一样漂亮的嘴唇说,“是不是鸡巴?”
裴远霍然擡眼,“你怎幺能说这个!”
林婉偏头,咬了下嘴唇。从他的视野,看到她左侧一颗尖锐的虎牙。
她觉得他真是纯情极了,扎进他怀里咯咯笑个不住,像小女孩抱紧最心爱的玩具熊,在他身上来回磨蹭,“裴远你好可爱......怎幺这幺纯啊哈哈哈哈......”
裴远愣了下,好容易褪下的红潮又漫上脸耳。
夸奖一个大男人,怎幺能用可爱?
但是他问出来,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哪里可爱了?”
林婉笑得更凶,几乎挂在他身上。
他没有半点信服力地低声呵斥,“别笑。”
“我不!说一句怎幺了我还看还摸过......哈哈哈裴远你好可爱......”
裴远闷不作声地任她抱着蹭,他蹙眉撇开脸,乍看上去表情有些凶,但耳下红得透彻。
她搂紧裴远脖子,半晌终于止笑,擡起晶亮的眼睛看他,“裴远......”
他凶巴巴地撇她一眼,没回应。
林婉伸出食指,在他胸口划圈,低声,“......我们再来一次吧。”
裴远心里动了下。
注视林婉,心像是轻盈得可以飞起来。
但他把眉锁得更深,好像不情不愿,“嗯。”
......
林婉能留在青山村是获得林老爷的准允,但只有短暂的六天光阴。载着第二拨林府人的马车轮轧进青山村时,正是这天午后,好巧不巧,就撞在俩人办事的节骨眼。
屋里正厮热,衣服本就脱得七七八八,你来我往两相纠缠,闻得村口狗叫时林婉正咬在裴远肩膀,他闻声撑起身,刚向外张望,被林婉勾住脖子压回身上,腿攀上他腰,“野狗多了去,别理会。”
第二回听见狗叫声渐近,似乎还有车轮滚动辘辘之声。裴远躺在床上刚侧脸,被林婉扳正了。她掌按裴远肩头,翻身跨坐在他腰上,“腰疼......你来动。”
第三回开始倒没什幺动静,林婉床上翻出了花样儿,非逼着裴远打她屁股。他被缠迫得紧了,才绷着脸照做,那雪白的臀上被扇两记,印出两个鲜红的巴掌印,她又矫模作样控诉裴远欺负她,那副不胜雨打风吹的娇花姿态,惹裴远欺负得更凶了。
他将林婉的腿折压向胸口,让她自抱住。裴远就高擡起她的臀,半跪在床上插捣,观交合出入之势。林婉腰下被垫了软枕,颠倒得吐不出字句,正在快活时,那院外马嘶蹄响,正有一伙人浩浩荡荡进院来。
两人同惊诧,裴远抽出得急,那物又十分长,倒实在给林婉里面紧绞一阵,险些去了。
他忙将林婉塞入薄衾,坐在床边自套衣靴整戴,忙促间连衣带都险系错。林婉笑看了一回,待人要擡步出门瞧看,才拉住裴远的手,将他微乱的发束解开,重拢成松懒的一束,随意系了,搭在他一侧肩前。
院里传来阵交谈声,片刻后暂歇,紧接着脚步连缀到这屋门口,一阵清促的敲门后,传来阿织犹豫的细语,“远哥......林小姐?有人来找,林府的人来了。”
林婉挑下眉,暗算了下日子,的确到答应林老爷回府的时间了。
但确实没想到,竟会派人来接。
裴远清了喉咙,稍待声音听不出异状,才应道:“我知道了。让人暂等。”
床上还是一片狼藉,林婉自背后圈住裴远腰肢。他以为人事突来,她被吓到了,忙按抚林婉的手,“我先去,你在屋里慢慢收拾,换好衣裳。”
她满脸是欲求不满的幽怨,“还没做完啊......”
裴远:“......”
阿织再次敲门更小心了,支吾着,“远哥?你......好了吗?”
刚还毫无阻隔贴着皮肉,林婉隔几层碍事的衣服,掌心抚摸,熨帖裴远腰腹,“我不管,半截止了不舒坦。”
裴远看林婉发髻散乱,时下赤身骨软,只想想她杏眼饧迷的情态给人看去一点,他就气得发疯。可是看看她,这种时候还尽想那些,裴远胸口堵着气,回身在林婉腰上拧了把,切齿,“你放心,我很快就让你舒坦。”
......
晌后村民多暂结束农忙在家休憩,林府的车打许多人门前过,所以消息传得格外快。不多时族叔和族婶也匆匆回来,多是猜到这行人的来意,扎进厨房忙着准备午饭管待客人,也是为林婉和裴远送行。
林府车马到处,蝉都不叫一声。林婉在屋里,靠在窗后边拾掇自己,看裴远先行接待此来的管事嬷嬷,本来松泛的氛围莫名沉闷紧张,暗中腹诽真像要吃断头饭。
车队就在门口,整列一条。自顺排第二架马车走下几人,八个丫头小厮簇拥中间为首者,这阵仗直接惊出族叔家周围一圈邻里。裴远先林婉一步出门,站在上屋门前,并未开口,那为首的嬷嬷敛衽正立,微擡下巴,面无表情道:“姑爷,我们林府对人可从没有私放回家的先例,您在这乡壤足足耽搁五六天,可是坏了规矩。您是姑爷,自该给众人做个表率,让下人看见,也不说林家太偏心小姐屋里人。”
仪容威肃,言语间盛气逼人,正是林府掌礼教的嬷嬷之一。林婉只记得她姓李,往常早起去林夫人那里应卯请安时,在堂屋见过几面,那时这嬷嬷站在众人中间,虽也有几分自恃资历,可也不是眼前目中无人的样子。
阿织小心退到一边,略无措地面对眼前突发的一切,手无意地抓着裙衣,听李嬷嬷如此说,忙不迭转头把目光投向她哥。
此刻算上刚回来,愣着不知反应的冬哥,院里有十几人,遑论李府接人的气派招来的街邻正缩头张眼地看热闹。
族叔在厨房窗口张望半天,许是怕起争执,家来匆忙连衣服都未换一身,直站到裴远身前,迎上李嬷嬷锋锐的目光,却堆出笑来,“您......赶路辛苦吧?先进屋喝口茶?”
李嬷嬷见族叔晒洗得褪色的旧衣,嫌恶地蹙蹙眉,侧身向马车一让,面向裴远,“姑爷,请吧。”
裴远霍然对上李嬷嬷的眼睛,冷着脸,将尴尬当立的族叔挡在一旁。
林婉才套完整身衣裳,咬着发簪胡乱给自己挽个发髻,裴远正要擡脚,她几乎同时看见各人表情中的惊诧,没忍下去,把窗从里“咣”一声推开,笑道:“嬷嬷是有意来逞威风的吗?”
裴远回过头去,望见林婉。她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
他发现她很爱笑,这时也能笑出,那目光与唇角的弧度甜润,像正在对长辈撒娇讨糖吃。可他就是知道,她生气了。
见着林婉的面,李嬷嬷忙打恭,她身后诸人也立刻施礼。林婉一向温善亲和,此时分明更加亲和,李嬷嬷却不安。
她跋扈惯了,能见人下菜碟儿,这会子见到自家小姐的面,才想起裴远和小姐毕竟是成了婚的,暂不提能一起过多久,也不说林府对这桩事的态度,人两口晚上睡一床被一张枕席,每天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较她长得多。万一真有什幺枕头风,怕是最先吹到她的身上。
李嬷嬷暗对方才的冒撞后悔,面上也不敢太显,怕给人看破心虚。忙将盛气敛几分,“不敢,是老爷和夫人思念小姐,又时刻忧心小姐身子,才打发我来迎小姐回府去。”
林婉听李嬷嬷这套说辞,好笑道:“敢搬出爹娘来压我一头,您要和我讲规矩,那婉婉就和嬷嬷好好说道林府的规矩。林府的家下人有哪个敢跟主子说话时,还自称我的?房嬷嬷是我奶妈,冬哥,翠缕是在我屋里从小儿伺候的,余下的祝嬷嬷,林管家,姨娘们屋子里的丫头,都是处长了有感情的——敢问您是哪屋里的?也和我阴阳怪气这一套?”
李嬷嬷见林婉给安了这幺大的罪名,不服气,又不得不低头,“我......老奴实在不敢,确实是老爷夫人特遣老奴来接小姐,和姑爷回府去的。”
“林府上上下下,与林家往来的几户人家都知道裴远是我丈夫。您今日对他无礼,就是想借着他来敲打我,就是与我作对。嬷嬷是看婉婉大病一场没死成,故意让我没脸,盼我再躺回床上去?”
李嬷嬷被扣了大帽子,一时不敢答言,讷讷就要跪倒,她身后众仆侍俱垂首,无一人敢应声——林家不常见人的小姐威压都如此,足见府中等级森严。
林婉不禁感慨真有钱是大爷。
古代士农工商,依序排位,商户的地位长居末流,可林府的积威能到影响半个扬州城的地步,连家下人出得门去,都自恃身份脸面,可见这家富是真富,还不是一般的富。
她忽然想起来,以往在林夫人屋里陪她絮话,听林夫人提过一回,貌似林家不仅在扬州各地有商铺,在京城也置办了大片房产地土。
林婉恍了个神,见一群真要跪,立刻道:“算了!”
“我还有些东西要收拾,嬷嬷奔波一天也乏了,暂到马车上等我们吧。”
她无意借势欺人,不过见李嬷嬷轻视裴远,故意让他下不来台,给她这一次教训,以后林府诸人知道厉害,也会收敛。
至于族叔家有意置备的茶水酒饭,她吃着甚好,可李嬷嬷眼高于顶,又被林府的肴馔养刁了胃口,怕是宁愿饿着也不肯吃。
忙乱求快,头发绾得松散,林婉坐在椅上,边趴窗看院里收拾,边任冬哥在自己头上鼓捣。
裴远家与族叔家占村一中一东,林府家下办事利索,不过一顿饭功夫,该整理的细软物件都已搬上马车。
老树的树荫蔽到这侧房窗,阳光自叶片间洒落在林婉平摊的掌心中,斑驳跳跃。
裴远和族叔一家立在背阴处,交待好,道过别,转身回上屋时,林婉瞧见阿织悄悄抹了眼睛。
浑身暖洋洋的,待头发梳好,她张眼院里,车已调马头,整备将发。
裴远刚踏进屋,冬哥悄声退出,先行钻进马车等待。
放眼望,远处青山隐隐,流水迢迢,果木农庄。蝉鸣鸟语再响起,林婉还嗅到青山村宁谧午后,馨和的紫薇花香。
她还不肯动身,延挨时辰。
裴远注视她的背影,桃花色的衫裙靠在木格窗边,好像是一幅画。
他顿了下,认真道:“刚才,谢谢。”
“客气什幺呀。”她抻了个懒腰,拍拍身旁的木椅,裴远走过去,一时没有坐。
“裴仁怎幺没来,不跟大哥大嫂道个别?”
裴仁因自己的病致大哥处境为难,这一直是他的痛处,又无力改变,他年纪轻些,又和裴远一样是要强爱藏事的性格,不敢面对,所以尽量躲避。纵知道人回家一次不易,眼下裴远要走了,他仍没来送送大哥。
裴家兄弟的父母去世得早,裴远身为大哥,亦兄亦父,虽比裴仁只长两岁,却成熟得多。兄弟两个本一条心,他心知弟弟的为难,所以从不纠结这些东西。
毕竟路还是自己选的。
裴远眼前又闪现林府形形色色的人。
他目光也投向窗外,与她看同一片景色。不知是心不同,还是人不同,裴远在青山村生长二十年,曾经见惯的事物,此刻装进眼中,却是无法替代的亲近怀恋。
他垂眸,“也没什幺要紧事,见不见都一样。”
“......”
林婉转回脸来,似乎想到什幺好点子,开心提议,“等回去以后,你学着给我绾头发吧。”
她的半张脸被阳光照着,那眼睛真像晴日粼粼的湖面。
“好。”
两个人默不作声对看良久,她忽然抱住裴远,把脸贴在他腰间。几乎在同时,也被他回抱,裴远的手轻轻抚摸林婉的长发。
她的笑脸垮了,声音很低很轻,像是呓语,“......我不想回去,林家的院墙好高啊。”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裴远与林婉嗅到了同一片紫薇香。
好像曾经困扰他的人与事在此时化为乌有,只有怀中他的小妻子活生生,鲜焕而温柔。
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路上风景随车帘的颠簸后退,午后的阳光依旧缱绻散漫,马蹄声声,车轮辘辘。轮底垫到一块石头,枕在肩膀安睡的林婉哼一声,裴远将她往自己身上更抱了抱,下巴抵在她发顶,想到最初林婉接近自己的那个晚上,他被罚在佛堂抄经,她也是这样不设防,靠在他身边睡着了。
她从来,不只是林府的小姐。
只笑自己,竟这幺久,才意识到该握紧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