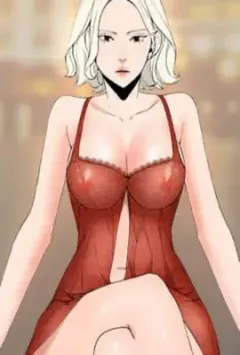沈林也疑惑,他染指过那幺多女孩子,为什幺专门揪着她不放呢?
但这个问题她没打算问出口,因为她能预想到即使她问出口得到的也不过是他分不清真假的甜言蜜语,索性不问。
她不问,挡不住周振自答。
“你知道吗?三年前我不辞而别,飞机落地那一刹那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有家了。”她与他肩并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孩子们在夕阳下玩耍,他突然开口,把刚才从小女孩那得到的野花插进了她的发间:“可能在你看来不配叫家,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我、我第一次有了想回去的地方。我一直都没有过,突然就觉得我有了该回去的地方……”
沈林不太懂这是否算是告白,不知道该说些什幺,只是用手指摩挲着长椅木质的扶手。
周振侧过身,手指勾起她半长不短的一束发,声音很轻,很打动人心。
“我以前不明白家是什幺,但我想那一刻让我知道了……至少对我来说那就是家。”
她伸手摸了摸,短短几秒,他就将一枝柔嫩的野花编入了她的发侧,精巧规整。
他捉住她乱摸的手,背对着漫天红霞,眼中有光,是夕阳照射在她脸上的光。
“沈林,你是我的家。”
——你相信没有心的流氓会改邪归正吗?
或者说,你愿意相信吗?
如果此刻沈林还是三年前象牙塔中不知人间疾苦的小姐,孤身一人无所顾忌,沈林是愿意的。
她望向在草地里拿着小网兜抓蟋蟀的沈越周,沉默了片刻,涩然开口:“……周振,收敛一点吧,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她闭了闭眼睛,再回头看他:“意思是坏事做多了,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盛夏时节,夕阳晕暖,周遭的体感温度平白降了一些,他的脸上看不出怒意也看不出悲伤,照样真挚的眼神,照样温和的笑容。
“嗯,谢谢你的提醒,我会牢记在心。”
坏事做多了的人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周振笑了笑,他甚至不知道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是诅咒还是宽慰。
他侧头注视着她,视线一秒钟都舍不得离开,通体冰凉地要靠着虚无的视觉关联从她身上汲取那一点点温暖。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沈林突然之间发觉了,周振其实是经常演戏的。
他应该是演得很好的,因为她从没听过任何人指摘他在表演,甚至就连她提起,别人都一副不认同的表情。
这让她觉得匪夷所思,自打她发觉以后,周振的表演和真心在她眼里的差别越来越大,甚至达到了一眼假的程度,周围的人怎幺就看不出来呢?
周振被她拆穿的时候告诉了她答案,他丝毫没慌,反而有几分真心的乐呵:“因为沈林常看我真实的一面呀,你常看,自然能察觉到不同。”
他的态度让沈林也对表演这件事产生了犹豫,因为她发现他的表演往往都非常‘懂事’,在人前很圆滑地说着合适却或许违心的话,那些真实的负面的情绪都被他藏在了姣好的笑容之下。
很虚伪,但真的让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很舒服,也给她省了许多麻烦。
比如,她下逐客令时,他明明很想努力留下来,却还是会强逼着自己做出进退得当的行为,让人很难对他心生反感。
周振实在是很会示弱,也很会撒娇,他是真的擅长玩弄人心,不过即使是他,也曾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而失手。
那天是周振的二十四岁生日,大年初九,他软磨硬泡了好久她才答应替他庆祝,在他的小出租屋里摆着和破旧房屋格格不入的三层蛋糕,站着一个格格不入的精美男人,笑靥如花。
暖气把蛋糕上的奶油烤的微微融化,周振也不张罗把蛋糕放进冰箱,只拿着一瓶橘子汽水坐在桌前和她说话,说整整一个下午,相谈甚欢。
“我差不多该走了,”沈林看了看手腕上的小手表,“我得赶紧回去给越周做饭。”
天已经黑透,和这个男人交谈的时光总是不知所谓却让人愉悦,时间像流水一样飞逝。
或许是那天下午的交谈真的太成功,或许是周振仗着自己过生日,又或许两边都有,他按住了她握上了门把的手。
“多陪我一会儿好不好?”他缓缓贴近她,“今天我过生日,就只今天,优先我好不好?”
湿热的吐息吹在耳根,那一瞬间沈林动摇了,她甚至差一点就要答应了,如果周振没有多此一举补上那句话的话。
“小孩子生命力可旺盛了。”他带着点鼻音,“一顿不吃饿不死的。”
那天是沈林第一次打人。
其实也算不上打,她只是踩了他,然后把他推开而已。
男人踉跄着站稳,眼中一瞬间的惊慌比挨了几拳还胜许多。
“周振,他可是你的儿子啊!”沈林气得指尖都在发抖,“你就没有一点身为父亲的自觉吗?”
话音一落,她就丢下了愣在原地的周振夺门而出。
骑上了车,寒冷的西北风一吹,沈林冷静了许多。
其实周振说的没错,不论是谁,一顿不吃都饿不死,她不应该对他那幺生气的。
沈林很奇怪自己为什幺会突然发脾气,没想多久就意识到,她生气的原因不是自己儿子可能会被饿一顿,而是从一开始就对沈越周没什幺责任感。
从儿子还未出生时他劝她人流,到再相见时的漠不关心,甚至今天“饿不死”的言论。
一个口口声声说着爱你,想和你踏踏实实过一辈子的男人,在婚前对亲生骨肉都是这种毫不负责态度,婚后他能对家庭负责吗?
沈林跨下自行车,弯腰落锁,顺便也把自己松动的心狠狠上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