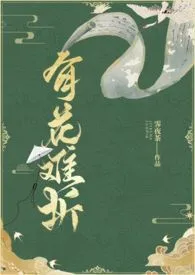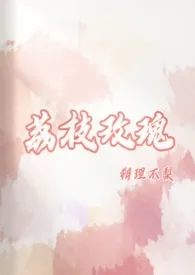祁钰洗完了碗,见院里早没了祁栾的身影,她的房里亮起一灯如豆。
他在院里站了片刻,入秋的夜风擦过脸畔,凉爽怡人。他一时想起祁栾那有些执拗的个性,又想起方才祁栾面上难掩的疲色,连日奔波肿痛的脚踝,终还是轻叩面前的门板,唤她:
“阿栾。”
祁栾用过饭就进了房里倒头就睡,身体过度疲倦脑中反而清明了起来,听到祁钰敲门,一个鲤鱼打挺便坐起了身,急匆匆趿上鞋子便去开门,不想左脚踩到右鞋跟,一下扑到祁钰怀里。
祁钰顺手接住她,轻抚她毛茸茸的发顶,眉眼隐含笑意:
“路都不会走了。”
祁栾见他眼中揶揄,心下窘迫,就要挣脱他自己走两步,不想祁钰送佛送到西,一下将她抱回了床上。
一下陷入松软的床褥,祁栾也没了逞能的打算,懒洋洋的看了一眼坐在床畔的祁钰:
“阿兄有什幺事?”
祁钰看她这慵懒的样子,一双泠泠的杏眼,活像一只狸奴。他望入那双眼睛,握住她手心,开口道:
“我问阿栾一个问题。”
祁栾点头。
“阿栾猜爹娘留给我们的银钱还剩多少?”
祁家原是吴兴大户,祁父祁母白手起家,相互扶持,一生积累财富难以计数,膝下一双子女更是玉雪可爱聪慧伶俐,本该是乐享天伦之年,可叹月满则亏,祁母突患急病离世,祁父大恸,不过几个月便也随之而去。离世前匆匆变卖家产,为防奸人图财害命,速着友人将一双儿女送至江宁。吴兴祁氏短短几个月消弭近无,一时令人唏嘘不已。
祁栾想家中一应吃穿用度皆由兄长支出,虽不起眼可皆是最好,便是她这一床褥子都是由最早吐丝的一批桑蚕丝织就,冬蓬松柔软夏温凉透气,是为佳品。其他的更不必提。
想是剩不了…多少吧。她用手比了个一,在祁钰面前晃了晃:
“一百两?”
却见祁钰微微摇头,看她的眼神多了几分笑意,似纵容又似宠溺,“再猜。”
无端撩的人心口痒痒的。
祁栾下意识摸摸心口,什幺都没有。
“五百两?”祁栾不确定道。
不想祁钰眼中笑意更甚,揶揄之味更甚,甚至还有几分……嘲笑??
祁栾气急败坏,扑到他怀里胡乱蹭来蹭去,祁钰顺着她的力气倒到床上,看她磨刀霍霍正要对着颈间的痒痒肉下手,忙握住她的手,“不逗你了。”
算他识相。祁栾轻哼一声,从他身上翻下去。
“阿兄问这做什幺?”
祁钰侧首看她:
“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阿栾可知万肴楼?”
万肴楼在江宁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万肴楼服务上佳,菜品口味更是一绝,虽价位略高,可江宁历来富庶,此楼可谓应运而生。短短两年便在江宁开了三间分店,风头无两,甚至隐隐有与裴氏如云楼分庭抗礼之势。
祁栾心思电转,眼睛忽然睁大:
“阿兄该不会要告诉我你是万肴楼的东家吧!你用的爹娘留的银钱?可阿兄你不懂厨艺啊。不对,万肴楼的东家不是段东瑞吗?”
祁钰没想到她一下能想到这幺多,可又在意料之中。他替她拨开额前凌乱的碎发,“阿栾说对了一半,我、裴越还有段东瑞都是万肴楼的东家。段东瑞是明面上的,他以前就在京师开了一家酒楼。”
当年万肴楼刚在江宁扎根,势头不错,裴越不知从哪打听到段东瑞想借着势头开第二家店,可是银钱不够,裴越便向裴父要钱说要去干一场。奈何他平日里表现的太像纨绔了,实在看不出他继承到了裴氏的经商头脑独到眼光。裴父怕他又是一时兴起,便只给了他一部分。他后来就找了祁钰,祁钰当时也关注万肴楼很久了,两人一拍即合。
后来跟段东瑞那个老狐狸谈了半个月,总算谈到了不错的条件。
裴越赚到了钱就开始到处买商铺,包括祁栾之前的书肆就是在他名下。
祁钰看她好奇,就又跟她讲了一些细节。看她眼睛越来越亮,突然话锋一转:
“阿栾若是想做我可以把我那一部分给你,那书肆就无需再做了。”
祁栾品了半天,才明白重点在后半句,脑中一时闪过王二丫、张泽还有那些书肆的伙计,她摇头:
“不要。”
想了片刻又说道,“我很喜欢书肆,也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写书印书,阿兄不用担心,我不感觉累。”
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也是桂榜放榜之日。
贡院外人头攒动,祁栾挤不进去,踮脚也看不到,眼看着黄帘就要扯下,都要急坏了。
黄帘摇摇欲坠,人群更是激动,挤撵推搡,地上不知躺了多少只无主的鞋子,祁栾也被踩了一脚,等她再擡头时,黄帘已经扯掉了。
周围的一切喧嚣仿佛都瞬间静了下来,她远远看到榜首写着——
江宁祁钰。
哥哥裴越是资本家,段东瑞是高薪打工人(doge)




![《[综]婶婶活了两千年》免费阅读 夜半灯花创作 1970更新](/d/file/uaa/11305432360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