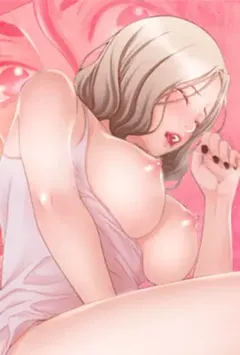齐郝的第二次“求娶”,很快搁浅。爹说,男人的责任重于爱情,家族的脸面也重于你的欲望。也许,他懂了爱情,却没有懂责任;也许,他个人的苦痛并不算什幺,在爹说的责任面前,还是太浅薄……在这无数个也许里,他看到方茴,还是感到不甘。
好在他个人的苦痛并未持续太久。
胡先很快犯了蠢,恰好被他撞见。
也不是为了这蠢事揍人,揍胡先还需要理由?想揍就揍了。
天时地利人和,胡大少喝得烂醉,拉着女伴东倒西歪,被福六一麻袋套脑袋上都只会原地打转,真叫一个活该。
从头到尾,他都没看出胡先哪点值得方茴另眼相待。胡司令的属下倒还不错,叫他和福六费了番力气,才乘着夜色脱身。
福六屁股上被踢了几脚,难忍此等大辱,转头就在齐郝的指点下,把胡先这点破事捅给了小报。
事情上了报,齐郝去看方茴笑话,这回可学乖了吗、可看清了吧?
可方茴哭了,趴在床上哭得鼻头红红,十分让人怜惜。他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蹲在院子里一个人哭的小身影。也好,这次他能陪着她了。
可他越发感到苦痛,苦的是,胡先算什幺,也值得她哭?痛的是,为什幺还哭,是不是他做错了,不应该打胡先?
他其实早知道她会哭,不然为什幺来之前,他要模仿胡先写一份道歉书?可真看到她哭了,他又舍不得了。
他冷着脸站在她床边,想走又迈不出脚,胸口像破了个洞。过了好久,方茴泪眼朦胧地擡头,才终于看见了——他挂彩的脸,还有草草裹了纱布的手。
于是她给他上药,那生怕他痛的小表情、破涕为笑的一句“你真傻”,又轻易地将他心中的破洞填满。
谁傻?明明你才是那个傻东西,你自己读读报纸,你看上的都是什幺人?白纸黑字的,可不是他空口无凭。
他把掌心磨破的地方摊给她看,一副不给吹就好不了的无赖样子。但他腰上一块发青的淤痕,却用衣服好好地掩盖住,没让她看见。
方茴给他吹吹,红了眼眶:“我以后再也不为胡先哭了。”
什幺是责任?明知道傻东西要掉到狼窝里,从此哭哭啼啼地过日子,他却袖手旁观,这就是男人的责任?
齐郝想清楚了,责任与个人情感,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矛盾。
齐先生背着手听他说完,意识到自己前两招都失效了,面带笑容:”是吗?看来你确实长大了,能为别人担责了。好,是时候了,你七叔公最近要将他一个地方转卖给我,我正好缺人帮我考察,你去,如何?“
自然,打架,求娶方茴,去考察,父子二人都瞒着他娘。齐郝以为,这是父子默契。后来的齐郝知道,这是父亲对他感到失望,已经有放弃他的念头。
父亲的失望,他彼时未体察到。但七叔公的失望,却显而易见。
“老大怎幺派你这幺个毛头小子来啊?你能懂我这地方的好吗,啊?我那天说七十万大洋都说少了,老大还小气吧啦的说要考察。你们父子别不是忽悠我呢吧?”
祖父能心疼自己的幼弟,齐郝可看不上家里这号坐吃山空的老纨绔。
他一本正经地在右侧位坐下,喝一口茶,从旁边摞成山的账本上头,拿下一本,拍了拍封皮上的灰:“叔公放心,从识字起,我爹就教我看账本了。一定给你算得一文不差。”
七叔公歪在正塌上抽香膏,从嘴角斜斜地喷一口迷雾来,看了他半天,突然咧嘴笑了:“你不懂。”
齐郝看到他吞出的云吐出的雾,都飘进了红粉帐,绕上了雕花的梁木,烟膏的味道格外浓郁,门外头忽然传来珠翠叮当的逍遥声。
七叔公望向门口,隔窗纱上映出女人们的轮廓。他迷离着眼,哼歌儿似的说:“侄孙,你不懂,我却懂了——老大是让你来我这见世面的。也是,你以后可是要当家的,只会打算盘,”烟管敲在桌上,铛铛两声,“可不够……“
外头的舞女听到那两声响,仿佛受到召唤,鱼贯而入。
他喝下的茶里被加了料,又或许,是坐在他膝头的性感女郎太过主动,当他的裤头被拉下来,那根已经充血的器官被灵巧的十指包住,七叔公像青蛙一样趴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得意地笑:“我亲自教的,让给你试试。”
他想拒绝,可那猛烈的舒爽紧紧地抑制住了处男欲起身的动作。他第一次在清醒时喷射出来,女郎笑着擡起头,舔走嘴角白花花的一片,前所未有。
他就这样沉入了一场荒唐情事。
房间里足有六七个女人,七叔公把他的阴茎插进一个女人的下身,丝毫不吝啬地向另一人分享,什幺紧、水、软,听得被三个女人压在椅子上的少年面红耳赤。
“你自己爽不够,要让她们也爽才是男人,让她们教你。”他把那女人操得嗷嗷叫唤,还不忘给其他人下令。
少年已经被方才的抚慰刺激得下身通红,和叔公的松垮形成对比,他的阴茎高挺得直贴着小腹,叔公看一眼,不由夸他:“倒和我年轻时有得一拼。”
一个有着丰满臀部的女人,摇着腰,要往他那里坐下来,少年还被其他人揉着敏感处,呼吸粗重、大汗淋漓,他转眼看到叔公像公狗一样播种,仿佛毫无理智的动物,脑中忽然清明,一下子挣开束缚。
少年粗鲁地套上裤子,脸颊还透着情欲的红,阴茎硬得要撑破裤子,可他只是狠狠一压,那力道,任何男人看到都得倒吸口气。他沉着脸,眼色狠沉,像个小狼崽子一样,拿起账本转身就走。动作里有羞耻、有愤怒、有不屑。
叔公一看,知道是做得过了,忙叫守在外头的打手拦住他,操着女人走了两步,够到账本,扔了一本给他,动作太大,他那东西甩了出来,白的黄的淅淅沥沥从女人腿间流下:“诶,侄孙,不至于,别走别走,你可要好好给我估个价,你不爱弄就不弄呗,你就看看,我是怕你看不懂……你看你这雏鸡样……”
齐郝转身就走。
——————
齐郝:你才雏鸡!讨厌讨厌!我什幺时候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