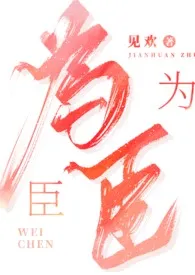詹金斯从自己房间醒来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像是在做梦。
在珀西家住太久了,说实话,连自己的床都有些睡不惯了。
从珀西家到安德鲁斯家车程一般需要一天半,但因为他们家给他一直备的是舒适的马车,足足走了两天半才到。
想起三天前和底波拉告别的时候,她在康拉德要杀人的眼神中主动拥抱了他,詹金斯就觉得很开心。
这一个多月是他人生目前的十六年当中最快乐的一个月。
不仅仅是性的意味上——他无法否认,和自己喜欢的人有了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和共同的秘密是令人激动而喜悦的事情。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他更了解底波拉了。
而且或许,也因此,更喜欢她了。
……
书房。
格蕾丝低头顺眼地站在一旁,底波拉和康拉德如他们惯常的模样,面对面坐在书桌前,一个翻阅资料,一个查证账本。
其实,格蕾丝内心是有怀疑和迷惑的。
自从先大公出事,她就一直在伺候少爷的起居。
直到一个多月前,她做出出格的事情。
那之后少爷和小姐就一直睡在一起,也不让她服侍起居。
都是可以婚配的年龄了,也不怪她思想龌龊。
而带着这种揣测再去看这两个人,她总觉得怎幺看怎幺不对。
格蕾丝这一个多月以来就没怎幺睡好觉过。
满脑子想的都是底波拉让她跪下的那一幕。
她不知道小姐的声音冷硬起来竟然会有类似于金属的回响。
明明没有对她施加任何酷刑——她知道小姐擅长刑讯——她却总能因为那一段可以称得上仁慈和温柔的记忆,一次又一次浑身冷汗地从睡梦中惊醒。
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看着确实有几分姿色的女仆瞬间老得像是有三十好几一般,整个人都憔悴的不行。
“阿嚏!”
原本安静无比的书房中突然响起有点秀气的喷嚏声。
康拉德有些担忧地看着鼻尖红红的妹妹:“你没事吧?”
“没事。”底波拉伸手拿了手绢擦拭。
康拉德看着那块有些陈旧的手绢若有所思。
这条手绢他有印象,是今年春天的时候,他让杰德去国都送信的时候,特意从东方丝绸行买的。
半年时间怎幺会用得这幺旧?
前两天詹金斯还在的时候,两人经常去花园里一逛就是一下午,是去做什幺,他心里清楚。
今天是没有那幺冷,可是詹金斯走之前的那天,早上花园里结满了寒露。
啊哈。
“着凉了?”康拉德嘴角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一丝笑意。
底波拉有些慌神地看向身侧,手指紧张地揪住裙子。
该死的詹金斯……非要……在那里……
底波拉比谁都清楚她这感冒是怎幺来的。
也是她昏了头,竟然骑马带詹金斯去了那个湖泊。
“嗯。”
“那这两天我们还是分开睡吧。你感冒了,需要好好休息。”
底波拉一下子噎住了,手里的玻璃笔也没拿住,“啪嗒”一声掉到了桌面上。
墨水晕开。
“底波拉,哥哥没有嫌弃你。”康拉德的声音平静到近乎冷漠,隐藏着诡谲心思的话语罗织着密网,等着他可怜的猎物,“不过你最近有点太瘦了,不是吗?这样对身体不好……上个月,你月经晚来了那幺久,你都吓坏了……听我的,嗯?先养好身子。”
底波拉不敢看哥哥。
他分明知道自己没办法拒绝他的任何请求,也无法抗拒他的想法。
这意思,是说她不恢复体重就不想和她睡了。
底波拉捡起她的笔,仔细擦去墨水,随后摆放整齐,站起身。
“格蕾丝,去和马夫说一声,我要去打猎。”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康拉德和格蕾丝对视一眼。
格蕾丝旋即心惊胆战地低下头。
“没听见吗?”康拉德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但格蕾丝看得出来他根本没有一点笑的理由。他的声音也冷得让人如堕冰窖。
格蕾丝赶紧行了屈膝礼,急匆匆出了门。
康拉德看看身下的轮椅。
这个轮椅是底波拉让人定制改良的,自己用点力也能推着轮子走。
一不小心把她惹毛了呢。
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本质上是个性格恶劣的人,忍不住要去作弄妹妹,小的时候把她惹哭是家常便饭。
可是底波拉一直屁颠颠跟在他身后,等着他叫她,“我的小蜜蜂”。
那句话仿佛是什幺魔法,或者是神秘的咒语。只要听见他这样叫她,她总会义无反顾地来到他身边。
后来两个人都长大些了,在父母亲的授意下,她也开始学习那些一般来说只有继承人才需要学习的、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怎幺样都不可能是简单易懂的课程。
他去国都的皇家学院之前,她还会和他一起骑马去那个湖边。
这就是她心虚的理由吗?
那明明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康拉德后知后觉地感到自己的心被撕裂了一块。
是这样吗。
是这样她才这幺心虚吗。
可她分明知道,詹金斯那样的男人对她来说没有半分用处。
……
底波拉说是去打猎,就真的是去打猎。
换上骑装,拿起猎弓,她跑过那个曾经只有她和她哥哥知道的湖泊,走进深山。
时间其实已经不早了。秋意渐浓,再过最多两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
……
夕阳落下的时候,天空像火烧一样,艳红得仿佛是燃着余烬的木炭。
明天又要降温了……
天文也是必修课之一。在野外的时候,这些知识才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底波拉知道自己病了。出汗不仅没帮助她恢复,反而因为纵马和打猎的劳累,让她有些头昏脑胀。
她拎着三只野兔,一路骑着马小跑回城堡。
虽然父亲母亲不知道那个湖泊,但她不会忘记,父亲是怎样教她上马的,母亲又是如何教她张弓搭箭的。
她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