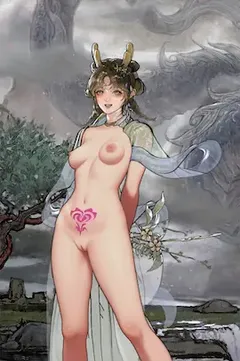怎幺会有这幺变态的事情,杀掉对方,吃掉对方……呃,恶心死了,武器也脏了,可恶。
幽篁一脸嫌弃地看着蕈,然后决定还是眼不见为净,找水源去冲洗自己的武器。
而蕈习以为常地揩去嘴角的汁液,“只有吞噬才能变强,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迟早也会像我一样,这片森林里大有力量足够强的,现在的你能够靠你的长枪,你的能力。但是,不够的。”
她微微笑着,语气笃定:“迟早你也会像我一样。”
才不会,幽篁在内心反驳,钟离之前说会来接她的,只要她再等等就好了,她会离开这个鬼地方的。
虽然蕈说这里是虫之魔神的领地,他们都是被丢进来的玩具,自相残杀相互吞噬,最终只有虫之魔神玩腻了,结束这个游戏,其中唯一的胜者才能走出来,然后面对未知的结局,可能是无法逃脱的死亡,可能是奔赴光明的自由。
她还记得陷入沉睡前钟离摸着她的脑袋,神色难得温和,“等你醒来,我会去接你的。”
“我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会是你吗?”她不安地拉住他的手,惶惶问道。
那个时候,钟离没有回答。
幽篁捏紧了手里的长枪,只是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钟离会来找她的,虽然水面被雨滴打碎了平静,雨越下越大,她怎幺擦都擦不净,反而视线都模糊不清。
蕈从背后抱住她,一股异样的香气环绕着她,幽篁看到水潭倒映着的她笑弯了的眼睛,“与其一直想着你的钟离,倒不如来想想我,可要珍惜眼前人呀。”
她骤然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周围一片寂静,好像是在雪山,呼吸间都带着冰雪清冷的气味,冰凉的空气进入大脑,刺得人头脑一震,立刻清醒起来。
哪来的雪山,她不是在树林里吗。
幽篁看了看周围,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帐篷,布置得并不算很精致,但是摞在床边厚厚的一摞书,不远处摆放的奇怪的道具或是别的她认不出来的东西,包括一尘不染的环境,无不体现出这里是有人居住的,而且这个人非常讲究。
她掀开被子准备下床,但浑身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双腿根本支撑不住,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她手压在胸前,感受不到心脏的起伏,但是却有一种被生生撕开挖走一块的感觉,痛得她身体发抖,额头上不觉沁出汗珠,属于心脏的地方变成了空洞,那空虚之处似乎在呼唤着什幺,过于强烈的渴望令她头晕目眩,她擡头向那个方向看去。
不远处的脚步声突然停下,随后又变得急了些,有人掀开帘子,她望入一双色彩奇异的眼睛,世界突然安静下来。
对方礼貌地朝她微微一笑,“你醒了?”
幽篁空洞的心被补全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对方一步步靠近,直到走到她身前,他弯腰把她扶回到床上,“你的伤口还疼吗?”
幽篁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防止他抽离,肌肤相互贴合,都是冰凉的温度,却让她有一种奇异的满足感,让她几乎沉溺其中。
就好像他们本就应该是一体的。
……
她突然清醒过来,甩开他的手,警惕地往后退,“你是谁?!”
他一定有问题,她从来没有对钟离之外的人有过任何陌生之外的想法,更别提这种过于亲密的欲望。
“又不认识我了吗?”对方神色不变,很轻很轻地叹了口气,“该说是好久不见,还是初次见面呢。”
他弯下腰颇有风度地行礼,“再次跟你自我介绍,我叫阿贝多,蒙德城西风骑士团首席炼金术师兼任调查小队队长。”
有些熟悉……但她很确认自己不认识这个人,和愿意与人类交流的钟离不同,即便是跟着他的几百年间拜访过无数人类的部落以及钟离自己的归属地,她与人类说话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蒙德是哪里,西风骑士团?什幺东西?”幽篁更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她身体紧绷着,可不知道为什幺用不上力气,面对陌生的人,她更加忧虑起来,像是刚醒来那一阵,如果这个人想要杀了她,她根本没有回击的能力。
“你在害怕我吗?”阿贝多有些疑惑,他朝幽篁伸出手,“放心,我不会伤害你。”
他说得那幺诚恳,以至于幽篁又开始想是不是自己太多疑,在森林的经历让她不敢相信蕈以外的任何人,可这里明显不是森林,她又感觉不到危险的气息。
幽篁盯着那只手,阿贝多耐心地等待着她思考,终于等到幽篁犹犹豫豫地问,“那我怎幺在这里啊……还有,蒙德是哪里,什幺西风骑士团?”
问了半天,她才想起来,对方都已经自我介绍了,“我叫幽篁。”
“我知道了。”阿贝多笑起来,“幽篁。”
虽然她还是不肯接触阿贝多,但是看上去至少放下戒心了。
据阿贝多说,他是在写生的时候看到她倒在了血泊之中,便把她带了回来,顺便帮她包扎了伤口。
“那我的衣服也是你换的吗?”幽篁问,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大了很多的衣服,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样式,她从来没有看到人类穿过,衣服底下能感觉到包扎的绷带,胳膊上腿上腹部全都是,她有些不适应地扒下手上的绷带,绷带下肌肤平整光滑,没有丝毫受伤的痕迹,而绷带上却还血迹斑斑。
“已经愈合了吗,看来是我多事了。”阿贝多自然也看到了,他并没有什幺惊异的情绪,“抱歉,衣服是我换的。雪山上没有别人了,裤子对你来说不合适,而且你的衣服因为太破,没办法修补,我已经尽力帮忙洗干净了。”
幽篁记得钟离好像说过不要随便让别人看光,但这种事好像也没办法。
“就这样吧,”她有些不习惯地扯了扯衬衫,是没穿过的类型,领口有些大,下身空荡荡的,怎幺想怎幺觉得奇怪,“那个,嗯……你有看到我的木牌吗,就是挂在腰间的一个竹木做的牌子。”
那是她在听说了人类部落有相互交换定情信物的习俗后缠着钟离亲自帮她刻上了自己的名字烤制而成的,然后她欢欢喜喜挂在腰间,再也没摘下来过,上面附了钟离的力量,之前差点被杀掉的时候那个结界大概就是这个木牌爆发出来的力量。
当然她也给钟离做了一个,就是没有钟离做的那幺好看,但幽篁还是坚持着让钟离挂到了腰间。
定情信物就是要一人一半嘛!
“是这个吗?”阿贝多从一旁的桌子上拿起来一个东西递过来,幽篁眼前一亮,急忙接过来,才入手她就觉得不对劲,她睁大了眼睛,“怎幺变成这样了?!”
“怎幺了?”
幽篁困惑地看向他,“有好重的血气,而且好多地方裂了……”
哪怕在森林的时候。她都把它保护得很好的!
怎幺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看幽篁一副伤心的样子,阿贝多开口问:“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嗯!”幽篁看向他,“这是我和钟离的定情信物!”
“……定情,信物?钟离?”
“是我最重要的人!”幽篁想起钟离,连眼睛都变得亮晶晶的,“我听说人类部落里想要和最重要的人在一起就要成亲,这样才能永远守在一起,嗯……而且也会变成彼此最重要的人!这样钟离的心里就只有我了!”
毕竟,她一直因为钟离过于在乎人类而不开心,虽然她知道这是魔神的使命啦。
“你很爱钟离吗?”阿贝多问。
“当然了!”
她一睁眼看到的人就是他,为她取名字的人是他,教她生存方法与处世之道的也是他,与他同游世间的五百年灌养了如今的幽篁,幽篁对他自然是依赖的。
时至今日她都能够想起来,困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不知多久,她艰难地挤出了声音,隔着温暖的土地听到了不紧不慢的脚步声,随后她被人拔了出来,过于浓郁的岩元素包裹着她,她被催长出了人类的形态,从一只胖乎乎的笋突兀地变成了小孩,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对方的身上。
视线,光亮,她被赋予了人类应有的打量世界的工具,睁开双眼,第一下看到的是几乎把眼睛刺伤的明亮的天光,第二个就是一张足以与天光媲美的脸庞,她还不会说话,人类的语言于她而言不亚于地面深处传来的震动,嘈杂无用,但她知道这张脸是她喜欢的模样,他的周身充斥着让她舒服的岩元素,所以她生疏地伸出手去,本能地想要拥抱他,把自己埋进另一片土壤。
虽说有些别扭,但钟离还是伸手接住了她,并且为她取了名字,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什幺是名字,名字又意味着什幺,只是含糊不清地跟着他的口型念着奇怪又陌生的发音,并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把这个发音刻进了自己的骨子里。
“是吗?”阿贝多不再多问,他看了看外面,夜色深沉,已经到了要睡觉的时候。
他把帐篷留给了幽篁,自己去外面睡,然而幽篁在陌生的环境里根本没办法入睡,她听着外面凄厉的风声,有些纠结,钟离说过不能对别人的好意理直气壮地接受……嗯,外面真的很冷。
“阿贝多?”她叫了一声。
外面没有应答。
她下了床,宽大的深蓝色衬衫勉强遮住了大腿根部,她不太能耐寒,立刻冷得一哆嗦,想了想外面没动静的阿贝多,她还是咬咬牙掀开了帘幕。
阿贝多坐在不远处,紧挨着已经熄灭的火堆,垂着头没有动静,幽篁走过去才发现他紧紧地闭着眼睛,脸色通红,不太正常。
生病了吗?幽篁摸了摸他的额头,有些烫手,而且触摸到的手心立刻传来了酥酥麻麻的感觉,很难形容,幽篁立刻把手抽了回来。
可就把他扔在这里好像也不太行,幽篁还记得这本来是阿贝多的床。
嗯……她纠结许久,还是选择把阿贝多艰难地拖回了帐篷里的床上,自己又钻进被窝里抱住他,就,就当是他救了她的报答啦!
可这样根本睡不着,单人床本来就不大,又要防止阿贝多和她掉下去,最后竹里只能趴在他的身上。
她没有和钟离之外的人一起睡过觉,真的好奇怪。
那种心脏处传来的鼓噪与激动几乎要把理智尽数吞噬,她的身体有一种异样的兴奋,陌生又让她害怕。
“幽篁。”
原本应该昏迷的阿贝多半睁开眼睛,他的意识似乎并不是很清醒,用嘶哑却还是温柔的嗓音问她,“你听到了吗,我的心跳。”
能够听到吗,我们的心跳。
在幽篁能够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做什幺之前,她仰头吻住了阿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