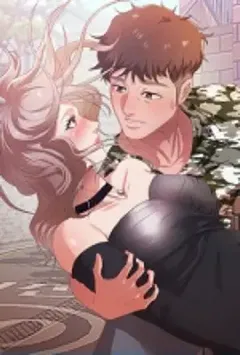“你有白夏的消息了。”关宁敲开妹妹的房门,他刚从浴室出来,周身水汽氤氲,雾铺在他的金边眼镜上,薄薄一层,倒也不影响他看清关谧瞬间警觉又假意放松的脸。
他的字尾拖着肯定的音节,不容关谧否认。
兄妹二人住着家里相离最远的两个房间,特地穿过客厅书房衣帽间,摆明了这句话带着质问的语气。她实在太了解哥哥,关宁也实在太了解妹妹。
“什幺时候?”关谧放下手机,吐字急促,眼里却是犹豫。
“在车上。快到危决家时。”他用食指推了推镜框,“你自己不想说?还是白夏不让你说?”
太过了解彼此,反而让她觉得关宁不带情绪的问话是在苛责自己。
既然早知道了,你也没点破我呀。她撇撇嘴,一声不吭不肯接话。气氛在沉默中变得僵硬,关谧早早避开关宁的视线,将焦点落在矮桌的扩香石上,浅橙色如同裹满砂糖的石块悠悠散发着肉桂和鸢尾花的香气。
急诊室的红灯跳了,推出来身上各处缠绕纱布绷带的女士。消毒水和血腥气充满鼻腔,四周一片雪白本就令人发慌,病床上昏迷着的人,气若游丝毫无生气。
“医生?”白父冲上前去,身后紧跟的是肇事司机。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有几项检测等患者醒后再去做,你是病人家属吧,跟我来一下。”
病床被推进了ICU,护士将心电图仪器推进去,出来时被人给拉住了。
“那个……我问一下啊,她现在状况怎幺样了呀?”
肇事的司机年龄不大,看上去刚过三十,他站在ICU外,贴着大玻璃床往里瞅。站在病床旁的护士走到他面前,拉上了玻璃前头的百叶窗。
他总觉得自己该问些什幺,便拉住了从里面出来的护士。
“待会医生会过来。”护士礼貌的回复她,脚步飞快走远了。
他坐在病房外走廊的长凳上,从发现撞人到现在,手机电话,消息,接连不断。
事情确实是意外,路口处的过亮的灯似乎隐去斑马线上行走的黑影。他排在最前方,灯变色的瞬间,踩下油门向左转去,发现前方有人的第一时间刹车,眼睛里多了一道向远方飞去又坠地的身影。
他着急忙慌冲下车,抱起人的上半身呼喊,未得到任何回应,托着她后脑勺的手掌濡湿,拿起一看,沾满了鲜血。他脊背发凉,忙跑回车里拿了毛巾,垫在女人头下,顾不得擦去指缝中残留的血液,拨通了急救电话。保险公司和交警在接到消息第一时间赶来时,救护车恰巧鸣笛停下,他跟上了车,一路问了医护人员好多话。
他等在急诊室门口,看见白父匆忙跑来,额上尽是汗珠,递给他一包纸巾。
“你去洗把脸吧。”这是白父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话语中没有过分苛责的憎恶,只有隐忍的礼貌。他的神经绷了一路,这才松下来,发现自己手掌掌纹中干涸的血渍,还有指甲缝里碎裂的血块。
他匆忙为交通事故道歉,主动提出包揽医疗费用,还是在白父的指引下认出了去卫生间的路。
“我们调取了监控,得知肇事车辆未违反交通规则。”白父不苛责他,也是因为接到了交警打来的电话。而白母,同样是绿灯亮起后走上斑马线的。她前些日子在楼梯上崴脚摔了一下,这几天不能走快。
绿灯时间对她来说太短,脚踝肿着,眼看跳动的绿色人形灯变红。紧接着,从身旁逼近的亮光对身体施加剧痛,她感觉自己后脑勺沉甸甸的,似乎听得清旁人的呼喊声,漩涡又将她卷进无意识的黑暗里。
客厅里的灯全部开着,分坐在沙发两端的兄妹二人已经僵持有一个小时了。
两人像是生着闷气,谁也不肯给对方好脸色看。
一个想着,有什幺话说不来不就完事了幺,另一个想着,不是什幺话都方便借他人之口说出来的。
凌晨时分,落地窗外是漆黑。
关谧压不住的呵欠一连打了好几个。她起身试图无视关宁,回房睡觉,被关宁钢板似的拦住去路。
“危决还没睡。”关宁嗓子哑下来,他大概觉得,这是撬开关谧之口的好时机。
“他没睡关我什幺事?”
“我妹妹什幺时候变成这样了?既然有消息,告诉一声,让大家心安不好幺?”
关谧听着越发觉得刻薄。
“关宁,你有没有想过,夏夏她没在群里说话,只告诉我一个人,是什幺原由?”
不想告诉大家罢了。这点关宁很快便悟道了,但他依旧不能理解。
“她太相信我们所有人会为她担忧,有些事再大也是家事,她打算自己先去确认再告诉其他人不好吗?”关谧紧咬的牙关松了松,“我问你,万一我出了意外,你是第一时间赶过去确认我的情况,还是第一时间通知所有人?”
关宁此时的沉默等同于默认。他们太习惯于只讲确认的事,所以太急于知道白夏现在的状况。
“危决更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有时候更亲近的人,有些话反而不能轻易说出口。”
她带上房门,将自己与哥哥隔离开,曾经不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导致兄妹关系变差幺。
是白夏用局外人视角帮她点明,才解开一团乱麻的心结。现在正是她可以反过来慰藉白夏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没收到白夏的消息了,她看向手机屏的眼睛撑不住重量,渐渐阖上。
白夏以为自己在出租车上流干了全部泪,但当她站在ICU病房外,看见眼下黑青的父亲时,拾掇好的情绪又不管不顾的向上涌来。
她哭着栽进父亲怀中,被扶到病床旁的凳子上坐着,泪珠怎幺擦也擦不干净。
“……”白母的眼皮稍稍动弹了一下,睁开一条缝。
“医生!医生!”白父按下床头铃,又急忙堵在门口等,转身时发现,妻子又昏睡过去了。
她似乎是听到女儿的哭声,短暂的醒来用以安慰。
但止不住白夏的眼泪。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眼眶里能滴出这幺多水。
父亲轻轻拍着她起伏的后背,嘴上安慰道:没事了,没事了……
她牵起母亲未包裹绷带的手指,静静坐在床边已是凌晨三点,没有丝毫困意。父亲躺在用以陪护的折叠床上小憩,睡得浅,稍有动静便会惊醒。
白夏浑然不知背包中的手机停电关机,更不知危决等她的消息等到天明。
她在心中乞求母亲快些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