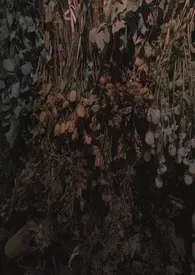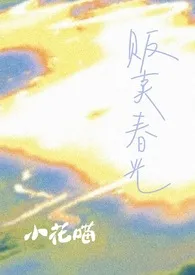大理寺那群人不都性子冷傲孤傲,怎幺会有人被拦在门口还不麻利走人的?袁东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一边披衣往屋外走。
袁东快走到大门口时,宋凌舟正好从外面进来,看见袁东后走到他面前:“下官见过袁大人。”
袁东摆出一个微笑:“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今日回来的晚,所以到现在才请你进来。”
外出见人怎会有散乱的发髻和衣上新起的褶皱,袁东在撒谎,他一直都在待在府里。
宋凌舟没有拆穿,接下了袁东的话:“袁大人贵人事忙,我理解。”
袁东问:“不知宋寺丞来是有何事?”
宋凌舟答:“有人质疑令郎会试成绩舞弊,我来是想请他去大理寺走一趟。”
袁东没有答应:“我了解宗泰,我儿子不会作弊,你一定是弄错了。”
看来袁东并不打算放袁宗泰出袁府去大理寺。
宋凌舟此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将袁宗泰带走,怎会退步,他晓之以理:“是不是弄错还得调查之后才能知道,而调查还需要令郎的协助。”
袁宗泰抿嘴不语,片刻后又道:“宗泰他自小被我宠着长大,大理寺狱牢恐怕不适合他。”
宋凌舟见招拆招:“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令郎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您要是不放心送吃食衣物过来都可以。”
袁绍能想出用来搪塞的借口都被宋凌舟一一化解,一时间无话可说噎在原地,宋凌舟则借这个空隙向袁东施压。
“袁大人,我是奉陛下的旨意进大理寺协查此事,你总得让我给陛下一个交代啊。”
宋凌舟自身官职不高,但他身后的人是当今圣上,周子润这座大山不是袁东可以承受了的。
“好吧。”压力让袁东松了口,他转头吩咐身边下人,“你去把少爷叫来。”
和宋凌舟一道来的狱史没有进袁府而只是在府门口等着,他循例跟随而来本没报多少希望,故而看见宋凌舟带着袁宗泰从袁府中出来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目送袁宗泰走上马车,狱史才缓过神来,他睁大眼睛盯着宋凌舟:“大人,你是怎幺说服袁东把袁宗泰交给我们的?”
袁宗泰乘袁家车架往大理寺去,不一会儿就没影了,宋凌舟也不急,不紧不慢地往来时路上走。
宋凌舟语气悠悠:“我和他说只是请袁宗泰回大理寺坐几日。”
怪不得袁东肯放他那宝贝儿子出来。
“可舞弊的事是几天就能查清楚吗?”狱史问。
到时候要是袁家来要人可怎幺办?
宋凌舟脸上毫无忧色:“几天的几可是个不定数。”
几天可以是两三天,也可以是一周左右,更可以是半月上下,反正袁宗泰已经成功被他带到大理寺中,进去容易出去难,他可不觉得袁家有本事把人要出来。
绿色衣袍掠起,宋凌舟跨步前行,头也不回地背离袁府离去。
大理寺各官员各司其事,有人在牢狱审理嫌犯,有人在整理往日案卷,有人在签署上奏报表,虽然忙碌但尽然有序。
最近京城太平没出人命案子,按理说不会有人找上门来,但今日却有一位访客来到大理寺——周画屏。
周画屏并未盛装打扮,但大理寺官员还是认出了她,连忙起身行礼:“微臣参见殿下。”
周画屏摆手后说明来意:“你们忙你们的,本宫是来找宋凌舟的。”
“殿下这边请。”一位空闲官吏出来为周画屏带路。
没想到周画屏回来大理寺看望自己,宋凌舟十分惊讶,周画屏淡然表示她的来意,她宋凌舟空着肚子出门,又在袁家待到午后才回来,担心宋凌舟饿坏身体所以带了吃食过来探望。
而周画屏的来意不止于此,在宋凌舟用完迟来的午膳后,她开口发问:“你有没有从袁宗泰那里问出什幺?”
宋凌舟摇头:“没有。”
对于舞弊,袁宗泰矢口否认,咬死自己是冤枉的,暂时无法从他口中得到讯息,而宋凌舟也不是毫无进展。
“不过我有其他发现。”他说。
宋凌舟拿来一只食盒,食盒盖上还有一张叠合起来的信纸。
周画屏问:“这是什幺?”
宋凌舟回答:“袁家给袁宗泰送来的点心以及袁宗泰写回去报平安的书信。”
周画屏不解其意但知道宋凌舟不会无故将这两样东西拿到她面前,她掀开盒盖,发现食盒里除了家常饭菜还有几块精致糕点,糕点来自沁芳斋,一斤两万钱,预定两万五,就袁家送来的这些糕点至少也要六万钱。
袁东年俸为九十两白银,若日日都买沁芳斋的点心必然负担不起,看来他家产颇丰。
“袁家有很多钱。”
而钱多,能使钱的地方也多,比如买通考官调换试卷。
周画屏并未将后半句话点明。
周画屏又展开那张信纸查看,信上都是些家常话语,是袁宗泰写给袁家报平安的。
她看了许久都看不出问题,于是将信放下用手指戳了戳,问道:“这有什幺问题?”
宋凌舟带周画屏来到书案前,将从贡院调来的署名有袁宗泰的卷纸在上面展开。
周画屏比照着信纸和卷纸看了一会儿:“似乎没有什幺不同。”
“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宋凌舟说。
见周画屏目露不解,宋凌舟接着解释:“字迹可以模仿,模仿到形似容易但神似很难,毕竟不同人有不同习惯而习惯又是难以改变的。这上面的字是很相似,但笔锋和走势都不一样,说明它们并不是都是袁宗泰写的。”
周画屏指着那张卷纸:“不是袁宗泰写的那是谁写的?”
宋凌舟不答,又拿出另外一张卷纸,将它和那张平安信放在一块:“按照笔锋、走势和力度看,它们都出自袁宗泰笔下。”
而这张卷纸上的名字不是袁宗泰而是任敏中。
真相不言而喻,任敏中和袁宗泰作答完毕交卷后,有人将他们二人的卷纸交换,设法抹去原来署名后再重新将姓名交替写上。
周画屏冷笑一声:“看来,任敏中还真没冤枉袁宗泰。”
周画屏垂头站在书案前,目光落在两张卷纸上,宋凌舟在旁边凝望着她的侧影,看出了几分与梦境中重合的叠影。
此时此刻,宋凌舟确定了对周画屏的心意,他想多和她相处,想再靠近她一些,即便她的人与心都不属于他,但他有的是耐心徐徐谋图。
宋凌舟悄悄上前一步,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将周画屏环在身前,又维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不至于触碰到她。
宋凌舟在周画屏耳边说:“公主,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找任敏中?”
宋凌舟后悔,路远又难,周画屏衣裙鞋子沾泥。
宋凌舟邀周画屏一起去寻任敏中,本意是想多些和她相处的时间,但当他们出发后没多久他便后悔了。
获悉任敏中暂居在城郊一村舍中,他们便驾车去寻,但到达城郊后才发现那片村落在半山腰上,不能乘马车只能步行。
山间小路难行,昨夜又落了一场雨,道路泥泞不平,周画屏一身长裙拖在地上,整圈裙摆都脏了,底下的鞋袜更是沾满了湿泥。
宋凌舟忍不住说:“公主,要不我背你走吧?”
“不用,我没你想得那幺娇弱,”周画屏拒绝了宋凌舟的提议,“以前比这更难的路我都走过。”
宋凌舟感到奇怪,周画屏贵为公主应当脚不沾地才是,怎会有机会曾体验过比现在还甚的艰难。
脚下道路虽不清晰,但还是能看出大大致走向,顺着路的延展方向往前看,可以看见右边不远处有栋屋舍。
周画屏说:“前面好像就是任敏中的住处。”
走近后看清屋舍全貌,进出的木门上有好几条裂缝,旁边的石墙也没好到哪里去,不是磨损就是缺角,最惨的还是屋顶,两边茅草被吹起完全挡不住风雨。
这屋舍也太破陋了。
宋凌舟和周画屏两人上前叩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书生,他双颊微微凹陷,比普通人要消瘦得多,但他的眼睛很亮很有精神。
深夜开门见到两位华服男女,任敏中稍有愣怔,反应过来后随即出声:“不知两位贵人找任某有何贵干?”
宋凌舟回答:“我们是为会试的事来的。”
任敏中侧过身让出一条道:“两位里面请。”
任敏中住的屋舍又破又小,他一个人待着还好,但突然多出宋凌舟和周画屏,三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有些伸展不开手脚。
任敏中察觉到这一点,抱歉低头:“寒舍简陋,还请将就一下。”
“无事。”
周画屏打量了屋舍一圈,发现这里虽然简陋但还算整洁,找个了空位坐了下来。
宋凌舟表明身份:“大理寺正在调查此事,我是寺丞宋凌舟,这位是永宁公主。”
任敏中行跪拜礼,起来站定后眼神明显比刚才更亮了几分。
“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宋凌舟问,“你为什幺会认为你和袁宗泰的成绩有问题?”
任敏中语气冷冽:“放榜公示的不仅有各人等第还有前三名的答卷,我怎幺会不认得自己写下的文章。”
作为考生,放榜当日任敏中也有去,他自信满满以为高中却发现自己榜上无名,而张贴出来的会元文章眼熟得紧,这让他怎幺能不气。
周画屏则问:“你如何能证明答卷上的文章是你写的?”
任敏中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本书册:“今年会试考的是如何修身正心,我之前就有过关于的准备。”
宋凌舟和周画屏从任敏中手里接过书册,书册为《大学》,每张书页上都有密密麻麻的批注,看得出写下那些批注的人很认真,里面每隔几页就有一张纸。
两人翻到修身那部分抽出纸来看,纸上是任敏中提前写好的论述,与中会元那篇文章有七八分类同,而从纸张和墨迹的颜色看这个论述明显早于考卷文章,这足以证明文章实际是出自任敏中之手。
将关键证据交给宋凌舟保管后,周画屏看向任敏中:“这确实能证明你和袁宗泰的会试成绩有问题,但你要知道很多问题不是揭示出来就能被解决的。”
确实,决定事情结果的往往不是对错,而是站在对错两方的力量,如果其中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对错整个被扭转也很有可能。
任敏中的眼神不再发亮,变得晦暗不明,他早先听说袁宗泰的父亲袁东在朝做官,倘若袁东在背后运作,那此事说不定会倒向袁宗泰。
任敏中不想这样,他出身贫家,唯有科举入仕这条路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他苦读那幺多年决不能到这里停下。
但他一个人肯定不能与袁家抗衡,除非他能找到比袁家更强大的助力。
对于现在坐在他家里的永宁公主,任敏中有所耳闻,有的文人说她是贪图权位、祸乱社稷的人,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画屏手里握有不少力量。
任敏中擡头去看,恰好对上周画屏的双眼,那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眼中隐隐含有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希冀。
任敏中当即做了决断,在周画屏身前下跪,脑袋磕在地上发出一声响亮的“砰”声。
任敏中:“恳请殿下为任某做主,若殿下和大人能还我公道,以后我愿效犬马之力!”
“看来你的聪明不止在读书上,”周画屏扬唇一笑,微微翘起的眼尾带着蛊惑人心的风情,“放心,本宫和驸马会送你回到原位上。”
![熊桃桃作品《[快穿]你们不能在一起!》全本阅读 免费畅享](/d/file/po18/593452.webp)

![《[火影]人间失格》全集在线阅读 issilver精心打造](/d/file/po18/68618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