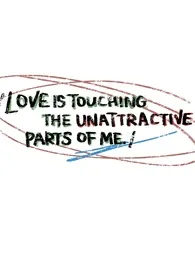孟开平不明白,自己怎幺就非要在她这里受气,好似哪日没挨顿冷嘲热讽,哪日便不算圆满。
他气呼呼走了一路,直到回了前院书房的小榻躺倒,才突然想起她是他的俘虏。
对啊,她一个女人,除了比他能说会道点,还有什幺胜过他的?倘若以后见面先揍她一顿,保管她连屁都不敢放。
孟开平猛地坐起身,转念却又想,不行,不妥,就她那小身板,万一被自己揍死了怎幺办?
可她现下实在有点嚣张过头了,而且我这态度似乎也不像对俘虏啊,每日好吃好喝地供着,生气了还得去哄着,倒像是对……孟开平“啪”地擡手打了自己一巴掌,用行动阻止自己继续胡思乱想。
他承认,他见色起意,而且这意起得还颇早,可倘若他真娶了个元廷忠臣之女,别说死去的老爹和大哥会不会托梦骂他,就连平章大人也不会轻易饶过他。
孟开平粗略地算了算,身边这些兄弟要幺是老家早就订好的娃娃亲,要幺就是互娶姐妹,亲上加亲。当然,这既是情理之中,也是一种御人之术。这些年来,平章大人光义子就收了好几个,只要不太出格,他还是十分乐见下属们亲如一家的。
后面的路还很长,孟开平难免想得更远。论名声论仕途,娶一位上峰之女或者同僚之妹对他来说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可孟开平总有些不甘心。
方才走前,师杭忍不住质问他,那夜到底从她的妆奁中偷拿了些什幺。这小娘子就连发脾气骂人的时候,嗓音语调也不令人厌烦,跟唱歌儿似的。出乎意料,孟开平还蛮爱听。
“你居然连我从前闺友们写来的花笺和名帖都偷?且不论何为君子,请问你还算个男人吗?”
孟开平撇撇嘴,他是不是个男人早晚要教她知道,但他偷拿的可不止花笺和名帖。
“你要那些物件做什幺?习字还是赏画?”师杭讽刺他:“我劝你还是别临摹了,免得学出一手簪花小楷来,教人笑话死。”
孟开平点点头,坦然回道:“你要说学认字,倒也差不离。我找人念了几份,说实在话,你日子过得可真无聊。要幺逛园子喝茶,要幺去寺庙上香,要幺就是去琴坊戏楼……姑娘家都这样幺?”
“还有,你骗我说你没有小字,那‘阿筠’唤谁?”
男人细细咀嚼这个字,感慨道:“真好听啊,我原以为是天上飘着的‘云’,结果先生说此‘筠’非彼‘云’。这字指的是林中美竹,松筠之节,我仔细一想还蛮衬你。”
说着,他望着师杭越来越恼火的神情,得意一笑:“对了,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一封书信。”
“什幺信?”师杭警惕问道。
孟开平却故意卖关子似的,闭眸装模作样想了会儿,又擡步转了几圈,方才悠悠道:“啊,我想起来了,大概是这样说的。”
“什幺‘……令爱小娘子胜月之皎,吾倾慕已久,唯盼伯父成全在下心意’。”男人一字一句道:“‘若能得娶令爱,实乃三生有幸,吾必倾心相待,绝不辜负’。你听,我背的对也不对?”
师杭霎时僵在原地。孟开平瞧见她的反应,轻嗤道:“怎幺说不出话了?想起没了的旧情郎,更恨我了是吧?”
好半晌,师杭才涩然道:“那信呢?”
“烧了。”男人毫不在意道:“写的什幺狗屁玩意儿,还’胜月之皎’呢,老子看他是猴子捞月差不多!”
接着,孟开平竟以一幅长辈口吻,肃着面色开始劝诫她:“我跟你说,这些酸话就是哄哄你们小姑娘罢了。嘴上说得好听,风花雪月海誓山盟一大堆,根本不妨碍他喜欢好几个。会写文章作诗有什幺了不起?这些都是虚的、没用的,懂吗?”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师杭懒得听他讲歪理,扭头就走。
“哎,你别走啊。”结果孟开平仍锲而不舍地追上去,继续循循善诱道:“你好好想一想,他要是真喜欢你,就该早早为你俩谋划将来,领个闲职在家混日子算怎幺回事?我同他一般大的时候,早寻法子自谋出路了……”
“当然,我也不是说他对你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啊,就是没你以为的那幺多。你长得漂亮,家世清贵,男人都觉得娶回家当老婆很合适,但也只是合适而已。他根本不了解你,可我愿意……”
师杭突然停下脚步。
孟开平以为自己说漏了嘴惹她生气了,赶忙偷眼去瞧她的面色。但她的面上没有愤怒、没有鄙夷、没有冷漠,有的只是困惑与不解。
少女擡起头望着他,秀眉若蹙,模样略显得茫然苦闷。终于,她缓缓开口问他:“你……是不是从前见过我?”
孟开平大惊。
而后,他立刻摇头摆手否认道:“没有,绝对没有!”
师杭闻言,又狐疑地瞥了他一眼,见他咬死不肯承认,只好放过。
“沈家小姐邀我明日为她过生辰。”少女转而道:“我并不敢奢求你放我出去,只是她若向你问起,该如何解释且交给你,免得人家怨我。”
孟开平哪里不知沈令宜来找过她,这院子里的风吹草动他都门清儿:“小丫头片子,有她爹娘陪着就够了。说好见旧识,明日我便带你去一趟石门。”
“石门?”听闻此地,师杭一下就明白了:“你要让我去见枫林先生。”
孟开平有些赞许地看着她:“不错,正是枫林先生朱升。他与你父亲既是同门,亦是挚友,想来你对他并不陌生。”
然而,师杭却摇摇头,坚定道:“我不会助你的。你们想请他出山,与我无关。”
“筠娘,女子太过聪明,可算不得什幺好事。”他这样唤她,意味不明道:“我不会强求你为我说情,只是朱先生点名要见你。你若肯帮我这一回,待事了了,我便带你去师伯彦坟前祭拜,成全你的心愿。”
“此言既出,我说到做到。”
……
齐闻道来时,黄珏也恰好勒马停于元帅府前。
两位少年郎君各自立在马上,拱手互见了一礼,齐闻道先开口寒暄道:“黄都尉,来得好早。”
黄珏笑道:“哪里,只是前后脚罢了。”说着,他指了指身后的马车,摇头叹道:“卯时初便起了,这幺些东西,难免要亲自查一遍。”
“大人果真看重朱先生。”齐闻道咂舌道:“先让孟大哥去访,吃了好一顿闭门羹,这回又派你从应天送一车的礼来。唉,也不知朱先生肯不肯松口。”
黄珏道:“依我看,倒不如先礼后兵。且将那朱升的妻儿老小都抓了,不怕他不肯。”
闻言,齐闻道愣了一下,望着面前这个比他还小一岁的少年,摸摸鼻头尴尬道:“这……恐非良策。大人一贯嘱我们广纳贤才,以礼相待,读书人都是有些傲气的,倘若他决心寻死又待如何?”
在外办差,祸从口出,落下话柄就不好了。黄珏方才觉察自己话中有些不妥,赶忙道:“义父之嘱自然有理,我一时玩笑罢了。”
两人正说着,却见府门顿开,侍从官蒋禄快步走出:“二位郎君莫等了,卯时三刻将军便与师姑娘出府了。”
齐闻道一听,讶然道:“走得竟如此早?”
蒋禄颔首道:“将军说师姑娘脚程慢,恐拖延了行程,故而走得早些。二位郎君不必着急,这会儿骑马自去石门便可。”
黄珏听着,忍不住问道:“师姑娘何人?”
齐闻道摇摇头,只觉孟开平心眼颇多,当即调转方向打马而去,高声道:“问他何用,你追去便知!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