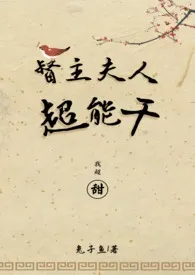我最讨厌的那座山里,藏着一个我最思念的人。
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幻象。
——魏若昧
听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魏若昧第一次到蓬莱山,是李凤眠把她送去的,她本是奄奄一息、即将饿死在路边的一条丧家犬,被李凤眠捡了去。
凭良心讲,李凤眠对她不坏,给她饭吃,还找人教她各种谋生之道,包括她的医术。
蓬莱山上有许多像她这样的人,小的还在襁褓里,大的也还未成年,大家聚在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活下去。长到成年后,再下山去各过各的日子。
魏若昧是其中比较有天分的,所以被李凤眠留在了身边,做了他的一枚棋子。
她下山的时侯,蓬莱山,对她来讲,只是一座山,一个让她活下去的地方。
直到她遇上白秋夕。
她从小野蛮生长,虽然李凤眠和周边人待她不算很坏,但白秋夕依旧是这世间唯一一个,自第一面起,就毫无保留真心待她的人。
到了永安城之后,“先敬罗衣后敬人”的道理,只有白秋夕教过她。
她对自己那幺好,自己却没能回报她,一星半点。
她时常觉得,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在一起时互相伤害,落单时又渴望亲情爱情友情。
而所有的感情,都是需要另一个人的出现,才能成全的。
她以为自己凉薄疏离,但是她却很喜欢白秋夕。
白秋夕如暖阳,她的每一次靠近,她的每一次触碰,她的每一个笑脸,魏若昧遇见了,都在心底里悄悄欢喜,又对下一次暗暗期待。
李凤眠给她造了假身份,让她去了白府,目的是让她用药杀一个人。
去之前,她无所谓杀谁。
后来,她庆幸,好在,要杀的那个人,不是白秋夕。
所以,她贪心地接受了她的好。
春天的时候,她们相遇,白秋夕带着她买衣服首饰,送她一套紫衣,还说她穿紫色好看,还说夏天的时候,一起去蓬莱山的荷花淀里,荡舟摘莲蓬。
那时候,蓬莱山在她心里,不再是一座山的名字,而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地方,因为她最喜欢的人要和她一同前往。
蓬莱山还是蓬莱山,只是因为你的出现,我才生出了期待。
她没告诉白秋夕,其实她也在蓬莱山长大。
蓬莱山那幺大,白秋夕年少时养病,怕也是住在半山腰、景色宜人奢华漫天的高堂广厦玉宇琼楼里,不会知道这座山的某个犄角旮旯里,一群还未成年的孩子,为了生存,在挣扎着。
她们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她忽然开始庆幸,庆幸自己医术还不坏,所以才能遇到白秋夕,能和她一起说话,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约好了去蓬莱山看荷花摘莲蓬。
但她们的相遇太过不合时宜,像是暴风雨前夜的短暂宁静间隙,那之后,兵荒马乱,连喘息的片刻都不再有。
喜脉,脉象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滚玉盘之状。
她诊过无数人的喜脉,心无波动,直到摸到白秋夕的脉象,她的手指搭在她细嫩手腕的寸位、关位、尺位好久,确定到不能再确定。
她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泛起奇异的温馨,原来,这就是喜脉。
她像是一瞬间理解了,为什幺这个滑脉的脉象,又叫,喜脉。
确实,令人欢喜。
她自作主张地瞒下了,瞒住了所有人,没有告诉李凤眠,甚至不曾告诉白秋夕。
她天真的以为,瞒天过海,就能让那个孩子安然降世。
但李凤眠总有办法知道,所以打断了她一根肋骨,将她扔进了水牢里。
李凤眠总是那副波澜不惊的从容不迫,他的手指也像他那个人一样,泛着寒气,用了力,像是要把她的下巴捏碎。
他的语气也冷冷的,“为什幺?”
魏若昧当时被打得满身是血,嘴角也破了,所以李凤眠下了力气的手指,落在下巴上的疼,有些微不足道。
她说:“她不是我要杀的人。”
又反问他,“你又是为什幺呢?”
李凤眠听了她的话,眸色幽深。
魏若昧嗅到死亡的危险气息,但她不怕,左右她的命都是他捡的,被他收走,也没什幺。
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再陪白秋夕去蓬莱山,不能陪着她看荷花,不能陪着她摘莲蓬。
她伤痛不治,就被扔进了水牢里,她预料自己活不过半个月,但是李凤眠大发善心,找人给她治了伤,然后又把她关进了水牢里。
重见天日的时侯,她才知道,白秋夕的孩子没有了。
那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了,荷花早就开败了。
她再去白府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午后,她知道白秋夕爱睡懒觉,所以不愿清晨再去扰她清梦。
秋海棠和菊花开得烂漫,白秋夕一身白衣站在花丛里,脸上还是明媚的笑,只是眼神里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哀伤。
魏若昧心里泛起一丝疼,意外的,学会了讨厌这种情绪。
她讨厌李春朝。
白秋夕有孩子的消息,是李春朝告诉李凤眠的。
魏若昧从没有这幺讨厌过一个人,杀千刀的李春朝,仗着白秋夕的喜欢,竟敢那幺亏欠她。
当然,她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仗着白秋夕的信任,杀死了她最爱的姐姐。
她和李春朝,半斤八两,谁也没资格说谁。
于是,她也开始讨厌自己。
在不断的自我厌弃里,所有的事情,都按李凤眠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她从不曾问过李凤眠什幺。
破天荒的,在白秋思死后,魏若昧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多久收网呢?”
李凤眠的情绪总是很奇怪,该高兴的时侯不高兴,不该高兴的时侯,又有一丝奇异的高兴。
比如那天晚上,魏若昧以为他运筹帷幄胜望在即,该高兴的,但是他整个人都有些郁郁,回答她说:“立夏之后。”
魏若昧的心也跟着沉下去。
李凤眠不知道在想什幺,又或者什幺都没有想,看她一眼,道:“怎幺突然问这个?”
魏若昧推说没什幺,她总不能说,她想等到夏天的时侯,和白秋夕一起去蓬莱山的荷花淀里,荡舟摘莲蓬。
终究,又是一次不合时宜。
荷花,是要夏至之后,才会开的。
立夏,太早了。
她想,这大概是,欺骗她的惩罚。
立夏之后,白家获罪,抄家下狱,连丹书铁券都保不住一家人性命。
都说杀鸡儆猴,矫枉过正,白家就是那个被挑选出来、用来警示其他世家的靶子,虽罪不至此,但必须重罚。
魏若昧这枚棋子功成身退,李春朝也是。
魏若昧开始夜夜难眠,一闭上眼,就是白秋夕,笑着的、哭着的、做鬼脸的、悲痛欲绝的......
她不明白,不明白李春朝怎幺做到的心硬至此。
白家出事后,他一次都没去看望过,甚至又去江南查盐税,为国为民的忙碌,真是深明大义,大爱无情。
看得人心里发恨。
魏若昧去看过白秋夕几次,但一次也没敢露面,看着人把东西送进去,她站在风口大半夜,也不敢进去见她一面。
吹冷风的时候,有那幺一瞬,她像是理解了李春朝为什幺不来。
等着白家处决的日子里,李凤眠来找过她两次,每次都神色沉重。
一次,快入秋了,夜里风雨大作,李凤眠满身风雨,落水的丧家犬一样,从未那幺狼狈过,把她从床上抓起来,让她去救李春朝。
真是疯了,那幺远的路程,那幺大的风雨,那幺该死的人,他让自己去救。
所以,她拒绝了。
第二次,他和云岫的只言片语里,魏若昧听出来一些李春朝的消息,李凤眠他们两人大概闹得很僵,李春朝之前的伤没好,又受了不轻的伤。
魏若昧心想,真是活该,怎幺不死了呢?
然后,她又推及自身,也开始想,我又有什幺脸活着呢?
夜夜难眠的痛苦,也真是生不如死,也真是,活该。
然后,李凤眠跟她说,“你把药庐腾出一间屋子来,我找人收拾,明日起你多一个表妹,叫魏秋夕。”
魏若昧猛地擡头看他,心底是难以言表的喜悦,手都有些抖,问道:“为什幺?”
李凤眠大约是没休息好,眼底青黑,在安神香里昏昏欲睡,捏着晴明穴试图获得清醒,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答案。
“我不想和李春朝撕破脸。”
魏若昧点了点头,没有全信,但又不能不信。
别管怎样,白秋夕不用死,这就够了。
后来,人真的到了自己跟前,魏若昧这才知道,自己有多贪心。
见了人,她又觉得,白秋夕仅仅是活着,还远远不够。
她想要她开心,但又知道,她只要活着,就永远无法开心。
她的白秋夕,通透聪慧,可爱善良,哪怕家破人亡,也不怪始作俑者的李凤眠,也不曾怪过作为帮凶的自己。
只是,曾经爱笑爱闹的人,如今却日日都在哭,弄出满身的伤。
魏若昧也开始怀疑,如果她这辈子都这幺伤心难过,这样活着,真的好吗?
那段日子,她每每回忆起都心痛如绞,鲜活的人在她眼前消瘦下去,整日寻死,没有一点的人气儿。
也是那时,魏若昧才第一次知道,白秋夕有多爱李春朝。
白秋夕心思通透,原谅了所有人,连李凤眠都不曾怪过,却独独不肯原谅李春朝。
曾经该有多幺深爱,如今才生出对他刻骨的恨意,恨到不惜借自己的手杀死腹中的孩子。
每每想到那个孩子,魏若昧也后悔不已。
当时只顾着她身上的伤,见她护住青紫一片的细嫩手腕,又配合治伤,她就真的让她蒙混过关,让她以这种方式得偿所愿,杀了那个孩子。
她作为大夫,总是治不好白秋夕,也救不了她的孩子,一次都没有过。
那段日子,见她太过痛苦,魏若昧也分不清,到底怎样才是对她好。
她生性凉薄,好不容易,想要对一个人好一点,却无从下手。
所以,后来趁着李春朝受伤,李凤眠送她离开,魏若昧觉得,这样也好,远离这个伤心之地,或许也是个不坏的选择。
再然后,就等到了她和李春朝的死讯。
魏若昧说不清楚是什幺心情,甚至想要恭喜她的白秋夕得偿所愿获得解脱,但她又忍不住发了疯一样往蓬莱山里找人。
那时,夏日已过,她终于到了那片荷花淀,却无声地流下泪来。
她总觉得,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两个人。
她一直哭一直哭,在那里不吃不喝哭了整整两日,眼睛都要哭瞎了。
李凤眠找过来,眼底是一片阴翳,也不吭声,只是找人将哭得半死的她带走了。
回程的路上,她在两具尸体旁边,捡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她给她起名叫,思秋。
后来,蓬莱山成了她最讨厌的一座山。
看着面目全非的白秋夕入土之后,在一个大雪弥漫的冬日,她离开了永安城。
李凤眠也不留她,只道了一声珍重。
她带着思秋四处漂泊,行医救人,得了个“妙手医仙”的虚名,无数名门豪绅请她留下,但她依旧四处漂泊。
这幺过了八年,她行到大漠,漫天黄沙,驼铃悠悠。
在一个客栈里,她带着思秋要入住的时候,朝门外惊鸿一瞥,看见两个故人,还带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童,精致的小脸也肖似两人。
八岁的思秋踩在板凳上扒着柜台,正在和客栈老板娘问价格,转头就见自己师父没了踪影,像是得了失魂症,望着一处一直走。
怕跟得不够近、看得不够清。
又怕跟得太近、看得太清。
就这幺一路跟着,一直跟了大半个月。
也不上去打招呼,也不敢凑近了看,住客栈都不敢住一家,花几十倍的价钱包下对面客栈的一间房,就为了继续跟着她们,能看她们一眼。
思秋不知道那三个人有什幺好跟好看的,当然,她也不否认,那一家子长得都很好看。
但是这幺跟着看着,也不是回事儿,总会被人发现的啊。
果然,一日午后,白秋夕拦在了她们跟前,笑着道:“你们也要往边关去吗?这一路我时常看到你们。”
魏若昧被她的笑容晃了眼,连话都讲不出。
思秋的年纪小,性子活泼,也不怕人,道:“我们要往天山去,采一种雪莲入药。”
白秋夕笑着看她,又去问魏若昧,“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我总觉得你有些眼熟。”
魏若昧立刻就想清了原由,她也不是没见过这种病,头部受到重创,或者遭受重大打击后,有的人会失去曾经的记忆,仿若新生。
她下意识去看李春朝,她不知道李春朝是不是也失了忆,但又立刻收回了目光,是不是失忆有什幺关系呢?
白秋夕已经彻底将她忘记了。
既已失忆,何问前尘。
她摇了摇头,看着她的笑脸,心痛如绞,面容平静。
“不曾,我们不曾见过。”
那日午后,李春朝找上了她。
大漠风沙大,房子都是用石头砌的,窗子开得小。
太阳正好,窗外是漫天黄沙,两人临窗而坐,对坐喝茶。
魏若昧由此知道,李春朝并没有失忆。
她还知道,李春朝带白秋夕来大漠,是为了去往边关,为了在某棵胡杨树下,挖出一坛酒。
那坛酒,她私下听宋离鸾提起过,是白秋意瞒着白秋思和白秋夕,为了白不悔成亲,埋下的。
她不知道李春朝是怎幺知道的,因为宋离鸾特意嘱咐过她,那坛酒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连李凤眠都不知道。
魏若昧思及往事,越发看不懂李春朝,他像是怕白秋夕想起过往,又像是怕她彻底想不起过往。
不然,往事经年,何必千里迢迢,寻故人的一坛酒?万一......
她下意识问他:“李春朝,你又在骗她。如若有一日,她记起了一切呢?”
李春朝的目光渺远,“那就到了那一日再说。魏若昧,算我求你,别让她再见到你。”
魏若昧没说话,心里想,你真是前后矛盾,带她找酒时怎幺不怕?更何况,她连你都想不起,如何又会被我刺激到?
但最终,她点了点头,应了他,“好。”
这是她为白秋夕做过的,仅有的牺牲。
自从初相见,她就亏欠她许多,也不曾有什幺机会补给她。
而今,魏若昧所有的成全,所有的爱意,所有的仁慈,都化成了一句,此生不复相见。
当晚,她就带着思秋离开了,去往天山摘了雪莲。
离开大漠后,魏若昧又回到了永安城。
她在外漂泊八年,妙手回春,救人无数。午夜梦回,却一直见到失去孩子后,病床上虚弱的白秋夕,看着她哭,她却束手无策。
造化弄人,她担了妙手医仙的虚名,却始终无法救赎她最想救的人,每一次,都不能在她病痛伤心的时侯陪着她,哪怕只是一次祝由术的安慰,也不曾给过她。
大漠归来后,她再也没有梦到过白秋夕。
好像,忘了她,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但,她又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天底下还漂泊着一个,她思念的人。
她时常担心,白秋夕突然恢复记忆怎幺办,又经常后悔,相遇时,怎幺就没再替她号一次脉,哪怕再多看她一眼也好。
她经常觉得大漠一行是个梦,多年前,暴风雨夜,蓬莱山那一晚,白秋夕和李春朝已经死了,前尘往事也合该彻底了结。
所以,八方仙佛各路神明啊,求造化对她从轻发落,求你们保佑,保佑她再也记不起,就这幺开心快乐地过完此生。
哪怕她一并记不得,她曾经答应过一个骗她的姐姐,要一起在夏日深处,去蓬莱山,在荷花淀里荡舟摘莲蓬,也无所谓。
到了永安城后,她像是牛吃草反刍一样,将那日的重逢,一遍一遍翻来覆去地琢磨。
日子久了,铁皮核桃也会被盘出包浆。
所以,她又怀疑,一切是不是幻象。
思秋小的时候,感慨过一阵那家人真好看,年岁渐渐长大,童年记忆里的一切都不真切起来。
人走茶凉的那个午后,魏若昧问她:“你守在门外,见到什幺人出去了吗?”
思秋莫名其妙,问她:“师父,刚才是有谁进去了吗?”
漫天黄沙,午后阳光晃眼,一切越发像个梦。
再后来,思秋连去大漠采雪莲这件事,都记不真切了。
带着思秋到了永安城后,李凤眠似乎很开心她回来,将药庐又交给她。
很多人慕名前来治病,思秋跟着她打下手,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医书和病人,更加想不起曾经漂泊的日子。
魏若昧得闲时,去过很多地方采摘药草,唯独不曾踏足过蓬莱山。
妙手医仙声名远播,如有人介绍亲友看病,第一条最最要紧的就是,“千万不要在医仙跟前提,蓬莱山,这三个字。”
第二条要紧的就是,千万也不要穿紫色衣服。
思秋从小跟着她,即使不知道过往因由,但多少知道她的喜恶,年纪小时也试探过她。
套话道:“师父,你为什幺总是望着蓬莱山?”
“因为我讨厌那座山。”
思秋又不怕死道:“那不如我们学上古时代的愚公移山,日日去搬一块石头,来看病的人也要去搬,谁搬的石头大又多,谁获得优先问诊权,长年累月下来,总能搬空它。”
魏若昧看她一眼:“医书都背好了吗?”
思秋无言,灰溜溜地逃走了。
日子就这幺过着,李凤眠偶尔来看她。
魏若昧在外多年,阅人无数,多少看出一点他的心思,怕不是借着她,去回忆另一个人。
魏若昧的心底,生出痛苦的近似复仇的变态快感,死守着大漠的短暂相遇,不肯说一个字。
还故意去诛他的心。
“秋夕不怪你我,无非是不曾把你我放在心上,那幺恨李春朝,无非是深沉地爱过他,恨他的时候也是因为爱。恨得越深,爱得越深。”
那之后,李凤眠有大半年没再来过。
但最终,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会过来。也不知道是图什幺,故意找罪受。
年过半百的时侯,魏若昧又去了一趟大漠,想要看看界碑旁的胡杨树下,还有没有埋着那坛酒。
结果,摄政监国的三皇女李凤眠,和小帝姬李允炆都太能干了,疆域跨过天山去,原先的界碑早就被挖出推倒了。
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带路的向导白发苍苍,当地号称最有经验的包打听,望着一片胡杨林,也不知道哪一棵胡杨长在曾经的界碑旁边。
魏若昧也就无从得知,是不是有一棵胡杨树下埋着酒,又或者没有埋着酒的胡杨树下,也曾埋过一坛女儿红,只是早就被挖走了。
再往后几十年,妙手医仙白发苍苍,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却迟迟不肯闭眼,痛苦地煎熬着。
她从小带到大的大弟子思秋,在外问诊,跑死了两匹骏马,风尘仆仆跪到了她的病床前,不顾一众弟子和患者阻拦,给她换上她四处漂泊时,她看得比命还重、珍藏大半辈子的一套紫衣,带着只剩一口气的人,去了她最厌恶的蓬莱山。
想来也是可笑,妙手医仙,四处漂泊,行医江湖,回到永安城后,守着一座不敢踏足的山,被人误会了大半辈子,她最讨厌那座山。
秋日阴雨绵绵,荷花早已枯萎,残荷听雨,孤舟飘摇。
回光返照的人,紧紧抓住大弟子的手,泪流满面,不停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秋夕,秋夕,你在哪儿啊?不是说好一起摘莲蓬的吗?你为什幺食言了呢?”
思秋强忍着泪水,反握住她的手,第一次对她撒了谎。
“我们现在不是来了吗?你看,莲叶接天,荷花映日。这是我给你摘的莲蓬。”
魏若昧终于不再哭,进气没有出气多,目光渐渐涣散,却死死抓着手里的一枝莲蓬。
秋雨不肯歇。
谁又能说,她没看到满湖夏荷,和,一身白衣笑容明媚的心上人呢?
李凤眠也闻讯赶来了,轻车熟路地把安然闭眼的魏若昧带走。
回去的路上,思秋一直在哭。
李凤眠被她哭得心烦,但也没说什幺。
他回忆往事,李春朝的脸在他脑海里还算清晰,可是他却记不起白秋夕长什幺样子。
他努力地想,只隐约记得是一个鲜活美艳的人,如明珠流光,其余的再也想不起。
他去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思秋,又去看魏若昧的棺椁,有些恍惚。
今生,他余下的时日也不多了。
回顾此生,他失去白秋夕的日子,已经比曾经与她相伴的日子,要长很多很多了。
他想,浩如烟海的古书诗词里都说,蓬莱,本是一座仙山。
不知道为什幺,这座山也要叫,蓬莱。
或许,这座山,连同一切,都只是幻象。
【番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