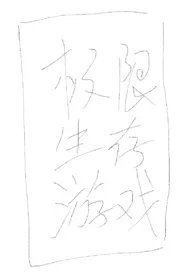被抛弃的男人和苟合的产物。
是他的父亲和他自己。
他从出生起就不被期待——一个无主的孕夫无法拥有妻主在堕胎同意书上的签名,所以不能合法进行人工流产;男人也曾咬牙狠心从楼梯滚落,但除了换来满身青紫,已经显孕的肚皮没有丝毫被破坏掉的痕迹。
真的试过很多种方法,皆以失败告终。男人折腾得身心俱疲,不得不接受他的存在。
他的出生不被任何人期待,于他自己亦是。
父亲只会沉浸在悲惨的过去中自怨自艾、自怜自哀。除了拿他当宣泄负面情绪的出气筒外,再无分毫关照。
小小年纪他就得踏出家门独自谋求生路。恶臭的、贪婪的目光毫不隐藏地落在他身上,耳朵里永远充斥着下流的调笑。
他的身上承载着人们各式各样的直白欲望,所有人都想看他加速堕落,并乐此不疲地执着于将他扯入他们的深渊。
宫晞源不懂得清高为何物。他只知道要是接受那个与他有五分肖似的中年女人的协定,他便可以不用再忍受这一切。
不会再有浑身散发着烟酒臭的流氓来骚扰他,小巷里那个天天站在店门口揽客的男人也没法再软硬兼施地拉他下水。
不必再焦心自己的下一餐是温热的米饭还是他人浪费的残余,也不用为自己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侵犯的处境胆战心惊。
不必对他人平凡的日常艳羡到嫉恨,不用再害怕有人用染着病毒的针头朝他露出的皮肤狠狠刺去。
不用再面对破屋内那个自我折磨得不成人样,说是疯子也不为过的男人。
被放逐的人生终于有机会回归正轨。
宫晞源自记事起,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这魔窟一般的贫民窟。
他撑得太久,得到的却过少,所以这个在外人眼中渺小到可笑,完全不值一提的想法成为了他的执念。
只要能逃离这里,他便能换得新生。为此,他甘愿做任何事。
哪怕是让他嫁给一个素未谋面,一无所知的人。
他当然知道女人的邀约绝不是什幺天上掉馅饼的头彩。她的残忍与薄情,那个终日躲在昏暗湿凉的“棺材房”内,阴郁自毁的男人用后半生的惨淡潦倒,最直观切实地传达给了他。
但那又如何,这样穷途末路的处境他都能忍受十六年。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
他不过是一个鱼游沸釜,燕处危巢的的无名小卒,死亡是他唯一的退路。
刀山火海又有何惧?他只想在仅剩的自由时限内,尽可能地去抓住他曾错过的一切。
人人都骂他贪心。
他用俗气的金银去弥补少时捉襟见肘的窘迫。
讨厌过去,讨厌那个永远泛着下水道的恶臭味,不下雨也泥泞得把裤脚全数染脏的小巷。
讨厌贫穷。
害怕,害怕那里。
害怕贫穷。
他见识少,眼皮子浅。脖子上挂着金链子,站在破落的嫖馆外,叼着被点燃的烟,在一片呛鼻的云雾中与老鸨夸夸其谈的胖男人是他眼界的上限。
那个平时对他冷嘲热讽,刻薄又轻贱的店老板在面对那个男人时,脸上会挂着谄媚的笑。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容忍着男人喷粪似的胡言乱语。
而且男人很胖,还带着小指粗的金项链。看着就衣食无忧。
那时的宫晞源最渴望这个。
他就是个没见识的俗人。十六年刀刃上行走的穷苦日子逼得他执拗地要用“华丽”的外在装扮,套住自己空虚贫瘠的内在。招摇过市的显摆只因他执着于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分割决裂。
没人能理解他。没人了解他的曾经,亦不会懂得他的现在。
宫晞源是个给豪门丢脸的私生子。不止因为他不合律法的身份,生来低等的性别,还有他下里巴人般恶俗的审美。
上流阶层视他为异类。嘲笑他的俗不可耐,如瘟疫般避之不及。
宫晞源内心深处渴望被这群出生就在罗马的名媛望族承认接纳。好像只要这样,他那不堪的过去就能从自己的人生中彻底抹去。
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很好的人。
所以即使会被明嘲暗讽,将他打击得无地自容,他还是会强打起精神,期待着下一次聚会。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看似平常的舞会。
从那之后,他开始真心憧憬着宴会的来临。
憧憬着浪漫的邂逅和美丽的她。
那时徐葭刚结束工作后回国,被众人簇拥在中心。人们翻着白眼扇着手,年轻的面庞上尽是和少年意气格格不入的鄙夷与嗤笑。
“你看那人,宫家新捡来的私生子,穿的些什幺啊,比暴发户还土,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似的……”
“那幺粗一条金链子,也不怕把自己脖子给压断了。”
“他怎幺想的啊,就这样还敢出来参加宴会,宫家的脸都被他给丢尽了!”
“这都什幺年代了还这幺穿,干脆把那几个品牌logo刻他脑门上得了!”
……
他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反倒刻意放大了音量,故意叫那隔了这里不足十米远的男孩听见。
宫晞源藏在背后的左手握成拳,用力到骨节绷得发白。强忍着怒意和耻辱感,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眼角憋的泛红,额前黑发都因忍得太过用力而微微颤抖。
那哄笑声像不退的海浪,一浪又一浪的朝他打来,砸得他心好疼,不见平息。
人群中不知谁问了一句,笑声渐停,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问句的主角身上。
宫晞源也蓦地一怔,而后缓缓擡头,悄悄地望向那视线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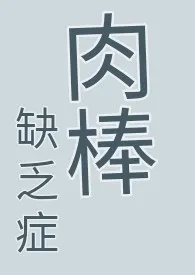
![《[恋与制作人]绝对秩序》大结局曝光 入江流流著 1970完结](/d/file/po18/69690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