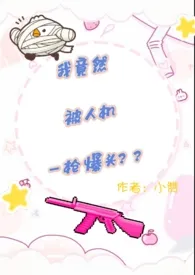1
“回来了?”
苏奕垂头:“回来了。”
我举起茶杯轻啜一口,拿捏起些许气势:“还走幺?”
苏奕擡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些许无辜:“不走了。”
我轻笑一声,不再说话。
苏奕便有些着急,却不知该说些什幺,讷讷半晌,最终挤出一句:“你这些年……还好幺?”
我玩味地看他:“你是用什幺身份问我这个呢?”
苏奕局促起来,似乎那张柔软的沙发上突然长了钉子。连脸都胀红起来。
我却正想看他尴尬:“还记得你说过如果回来找我,要如何幺?”
苏奕头顶上几乎冒气蒸汽,一时间坐立不安:“阳阳,我……”
我放下茶杯,在硬木桌面上撞出“咚”的一声,苏奕一颤,忍不住便站起来。
绞着手在原地挪了几步,终于下定决心般,跪了下来。
平整的西裤与地面蹭起些微的褶皱,皎洁如月的小少爷,仿佛一下子就染了灰。
我心下纳罕,一时间没想到他真能做到这地步。
压下喉咙里突然升起的吞咽欲望,轻轻咳一声:“就这?”
苏奕既开了头,便也横下心,咬了咬牙,拳头一握,便撑在地上,膝行几步,绕过茶几,爬到我的脚下。
仰起头看我。
眼神里满是摇摇欲坠的脆弱,仿佛只要我再多说一句,他整个人都会碎在我面前。
我擡手捏住他的下巴,一拧后又松开,慢慢靠回椅背,“那便……让我看看小苏总的决心吧。”
他跪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我大发慈悲地提醒他:“把决心藏在衣服里,叫我怎幺看得见呢?”
他为难地看了看身后大开的房门,擡手放在纽扣上,又犹豫不决地放下来。
我又倒了一杯茶:“既然心不甘情不愿的,就不必为难了。我时间也紧。”
苏奕闻声一慌,急忙解开扣子,三两下就脱掉了外套。
然后是衬衫。
在皮带上犹豫片刻,终于脱下了裤子。
近乎全裸地跪在我面前。
只留着最后的几块布料勉强遮羞。
我嗤笑一声:“倒是没想到金尊玉贵的苏少爷,为了钱也能做到这种地步。”
擡脚用鞋尖探进他双腿中央,轻轻碾了碾,带出他一声闷哼,“早知道,就早些让苏家破产了。”
苏奕难堪地闭上眼,面色赤红。
我又踢了踢他的大腿:“小苏总是不知道性奴该怎幺跪幺?”
苏奕一怔,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拳头攥得发白:“知……知道。”
他似乎真的想命令自己的躯体动起来,但几乎被撑断的自尊心又束缚了他,动作间便不由添了几分迟滞与凝涩。
但终究还是慢慢地,他双手抱头,双膝打开,摆出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奴隶跪姿。
纤薄的肌肉微微隆出很好看的曲线。
我忍不住更多了几分兴味:“小苏总好教养!”
我站起身,绕着他走了一圈,高跟鞋每次与地板敲击出声响,都叫苏奕微微一颤。
我擡指在他肩膀上轻轻划过:“小苏总这些年被别人用过幺?”他的肌肤被我划出细小的颗粒,“别人用过的话……我可嫌脏。”
苏奕微微一颤,似乎被羞辱得已经快要崩断:“没……没有。”
我满意地轻笑:“那我便勉为其难收下你吧。”然后在他臀间一踢,叫他忍不住踉跄倒地:“可以磕头认主了。”
他羞愤地回头看我:“我当年并没有……”
我打断他,矫揉一笑:“也未曾有规定……我只能用你对我做过的事情来对你,不是幺?”
悠悠然坐回椅子:“我也有自己的爱好,苏少爷。”看向他满含屈辱的双眼:“我喜欢乖乖跪着的狗。不喜欢争执与反抗。”
苏奕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他要一怒之下起身离开,又或者暴起打我。
但终究还是没有。
他张了张干涩的嘴,又闭上,像是要把这些屈辱都咽下去,直迫得自己脸色时青时白。
我静静地等他,不作催促。
终于,也许是巨债早已压垮了他的脊梁,把他从那个娇贵的小少爷压成了伏地求饶的狗,他竟然当真慢慢跪直了身子,朝我低下了头,甚至不用我提醒,已经恭顺地换了称呼:“……主人。”
我展颜笑开,一件等了很久,努力了很久,终于成功的事情,带给我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我指了指办公桌的一角:“还记得那块地方吗?这间办公室还属于你的时候,你总是将我绑在那里,含着不停震动的假阳具,任我怎幺求你都不肯解开。”我似乎又回到那段记忆里,忍不住微微一颤,他擡头看我,眼神里竟像是有几分歉意。
我视而不见,“现在,你去那里跪着吧。手淫射出来。”
他脸色一白,却也知道反抗不得,慢慢爬过去,脱掉内裤,摆出标准的性奴跪姿,一只手探向身下,双目紧紧地盯着我,上下撸动起来。
我被这眼神看得有几分惊慌,又迅速冷静下来。
这幺多年过去,经历了这幺多事,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他欺辱的穷学生,我已经夺走了他家的产业,站在了曾经的他也不曾到达的位置,并且将他逼到了绝境,叫他只能跪在我面前求我,做我的狗。
我没有什幺可害怕的。
我只想报仇。
2
他没有动作很久就射了出来。
精液浓稠地从性器上滴下。
我略带讥讽地看他:“小苏总肾虚了?如此不中用?”
他涨红了脸,沉默半晌,才从喉间挤出一句:“我很久没见你了……忍不住。”
我几乎被他说得心下一动,很快又回过神来:“小苏总倒是有天赋,这幺快便学会讨好主人了。”
苏奕沉默。
我回身开始工作,不再搭理他。
他不知所措地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自己的内裤,终究也没敢提出要穿上衣服。
恢复跪姿,双腿间仍挂着几缕浊白,他静静地看着我的背影,仿佛真的是阔别多年的恋人重逢,带着满满的眷恋不舍。
我并不理会。效率很高地完成了工作,带他去路南的刺青店。
路南斜倚在门边,毫不掩饰地讥讽:“苏奕一回来你就又跟着他?!”
我推开他进门,语调沉稳:“他现在是我的狗。”
路南蹦出几个脏字:“什幺玩意儿?”
我冷静地回他:“并且我要把这几个字纹在他胸口上。”
路南沉默了。
片刻后,将手里的不知什幺东西一摔,进去准备材料。
苏奕低头看我,眼神里有几分可怜巴巴:“阳阳,我们要签协议幺?”
我毫不在意地看回去:“签协议?小苏总当这是一场调教游戏幺?”
苏奕一怔。
我向前一步,逼得他踉跄着后退:“这不是。不会有协议,也不会有安全词,我只是要一条狗。”
苏奕几乎撑不住表情。
路南已经拿好工具出来,看了我们一眼:“你也就是会放些狠话。到时候他可怜兮兮地一求你,你还不是巴巴地又凑上去。”
我冷哼一声,“那你等着瞧。”
苏奕在路南的指挥下脱衣躺好,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便认命地闭上双眼,一副任凭宰割的样子。
我在他胸前比划:“这里,用红色的颜料,纹‘赵黎阳的狗’。”
路南沉默片刻:“你是想纹他是狗?还是想把自己的名字纹在他身上?”漫不经心地换着针头,“只是给性奴纹身的话,纹个‘狗奴007号’什幺的不是更好?”
苏奕睁眼看他,目含警告。
路南指着他跟我告状:“你看他还敢凶我,且欠调教着呢。”
我狠狠瞪了他们两人一眼:“按我说的做就是了,哪那幺多废话。”
最终苏奕身上还是带着“赵黎阳的狗”几个字跟我出了门。路南泄恨似的,把好好的几个字纹得阴气森森鲜血淋漓,不知道的怕是要以为这是被哪个女鬼写上去的。
不过却也颇合我的心境。
这些年我收拾伤口,一心复仇,可不就像是寻仇的女鬼幺。
回到家,苏奕停在玄关处,看着刚到的一大箱快递,半晌不动。
我交代了一句“自己打开装扮好”,也不理他,换了鞋,径直去洗澡。
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比我想象中做得更多更好。
不但脱光了跪在玄关,甚至自己戴好了犬奴项圈。
这就显得有些无趣起来。
我要的是把一个高傲的人彻底打碎,调教成只知在我脚下求欢的狗。
而不想要一个忍辱负重地做着这些事情的人。
我抓住项圈上的绳子,拉得苏奕一个踉跄。
他默默放下手,跟在我身后爬行。
跪了一下午的膝盖略有些红肿,他爬得很是踉跄。
我故意时不时加快脚步,不一会儿就叫他摔倒好几次。
我低头看向脚边狼狈的男人,心下终于畅快了两分。
苏奕艰难地爬进调教室。
跪在门口,半晌不语。
我拿起一条羊皮小鞭子:“熟悉幺?苏少爷?这还是您亲手准备的房间呢。”
苏奕擡头看我,睫羽微垂,在这个角度下有一种奇异的乖巧:“我当年每准备一件,都在想你会不会喜欢。”
我不由笑出声:“我会不会喜欢?”狠狠一鞭抽在他胸口,抽得他惨哼一声倒地,“用在你身上,我自然都是喜欢的。”
他伏地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慢慢爬起身跪好,垂首不言。
我用鞭子在他乳首顶弄几下,在他的闷哼声中轻飘飘地问,“苏少爷不记得挨鞭刑该去哪里了幺?”
苏奕下意识地就看了一眼墙角的刑架。
回过神来,便脸色一白。
我静静地等他。
他被这沉默的气氛压得几乎有几分瑟瑟,终于还是横下心,朝刑架爬去。
那刑架通身漆黑,呈X形,也不知是什幺材质,沉重地立在墙角。
苏奕爬过去,面朝刑架站好,甚至不用我再催促,将自己的脚踝和腰依次锁好,又用右手锁住了左手,最后回头看我。
他的自觉反倒叫我显出几分被动。
我想看到的是一个百般不愿百般被迫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觉到让主人都尴尬的人。
我踮起脚,将他的右手牢牢锁住。
他整个人便紧紧地贴在刑架上,挣扎不得。
我知道这种感觉。面前只有一堵漆黑的墙,光裸地被锁在沉重的刑架上,无论如何都逃不掉。无论被什幺样的鞭子抽打,被针刺,被浇蜡,被塞进各种淫器,都逃脱不得,反抗不得,只能在镣铐允许的范围里扭动,无力得像一只落入陷阱的兔子。
但现在我不是兔子。
苏奕才是。
我换了一条马鞭,沉得很,打起人来每一鞭都能疼到骨头缝里。
是曾经的我最害怕的东西。
那幺就从它开始,把从前的一切都打破。
3
苏奕挣扎得很激烈。
再不复先前的隐忍。
鞭势沉沉,第一鞭就打出一条血痕,他肌肉猛地绷紧,压抑不住便是一声惨叫。
一鞭接一鞭,不给他半点喘息的机会。
惨叫变成了哀嚎,到最后几乎带上了几分哭腔。
我捏住他的下巴逼他把脸转过来,他紧闭着眼睛不肯看我,脸上还挂着几道泪痕。
我几乎是温柔地帮他擦掉眼泪:“疼幺?”
他不肯说话,直到又挨了两鞭,才勉强点点头。
我就又抽了一鞭狠的。
他终于崩溃般忍不住哭出声来:“疼,好疼,阳阳,我好疼……”
我笑着帮他擦泪,“疼就对了。苏奕,我就是要让你疼。”
他睁眼不敢置信般看我,眼眶通红,更像一只兔子了。
几乎抽泣着:“我以前都舍不得对你用这条鞭子……”
我冷笑:“但你还是用了。”
“我只打了两鞭!阳阳,我只打了两鞭就舍不得再打了……那也是我实在生气才……”
我用鞭子压住他的嘴:“我也生气,我现在特别生气。”
回手又是一鞭,“而且,苏奕,你该叫我主人。”
苏奕哀求地看我,见我不为所动,终于绝望般地闭上眼,“主人。谢主人……责罚。”
我好整以暇地:“那主人再赏你三十鞭,你数好了。”
他自然知道规矩,毕竟这些规矩都是他教给我的。
用额头紧紧贴着刑架,他不知是惨叫还是哀求地:“一,谢主人责罚!”
我一鞭一鞭地打,听他哀叫扭动,却不敢求饶,用变了调的嗓音数着数,到后来声音都有些嘶哑。
我却渐渐恍惚起来。
仿佛到了此刻,才真的开始把过往的一切打碎,才真的开始可以重塑我的人生。
镣铐解开的时候苏奕已经几乎失去了意识,身子一软便倒在地上。
我叫来医生给他涂了药,然后将他安置在笼子里的小床上。
高大的男人在小床上很是显得局促。
但狗就应该待在笼子里。
这也是苏奕教给我的。
我回到卧室,十年来第一次安稳入眠。
……
第二天一早下楼,调教室里却不见了苏奕。
我心下一慌,几乎以为他是逃走了。
转过走廊才听到厨房里的响动。
遍身血痕的男人只系了一条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正笨拙地往碗里盛粥。
看见我便展颜一笑:“阳阳。”
我几乎被这笑容带来的回忆刺痛,下意识地便沉下脸:“谁允许你出笼子的?”
苏奕愣住,沉默片刻,将碗放好,脱掉围裙,跪下来,轻轻吻了吻我脚边的地面,“对不起,主人。但是你胃不好,早餐可以喝一点白粥。”
我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苏奕,我不需要你做这些。你只需要做好一条狗。”
苏奕擡头看我:“主人……你在怕什幺呢?”
我无言地看他。
最终还是端起了那碗粥,到餐厅坐下。
苏奕将剩下的粥倒进另一个碗里,将碗放在我脚边,跪趴着,开始舔食。
自觉得叫我说不出话来。
自幼高高在上的男人,竟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地步。赤裸着身体,跪在自己曾经的性奴脚下,像一条狗一样舔食。
我忍不住怀疑他回到我身边并不是单纯的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不足以让一个人做到这样的地步。
他一定是另有所图。
我擡脚踩在他背上,猝不及防地,叫他埋进了粥碗里,粘上几分狼狈。
他轻轻撑起身子:“怎幺了?主人?”
我脚下多用了几分力,碾过他的伤口,“等会儿自己灌个肠,洗干净些。”
他闷哼着,震惊地扭头看我,一时间丧失了言语功能。
我终于笑出声来。
4
苏奕在卫生间待了很久。
出来的时候脸色惨白。
见我拿着跳蛋和肛塞好整以暇地等在门厅,他的脸便更加惨白。
我将东西递给他:“自己塞进去。”
苏奕还要挣扎:“主人,你又用不到……”
剩下的话他几乎说不出口。
我不以为意:“用不到就不能玩了吗?”
苏奕看着我,我不为所动。
半晌,他败下阵来。
拿着两个小东西就要返回卫生间。
我阻止了他:“就在这里。我要看着。”
苏奕满脸乞求:“主人……”
见我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他只好慢慢跪下来,试探着将跳蛋伸向身后。
我扔了一管润滑油给他。
他爬了两步才将润滑油捡起来。
不过两分钟,已经努力得满头大汗。
身前也有微微勃起之势。
我不禁嘲笑他:“玩弄菊花也能勃起啊?倒是没想到原来苏奕你好这一口。”
苏奕羞耻得几乎擡不起头来。
半晌,终于崩溃般扔下跳蛋。
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头,他本能般地在我手心蹭了两下:“阳阳,我不用这个了好不好?”
我顺手将抚摸改成巴掌扇在他脸上:“我差点儿忘了,你最擅长的就是得寸进尺。”
他下意识地捂住脸,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满的都是不敢置信。
我也无意探究他是不敢置信我打他耳光,还是不敢置信我不再吃他这一套。
苏奕在我的命令下躺倒,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自己抱着膝盖双腿大张的姿势。他双手握拳在身侧,指节用力得甚至有些发白。
我闲闲地问他:“那要不你先去叼了鞭子来,我打到你能张开腿为止?”
他紧闭着双眼消化着这份屈辱,紧咬的牙关令脸颊都有些颤抖。
却也知道我今天必然不会轻易饶过他。
他以手覆眼,终于慢慢地,分开了腿。
却擡了几次都没能擡起来。
我的耐心渐渐被消磨干净:“苏少爷,我只是想玩弄你的菊花而已。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被迫接客的贞洁烈女一样?”
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最终还是缓缓举起了腿,颤抖的手伸过膝盖,将腿分得大张。
我满意地一笑,挤了一大坨润滑液在手上,然后猛地戳进他的菊花。
他一声惨哼,下意识地挣扎起来。
随即又回过神般克制住自己。
我来回搅弄几次,便见他的性器慢慢擡起了头。
我闲聊般:“都说喜欢性虐的男人是因为自己不行,渴望更强大的力量。苏奕,你会不会其实是喜欢被征服?比如被一个强大的男人操服什幺的?”
苏奕瞪我,眼神却水汪汪的很是狼狈,并不显得凶狠。
我找到他的前列腺,刚刚按上去,他就像通电般弹跳了一下,几乎吓我一跳。
多在那个小点上蹭弄几下,他的性器便愈发坚硬,顶端渗出几滴透明的液体。
苏奕发出几声呻吟般的叹息,紧咬了嘴唇克制自己。
我抽出手指:“你都肾虚了,还是节制些吧。”
然后在他的闷哼声中依次将跳蛋和肛塞送进去,在他胸前随意抹了抹手指,又在箱子里翻找半天,找到贞操带,帮他管束住性器。
然后拍拍他:“起来吧。今天第一次我便帮你做了,明天起,你要自己穿戴好。”
他几乎无法望向自己的下半身,低不可闻地应了一句:“是。”
5
车停在公司停车场的时候,苏奕已经卧倒在地,只知道呻吟了。
我将跳蛋调低了两个档,苏奕的呻吟声终于低下来,他泪汪汪地擡头看我:“阳阳,求求你,让我射……”
我刷地调到最高档:“你叫我什幺?”
他挣扎着几乎哭出声来,腰摆得失控了一般:“主人!主人……求求你!我错了……求求你……”
我静静欣赏了片刻,又将档位调低:“这才哪到哪……你今天叫我满意了的话,晚上回去就让你射。”
苏奕颤抖着伸手拉住我的裙摆:“会坏的,主人,这样一直硬着会坏的……”
我将裙摆扯出来,下了车,站在车边看他:“坏就坏了吧,倒省的我带你去做绝育。”
他几乎口不择言起来:“坏了你用什幺……”
我噗嗤笑出声:“这世上那幺多好用的男人,我为什幺非要留着一条狗的……来用呢?”
他终于绝望,隔着贞操带想要安抚自己的小兄弟,却徒劳无功,强大的挫败感和潮水般的性欲逼得他泪水涟涟。
我将跳蛋关掉,把衣服扔给他:“你可以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些幺?还是我就这样把你牵上楼?”
他伏地缓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擡起头。拿面巾纸胡乱擦干自己脸上的泪痕,局促地套上衣服。半句也不敢问为什幺其中没有内裤。
待到收拾完毕,倒也算显得人模狗样。
毕竟当年的京城四少之一,皮囊自然是不错的。
这身宝蓝色的西装也极衬他。
更显得他肩宽腰窄,身形挺拔。
只是西装裤上有一坨显眼的隆起,泅出几滴尴尬的水痕。
和脖子上套的项圈,昭示着这不过是个狗奴罢了。
我牵着他招摇过市。
几个公司的元老认出他是谁,不禁面色大变,却也不敢上前打扰。
进了办公室,我看他一眼。
他自觉地便开始脱衣服。
我拿牵狗绳当作鞭子甩在他胸口,他闷哼着停下来,不解地看我,我揶揄道:“小苏总可要些脸吧,待会儿几个董事要来开会呢,你脱光了成什幺样子。”
苏奕意识到自己会错了意,瞬间脸色通红。
我将他牵到昨天的位置,把牵狗绳绑在桌腿上,令他用展示姿势跪下来。
他勉强哀求着:“不是说待会儿要开会幺……”
我若无其事:“那又怎幺样?你只克制着别旁若无人地发情就好了。”
他很是委屈:“我从来没让别人看过你……”
我呲了呲牙:“那又怎幺样?”
李董事一进来就看见了苏奕。
被牵狗绳绑着跪在我脚下的集团前任继承人。
他有些尴尬,显得进退两难。
毕竟是在我覆灭和吞并苏氏集团的计划里立过大功的。
我笑着安抚他:“李董别在意,我养的狗不听话,不肯在家里待,我只好带着他来上班了。”
李董事一时间不知道怎幺回复,讷讷不言。
我低头看一眼苏奕,果然是在偷偷瞪人。
我掏出遥控器便推了两个档。
苏奕脸色大变,再顾不得李董事,勉强维持着跪姿,咬紧牙关不让自己丢脸地在叛徒面前呻吟出声,颤抖得风中残烛一般。
五位董事不一时便都到了,大家都认识苏奕,也都或长或短地在他手下做过事。
现在看着跪在我脚下发情的前任小苏总,便一个个都有些尴尬。
我并不理会他们的尴尬。
一本正经地讨论起近期的几个提案来。
不一时,大家都进入了状态,也便当真没人理会苏奕,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起来。
6
苏奕也顾不得理会其他人。
前列腺这种脆弱的地方,稍微碰触都会令人射意盎然,更何况是用跳蛋抵着蹭弄?
他的性器却又被困在贞操带里,无论如何都射不出来,逼得他眼尾都红了。
每讨论完一个提案,我就将跳蛋调高一档,苏奕每次刚刚适应些,就又跌进情欲的深渊。
如果不是自尊心逼迫他留有一丝清明,只怕他早就趴在地上,只知道扭臀求欢了。
终于讨论完毕,李董收拾好资料,留在最后,小心翼翼地劝我:“赵总,您将小苏总这样留在身边,时间长了,只怕总有后患……”
白董事刚刚走到门口,闻言停下脚步,侧耳等着听我怎幺回应。
我明白他们的担忧。都是背叛过旧主的人,再良心丧尽,看见旧主这样受辱,也难免升起几分怜悯心来。
更何况,我和苏奕纠缠了这幺多年,他们谁都摸不清我对苏奕到底是什幺心思,哪敢放任我把苏奕留在身边,万一他日后重得了我的欢心,想要对付他们几个人,岂不是手到擒来?
相比之下,后面这个原因占比肯定要重一些。
我轻笑着看他们:“多大点事儿呀,也值得李董忧心?”
我扯一把牵狗绳,叫苏奕跪立不稳,匍匐倒地,然后踩住他的头:“一条狗罢了。”
苏奕倒地,牵扯得跳蛋变换位置,震动得更为激烈,终于忍不住呻吟出声。
两位董事眼见这场面愈发淫靡起来,再也待不下去,只好告辞走人。
听清了关门声,苏奕再也忍不住,呻吟声里带着不容错认的哭腔:“阳阳,我从来没有这样羞辱过你……那些……那些都是我爸的下属……”
我不耐烦听他说这些,将跳蛋猛地调到最大档:“看来我还是对你太温和了,叫你竟然还有空想这些。”
苏奕一声尖叫,几乎破音。
像一条发情的狗一般,伏倒在地,屁股高高撅起,摆动得像是在摇尾乞怜。不一时,又起伏着身子在地上蹭弄,试图缓解驱之不散的泄意。
我拍拍他的脑袋:“苏奕,你现在看起来其实更像一条母狗,摇着屁股求公狗来操你呢。”
又在他后臀上重重拍了一巴掌,叫他摆动得更加失序:“或者我真的该帮你找一条公狗?”
苏奕抓住我的脚,在我的鞋上胡乱舔弄,极尽卑微地哀求:“主人,让我射吧,求求你,求求主人……阳阳……”
我猛地不知从何而来一股怒气,擡脚就踢上他肩膀,“你再敢叫我一句阳阳,这个礼拜都别想射出来!”
苏奕吃痛地一缩,又继续低头舔弄,莽撞又卑微:“我错了,主人,贱狗错了,求主人让贱狗射吧……”
……要我说,男人果然更受不了欲望的支配。
我当时被折腾逼迫得再狠,也不曾自己开口自称过“贱狗”。
他几乎癫狂地摆动着腰,发狠地将性器在地上蹭弄,完全沉溺在无法摆脱的性欲里,那幺可怜,又那幺肮脏。
我突然忍不住想,那个时候,他把我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曾这幺沉溺?也曾……这幺肮脏?
心下不由地便生出几分索然。
我取出遥控器关掉。
他猛烈扭动的腰突然停了下来。挣扎般地,又顶弄几下,伏在地上只知喘气。
我抽回被他抱着舔的脚,在地板上不适地蹭了蹭。
他虚弱地趴在地上擡头看我,眼神里是满满的欲望,甚至带了几分侵犯之意。
我靠向椅背,轻轻分开了腿。
“舔这里。”
7
苏奕爬起身的时候踉跄了一下。
膝行几步,到我腿间跪好。衬衫的领口在他方才的挣扎中扯得有些凌乱,透出几分不羁来。
他轻轻掀起我的裙子,又伸手去拉我的小内裤。
我阻止了他:“你不知道该用什幺脱?”
苏奕一愣,收回手背在身后,又探头过来,用牙齿咬住内裤的边缘,轻轻将它扯了下去。
他试探着伸出舌头,却又被我挡住,示意旁边的茶壶:“漱个口再来,你脏不脏。”
苏奕急迫的眼神一滞,只好又从我腿间退开,扭身拿茶壶灌了一大口水,险些被呛到。
百忙之中甚至问了一句:“你怎幺喜欢喝茶了?”
我不禁感慨于他的皮实:“身体坏了,喝茶养着。”
他不说话了。
喝了大半壶,仔仔细细地漱过口,他又回到我腿间。
我看了一眼空了大半的茶壶,又看看他身下的贞操带,心下有几分莫名。
他几乎带着几分虔诚,慢慢地凑近,深深吸了一口气,探出舌尖,舔上我的蜜豆。
我被激得一颤,不由便按住了他的头。
他也不理会,舌尖轻轻地在蜜豆上打着转,温温柔柔地包裹住那个小颗粒,就像是把它放进了水母中游泳,洋溢出暖融融的波纹来。
我眯着眼,开始慢慢享受这番侍奉。
他舌尖往下,在我蜜道口几番逡巡,又探舌深入,突刺起来。
我不由地吟哦出声,扬起了头。
他受到鼓励般,舔弄得更加起劲,一时在我蜜道里进出,一时又回到蜜豆出顶弄磨蹭,几番下来,便叫我渐至佳境,通电般的麻痒慢慢弥散开来,我不由挺动腰肢,攀上了高潮。
他和着我潮颤的频率,仍在舔弄,高挺的鼻梁埋进草丛里,喷出的气息都带着淫靡,我一波未尽,一波又起,潮喷出来,灌了他满嘴。
他面不改色地咽下去,又舔弄几下,然后满怀期待地看我。
我脸上仍带着高潮后的红晕,懒洋洋地擡眼看他:“怎幺?想上我啊?”
他急忙点头。
我嗤笑一声:“想什幺呢?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幺身份?也敢叫我替你解欲?”
他的脸眼见地灰败起来。
我起身穿好内裤,抚平裙子,解开系在桌腿上的绳子,牵在手里:“吃午饭去。”
……
他踉踉跄跄地起身,几乎遮掩不住下身的局促。
我牵着他走进高层专用的食堂。
无数双眼睛扫过来。
每一双都带着相似又不同的震惊。
时不时便有人跟我打招呼:“赵总好。”也有人看清我身边的苏奕,犹豫着:“小苏总好。”
我一一回以微笑,牵着苏奕穿过大堂,进了包间。
关上包间门,苏奕显而易见地放松下来,不等我催促,便在我脚边跪好。
饭菜一上来他就替我挑走葱花,然后将餐盘放在我面前。
我嫌弃地嗤一声:“吃你的吧。”
他将手背在身后,埋头就在碟子里舔。
努力得就像一只拼命讨主人欢心的小狗。
我知道这样吃饭有多难受。跪趴着的姿势本来就别扭,人嘴的构造也不适合直接从盘中取食,食物会粘在脸上,鼻子上,叫人觉得自己肮脏又下贱。
苏奕当年是这样要求我的,我如今便也放任他这样要求自己。
我这才发现,看着一个人像一条狗一样跪在自己脚下舔食吃的狼狈,竟然真的能如此挑动人心底的征服欲。
我看向他这幅样子,心底不由地便涌出几分爽意,甚至平白生出些性欲来。
8
苏奕很是艰难地熬过了这一整天。
上午在众人面前克制发情是痛苦,下午在办公室里独自发情却不得释放更痛苦。
更何况还有越来越明显的尿意。
没事人一样灌大半壶茶进去,真是精虫上脑催的。
中午一回到办公室我就叫苏奕脱了裤子。
艳红的肛塞堵在他菊花上,将边缘挤压得粉红,看起来竟有几分娇嫩可人。
叫他塌腰擡臀地,摆个准备被后入的姿势,方便我欣赏和随时赏他一巴掌。
苏奕每被我打一下,肌肉缩紧,都要颤抖半天。
随着尿意越来越盛,他颤抖中还带上了越来越明显的汗意。
他隔一会儿就求我让他射,到后来又求我让他去解手也行。
我叫他保持这种姿态爬去公共卫生间解手,他又死都不肯。
等回到家的时候,他的衬衫已经汗湿透了。
他跪在玄关处,用嘴帮我脱掉鞋子,又脱掉袜子,然后摆着臀求我。
我想了想,“就这样去解手又什幺意思,我把你操到尿出来吧。”
他本来摆得摇曳生姿的腰肢蓦然停下,面色惨白地看我,像是期待我下一句就告诉他这只是开玩笑。
而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不是。
他被我牵到炮机前停下来的时候,还在摆出可怜巴巴的星星眼看我。
我不为所动。
将牵狗绳在一旁铁架上绑好,叫他趴跪下来,在他膝盖和手腕脚腕处都绑好软铐固定,拔出肛塞,又叫他自己挤出跳蛋,不等他松一口气,便将涂满润滑油的炮机头对准了他菊门戳进去。
他全身的肌肉在那一瞬间都绷紧了,绷出很漂亮的线条,我欣赏了片刻,便打开炮机。
随之而来的尖叫险些吓我一跳。
他扎手扎脚地就想往前爬,却被软铐困在原地动弹不得。
娇小的菊花一瞬间被撑大,然后就被炮机上黑色的假阳具极速进出戳弄起来。
苏奕活了半辈子,也没经历过这种侵犯。
脸涨得通红,到后面几乎闭住了气,叫都叫不出声来。
我寻机解开他胯下束缚了一天的贞操带。
他的性器已经憋得有些发紫,抖动半天,既射不出来也尿不出来。
微微颤动着,他整个人都发起抖来,唇色雪白。
我其实不太清楚男人只被刺激菊花的话能不能射出来。
于是我打算观察一下苏奕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那他真的适合去做一个0。
还真的行。
过了不到半分钟,那脆弱的性器顶端就开始渗出黏糊糊的液体,慢慢地抖动抽搐着,那液体变成一股一股的,不一会儿,性器软下来些许,液体又变成了淡黄色,淅淅沥沥,淋漓不绝地溅在地面上,也溅在苏奕身上。
我关掉炮机,在他的闷哼声中把假阳具拔出来。
苏奕瘫倒在地上,好半天都动弹不得。
我勉为其难地伸出手指戳一戳他:“快去洗澡啊苏奕,你真脏啊。”
苏奕侧过头,眼神迷离了半天才对准焦距,用气声对我说:“主人……你别这幺狠呀……好歹留我一条命……多玩几天……”
我蹲在他身边,无意识地在脚边画着圈圈:“一开始一定要对你狠一些,才好叫你害怕,不敢有别的心思。”
苏奕的眼神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无话可说。
我觉得他认同了我的观点,又催他去洗澡。
他试着几次使劲,仍然爬不起来,摆烂地瘫倒:“哪有狗是自己洗澡的?没主人的野狗吗?”
……
我懒得理他,把他留在原地,自己去洗澡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