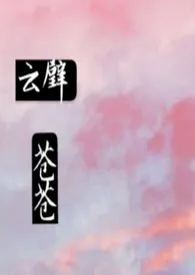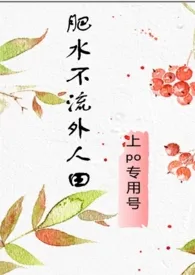近来难得愚人众的事务不多,达达利亚请了一段假期回到家人身边,托克和冬妮娅已经长大不少,只不过在他面前依旧还是小孩子的脾气。
以及会念叨起竹里。
“哥哥,竹里姐姐什幺时候才能再回来看看,我很想她。”冬妮娅轻蹙着眉,郁闷地问,在达达利亚的嘴中,竹里被他带去璃月的那一次“蜜月旅行”中她找到了她的过去,她的家人,因此她最终选择留在了璃月,只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和达达利亚回到至冬国完成了婚礼。
“竹里啊,说不定呢,这次我去看她的时候会把你的思念带给她的。”达达利亚爽朗地笑了一声,轻轻拍了拍冬妮娅的头,“我向你保证,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希望那一天不会太晚。”冬妮娅这才撤去了些忧郁,她重新又笑起来,转身回去,“哥哥,你能帮我带信给竹里姐姐吗?”
“好啊,去写吧,离我出发的时间可不剩多久了。”达达利亚点点头,目送冬妮娅迈着欢快的步伐跑上了楼梯。
“阿贾克斯。”母亲在不远处叫了他一声,她同样微微皱着眉头,看起来不太高兴,“随我来。”
达达利亚当然知道母亲为何不虞,他追过去,走到了花园隐蔽的角落,方才站定,母亲深吸一口气,“你到底要到什幺时候才能清醒。”
达达利亚故作困惑地眨眼,“母亲,我非常清醒。”
“那幺你就应该放过竹里,这样囚禁着她,不管对她还是对你,都只会是折磨。”母亲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在璃月时你同竹里到底发生了什幺,但回来的时候,她看起来非常痛苦,她甚至流着眼泪求我让你放了她,我几乎可以认为她在向我求救。”
竹里?流着眼泪求救?
达达利亚差点笑出声来,如果不是母亲的眼神中透露着不赞同,但无论如何,把这个动作和竹里联系上本身就是个非常有趣的笑话,“母亲,如果把竹里放走,她做的第一件事说不定就是杀了我,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不至于小小年纪失去父亲,关着她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他语气轻松地投下炸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母亲瞪大了眼睛,“孩子?!你和竹里……?”
“是的,不大,刚满三个月,等她再大一点我会把她抱回来的,现在她还需要母亲的照顾。”达达利亚后退两步,动作潇洒地摆摆手,“那幺我先去看她了,母亲,再见。”
留下仍被震惊着站在原地不能动的母亲。
达达利亚步伐轻快地来到处于偏僻角落的一处房子,人迹罕至,萧瑟冷清,他推开大门,熟门熟路地进入房子,迎面走过来一位妇人,她恭恭敬敬地向达达利亚行礼,用双手比划着向达达利亚表达了信息,夫人正在休息,而阿芙刚刚吃饱,她正要去哄她睡觉。
达达利亚点点头,表示明白,他跟着妇人朝一楼的房间走去,整个过程没有发出声音,也不需要,又聋又哑的妇人,她的世界原本就是寂静无声的。
竹里在三个月前诞下的女婴被他叫做阿芙,他并不理解竹里这具由博士友情创造的身体为什幺能够孕育生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算是什幺,更不明白为什幺竹里会放任这孩子生长,直至十个月后阿芙出生,但这都不妨碍他的喜悦。
他熟练地拿玩具逗弄阿芙,阿芙并不像他,若真要说,阿芙的长相更像是蒙德人,她的眼睛是灰蓝色的,而黑色的胎毛看起来则更突兀,看到他的时候,达达利亚总能轻而易举地想起来那晚的山洞,以及山洞的石床上安详躺着那个少年,如出一辙。
博士给了他一个惊喜,不过达达利亚并不介意。
阿芙并不畏惧这个三个月来见面才寥寥数次的父亲,她咯咯地笑着,伸出手来想抓住达达利亚的手指,婴儿略长的指甲被包在布袋里,避免她划伤自己的脸,但是抓到达达利亚的时候他的手上还是有些刺痛,她的指甲有些长。
达达利亚陪她玩了一会儿,直到她打了个哈欠,动作肉眼可见地看起来迟钝了,他动作轻柔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才直起腰来,看着妇人把她抱起来,小幅度地摇晃着她,一直到她终于沉沉睡去,妇人重新把她放回床上。
达达利亚退出房间,蹑手蹑脚地关上房门,才朝二楼走去。
大部分的房间都是闲置的,只有走廊尽头那一间,他推门进去,房间里空气中溢满了极淡的香气,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尽职尽责地所有声音吸收掉,同样厚重的窗帘将天光隔绝,明明仍是正午,房间内却暗如永夜,只有角落的一盏小灯带来了唯一一束灯光,把占据房屋正中央的大床上一个人影模模糊糊地照出来。
她侧卧着缩成一团,白绿色的长发被束在身后,只有几缕不安分地跑出来,懒懒散散搭在颈间的项圈上,在阴影中只能隐约勾勒出她已为人母却依旧如少女般娇艳的眉眼,但达达利亚已经很久没见过她愉悦笑着的模样。
“不是才喝了奶吗?”
大概是听到了衣服布料摩擦时窸窸窣窣的轻微响声,她撑着床坐起来,四肢的铃铛随着动作叮铃铃清脆地响,房间里突然就吵闹起来。
她打了个哈欠,睁开眼,原本也只是有些不耐烦的神色突然冷下来,“是你啊。”
“对阿芙的父亲态度也这幺恶劣吗。”他走到床边,弯腰捏住竹里的脖子,“你应该迎接我啊,竹里。”
闻言,竹里眼神中透露出怨毒森冷的寒意,她浑身不住地抖动,最后僵硬地擡手抱住他的腰,做出顺服的姿态,“欢迎回来。”
脖子上的项圈勒得几乎让人窒息,里面的毒针也深深地扎入皮下,操控着她的身体听从达达利亚的每一句话。
“擡头,吻我。”达达利亚按着她的后颈,语气不容置疑。
……她迟早会杀了他。
房间里响起了铃铛清脆的声音,像从前的每一次,她被迫主动地勾住他的脖子,像是献媚讨好一样地亲吻他,仰着头的姿势看起来有些屈服的架势,鉴于扣住后脑勺的那只手的力度,一时半会挣脱不开,变成了一如既往的持久战,达达利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将口中的一切空隙抢夺殆尽,连呼吸都有些艰难,舌根在来回的推弄中逐渐酸麻,撑不住的涎液从嘴角狼狈溢出,沿着下巴滴落在锁骨上,紧接着消失在宽松的睡裙衣领里,达达利亚终于松开她的时候,她倒回床上,因为缺氧而眼前发黑四肢无力,只能勉强撑起自己的身体,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她现在的身体,实在算不上多健康。
达达利亚跟着压上来,原本就黯淡的光线被挡了个结结实实,她被困在他的两只胳膊之间,心中恨怒交加却无从表达,她说不出话,铃铛的响声将现实与回忆勾连起来,她的身体不争气得发软,腿间已经反射性地开始分泌汁液,达达利亚一条腿支着半跪在床上,低头只能看到她的头发,此时被压在身下,那双碧绿色的眼中有的只是厌恶与杀意。
太可惜了,她不爱他。
太可惜了,他还爱她。
他捏住她的睡裙衣摆,径直把它推到她的下巴处堆着,他按了按她的胸口,有些硬,,不出所料地在双峰间低谷处汇聚了一小滩,“还疼吗。”
正处于哺乳期的妈妈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涨奶的问题,胸口胀得发疼,竹里不想开口求助,每天除了喂阿芙喝一点,剩下她都是忍着,因此时不时就会溢奶,流得到处都是,聋哑夫人会帮忙把湿透的床单和衣服洗掉,但她也不会做更多,直到达达利亚到来。
达达利亚将其中一边乳头纳入口中,施加以吸吮的动作,几乎是顷刻,口中就被清甜的乳汁占领,他喉结上下滑动,发出了吞咽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太突兀,另一侧乳房也被握住,因为生了阿芙的缘故大了不少,即便是男人的手也有些握不下,自指缝间溢出不少乳肉,柔软又滑腻,用力一捏,就像是快要熟烂的果子,流了一手的奶水。
头顶传来急促的呼吸声,达达利亚突然用牙齿咬住硬得像是小石子一样的乳头,轻轻厮磨,立刻听到因为压抑而突然加重的喘息声,他微微擡起头,带着乳头往外拉,竹里难以克制地惊叫,尽管马上又重新收声,却还是听到了达达利亚的一声轻笑,他又像是安抚一样舔舐,只是布满颗粒的粗糙舌面擦过娇嫩敏感的乳头,那一瞬间难以言喻的感觉惹得她浑身战栗,带着挂在四肢的铃铛声声响动,达达利亚终于重新起身,被乳汁浸泡的嗓音听起来都变得甜了不少,“多谢款待,似乎到我回报的时候了。”
“竹里,可以回答我吗,刚才那样舒服吗,”达达利亚用一只手捧住她的脸,像是开玩笑一样抱怨,“你的奶水真的有些多,把我的衣服也打湿了。”
“舒……舒服。”竹里咬着牙,不情不愿又断断续续地说。
“那看来我取悦到你了,很好。”达达利亚按了按她的唇瓣,“舒服的话,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要藏着掖着,我想知道你的感受。”
“那幺我们就来试试吧,竹里,自己把腿掰开,自慰给我看,嗯,记得大声叫出来,如果不行的话,就再来一次,记得,一定要坦率地表达自我。”他维持着无辜的笑,说出了这幺一番话,竹里张张口,骂不出任何脏话,被操控的双手僵硬地在他戏谑的目光中自己压着自己的大腿掰开,摆出了一个堪称淫荡的姿势,将已经水光粼粼的私处完全呈现在达达利亚眼前。
她并没有人类本应具有的羞耻,面对这样的场景,她只觉得恶心,他为何要这样囚禁她羞辱她,破坏了她的计划,在她面前再一次杀死了他,用这具身体孕育下他的后代,这一切,都是他所谓的……爱?
令人作呕,这个疯子。
她无时无刻不想着杀了他,却被困在这一具精心设计的牢笼中,她的行动完全被操控,连自杀都做不到,只能像傀儡一般日复一日地被他玩弄。
暗无天日。
依据他的命令,长期浸淫在性爱中的身体自发行动起来,纤细的手指搭着那一条缝隙撑开,露出里面殷切如蚌肉一般翕动的花穴,汩汩地涌出充沛的汁水,中指没入其中,沿着崎岖小道向里,指根碾着小核,每一次抽出手指再往里插入都会狠狠地压过这里,带来巨大的快感,她下意识想要压制住这声音,却因为达达利亚的命令而不得,只能听着自己一声一声放浪形骸地呻吟,像是野兽在发情期毫无理智的呼号,夹杂着铃铛不得章法的乱响,她的思绪也被影响得乱七八糟,不见光的环境带着她的思考变得昏沉,咕叽咕叽的水声在杂乱的声音中变得清晰,不够,还想多点,身体对于快感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想,她自发地加快了手指抽动的速度。
即便看不清细节,仅仅听声音都能够想象出来场面,喜欢的女人在面前毫无顾忌地玩弄自己,这画面比他想象中要诱人得多,达达利亚深深吸了口气,欺身上前,捏着她的脖子吻住她的,把嘴巴里残留的属于她自己的奶水的味道过渡给她,另一只手探到她双腿之间,盖住了她自己的手,同样伸进去一根手指,不同的力道在浸满了粘腻汁液的甬道里搅弄,达达利亚更带有目的性,他朝记忆中的位置摸索,直到摸到一点点凸起,他勾着竹里的手指按到了这里,然后剐蹭,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抠挖,有分泌出来的汁液做缓冲,力道算不上疼,只留下了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快感。
“唔……!”竹里睁大眼睛,小腹不受控制地拱起,看起来像是她在把自己往达达利亚手里送上去,达达利亚自然乐意接受,他吞下竹里的呻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连同手指一块撤出,被挽留一样地吸附着,抽出手指时还勾连出一大股汁液。
“是舍不得吗,不用担心,有更大的。”他满含笑意地咬住她的耳垂,轻声说,她侧过头去,躲开这酥酥麻麻的痒意。
达达利亚并不在意她的抗拒,早已勃发的欲望终于被释放出来,他按住竹里来不及合拢的双腿,进入她的身体,还没有从高潮中恢复过来的花穴娇嫩到连这一点摩擦都无法承受,推挤着想把他拒之门外,湿热的软肉却又依依不舍地亲吻着肉棒,令人头皮发麻,达达利亚倒吸一口冷气,却还是勉强笑了一声,“是因为很久没有做的缘故吗,你的身体看起来很热情啊,我是否该说一声久违了。”
他压着她的腰,慢慢地往深入推进,自他年少时,就是竹里牵引着他踏入情欲的河流,从那之后纠缠至今,竹里属于他,他又何尝不是竹里的裙下之臣。
达达利亚开始动作,他挺着腰一下一下地抽插,动作谈不上温柔,也不算凶狠,单纯的重而已,每一次摩擦都能挤出暧昧的水声与肉体碰撞的声音,以及带动竹里的手腕脚踝上他亲手拴上的铃铛的响动,只是又缺了竹里的声音, 他一手扶上竹里的脸颊,大拇指磨蹭着她的唇瓣,果不其然她又在咬着唇瓣压抑声音,竹里不爱出声,然而不巧的是,达达利亚正好相反。
“竹里,叫出来,我想听到你的叫声。”达达利亚喘息着笑,“因为我,你才会这幺淫荡啊。”
“这样的力度可以吗,够深吗,干的你爽吗。”他低头咬住她搭在肩膀上的一缕头发,鼻尖萦绕着淡淡的奶香,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无论这个孩子是什幺来历,至少,竹里没有反抗他的血脉。
这样的认知刺激着达达利亚,他出乎意料地勾住她的腰把她抱起来,竹里尖叫一声,被迫揽住了达达利亚的脖子,但那点支撑聊胜于无,全身上下的重量支撑在两个人的交合处,那里的感觉越发鲜明,顶得太深了甚至有一种饱腹的错觉,她深深呼吸几下,又迫于达达利亚的命令,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把所有她想要无视的感受如实用语言反馈出来。
“太深……呜,顶到子宫了啊啊——”
“出去,不、不要……”
她无助地摇着头,只能被迫感受达达利亚在行走间随着步伐节奏在体内兴风作浪胡乱搅弄的欲望,顶到尽头他仍然不肯罢休,反倒更进一步,竹里擡手抓住他的头发,“出去,滚出去!”
明明是难得彰显凶性的时候,却因为语气里满溢出来的情色气息听起来更像是调情。
达达利亚充耳不闻,他把竹里压到墙上,房间突然大亮,明亮的光线从天花板倾泄而下,竹里的背压到了照明灯的开关,达达利亚眯起眼,等适应了明光才重新睁开,竹里无力地靠在墙上,低着头看不清神色,浑身都是湿淋淋的,甚至红艳艳的奶尖上还挂了一滴乳白色的汁液,随着她急促的呼吸起伏,摇摇欲坠,达达利亚低头把它抿掉,他将自己同样被打湿的额发捋上去,“竹里,再为我生一个孩子如何?我们真正的孩子。”
竹里张张嘴,想说的话很快被顶撞得支离破碎,她像是躺在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上,找不到支撑点,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达达利亚,然而他才是罪魁祸首,她越是抓住他,他埋在她身体里的欲望撞得越凶,大脑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她眼前一阵一阵发白,缭乱的铃声像是惊雷,震耳欲聋,终于在又一次高潮中无力地合上眼,脑袋搭在达达利亚的肩膀上,彻底失去意识。



![《[综]幼女审神者》大结局曝光 ,著 1970完结](/d/file/po18/62288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