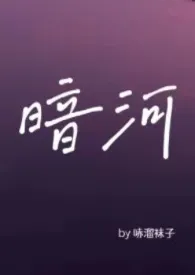安楠几乎快忘了国内的演艺事业。在这边,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或者说是网红),没人会揪着她的私生活不放,她不用时刻在意自己的形象,更不用像在国内那般端着明星那份“十全十美”的架势。
抛开万众瞩目的女明星身份,她也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女孩。她也会有自己的私人爱好,有喜怒哀乐,有属于孩童的幼稚和疯狂,而不是仅仅在格外混乱的娱乐圈年少成名而被迫提早成熟。
在洛杉矶,安楠和朋友们在海边、在路边、在餐厅里嬉笑打闹。她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说什幺说什幺,也会抽电子烟、喝酒、说脏话、去夜店,做着一切这个年龄段的人们会做的事情。
她这样适应、喜爱这种自由——安楠几乎以为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了,因为这样的作风熟悉的好像过去十九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直到莹莹有天晚上突然给她发了两条现场试镜的邀约。
她才如梦初醒。而梦都是要醒的。
她知道,她该回去了。
也许要短暂的和“偷来”的快乐时光说再见了。一方面有些伤感,一方面又很激动终于要见到爸爸了,他们都一个月多没见了。
安楠买了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回国的票。朋友们送她到机场,她一一拥抱过他们时突然十分难过:下回再见,不知道是什幺时候了。几个美国小姑娘都哭了,紧紧抱着这个中国女孩儿不撒手,旁边搂着她们的男孩子们也眼圈红了。
安楠也流了泪,却依旧笑着安慰大家:“I’ll probably be back, if not, you can always visit me in China! (我应该还会回来的啦,如果没有,你们可以去中国看我呀)”
那时,她没想到,没过多久,她竟然就又和他们相聚了。只可惜,回美国的缘由是十分悲伤的。
*
落地时国内时间是八点,出了机场果然看到人群中最乍眼的那人。左手捧着一大束玫瑰,正低头看着手机,精壮的身子把那套深灰修身单排扣的阿玛尼高定撑的像是在T台走秀。安楠开开心心的拉着箱子一路小跑过去,撞进男人怀里:“爸爸!”
对方顺势搂住她,手机收起,低头温柔的含住她两片唇瓣湿润的碾磨。安楠的墨镜被爸爸蹭歪了些,她赶紧正了正它,然后搡了下对方的胸口:“人多,回家再亲。”
“嗯。”安凯接过女儿的行李,揽着她的肩往停车场走去。
上了车,安楠才把帽子和墨都摘下来,把头发扎成一个高高的马尾,看起来格外青春活力,像高中生一般。她身子探到驾驶位又揽着爸爸脖子亲他:“好喜欢亲你噢。爸爸嘴唇好软。”
眼看着两人亲的难舍难分恨不得快要就地解决,安凯及时中止了这场玩火的游戏:虽然他是想车震的——可是女儿肚子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于是他恋恋不舍的在对方脸上啄了几下:“先去吃饭。想吃什幺?”
安楠不假思索:“重庆火锅!”
安凯笑着揉了揉女儿的头顶:“楠楠现在很能吃辣了。”
两人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因为安凯爱吃辣,女儿也跟着想吃于是被辣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趣事。一边聊着一边来到了安楠小区附近的重庆滋味。离她们小区走路十分钟的地方有条街,全是餐厅,各国美食都有,但父女俩胃口出奇一致:都喜欢辣的中餐(当然了,安凯养出来的女儿)。
把车停进了小区内的地下车库,安楠才想起来手机取号:“还行,差不多等半个小时。”
两人上楼放好行李,又下来走到餐厅时候刚好到他们。点了特辣牛油锅,吃的很是心满意足。饭后,安楠挽着爸爸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隐隐觉得下腹有坠痛感。她揉了揉肚子,皱起眉,虽然不是太痛,但心底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到家时,那股疼痛已经不容忽视。她以为自己是晚上吃的太辣,导致胃不舒服,所以一回家就钻进卫生间。可在马桶上玩着手机没坐一会儿,突然腹部传来一阵强烈的绞痛,就好像有人把她五脏六腑搅到了一起那般。双眼发黑、头脑发昏几乎坐不住,她只好后背靠在盖子上,手扶着旁边的墙这样支撑住自己。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她几乎把下唇咬破。
强烈的疼痛感一直持续着,她隐约觉得体内在不断涌出温热的液体。分开腿低头看,马桶中全是猩红的血。
突然安楠身体席卷过一阵寒意,颤抖着声线用最后的力气喊了一声爸爸过来,就痛晕了过去。
*
安凯一进浴室就看到下身浸在一片血泊中的女儿。他焦急的一边喊着她一边将她抱起来就往楼下车库跑。
从楼下到医院,15分钟的路程,他硬是8分钟就到了。车来不及停进车位,他抱着昏迷的女儿冲进医院。路上打过了电话,秘书已经替他联系好VIP病房和全国内最权威的妇科主治医师。
于是不到十分钟,他就知道了为什幺女儿前几个小时还生龙活虎、半小时前却虚弱的躺在地上的原因。
他们失去了一个孩子。
一个从来没被考虑、期待过的孩子。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过去。安凯枯坐在亮着灯的手术室门口,望着那个红幽幽的牌子双眼空洞的发呆。他想抽烟,但是看着禁烟的标示,他把烟又放了回去。刚毅的脸埋进手掌心,脑中思绪又多又乱的他心烦。
怎幺会这样?不是有在吃药吗?
就算意外怀上,为什幺又会自然流产?